【姚勤然|金龙贺岁·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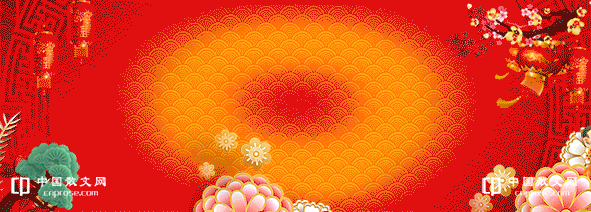
姚勤然|金龙贺岁
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作家简历
★
姚勤然 河南长垣市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南思客》签约作家,长垣市作协副主席,长垣市第二届政协委员,现为中州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作品被多家报刊杂志登载和自媒体转载。《豆豆》获2004年女友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鲁迅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七届全国青年征文优秀奖;《雨中的父亲》获2022年第九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天然文岩渠成百里画廊》、《长垣与黄河》等入选《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栏目。
家在长垣
在四川的时间久了,时常会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家迁过来,四川可是天府之国啊,气候温润,名山大川峨眉山、贡嘎山、九寨沟,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等美食数不胜数,而且你妻子还是四川人……朋友列举了诸多理由。每每这个时候,我会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家在长垣。
妻子是江油人,常年在家料理家务,她经常给我说,她现在成了地地道道的长垣人,我却变成四川人了。是啊,我在四川做事,一晃就二十多年了。但在我心里,我的家在长垣,始终没有改变,每年春节我都会提前到家。
我总觉得,我的心时常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系着,无法挣脱且又魂牵梦绕。长垣第一位县宰子路最早把他老师孔子儒家思想的光辉播撒在了这片古蒲大地上。曾几何时,夜深人静,先贤关龙逄、蘧伯玉、李化龙穿越时空纷纷出现在我的面前……出现在我面前的还有与长垣有着不解之缘的酒圣杜康,汉书《说文解字》载:“古有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长垣”。古蒲长垣,既是杜康酿酒的地方,又是杜康生活安居之地。长垣人受杜康的点拨,最早掌握了酿酒技术。也难怪长垣人对酒情有独钟,据说一业务员为了顺利拿到业务,手举一瓶白酒一干而尽。
长垣在河南的东北部,与山东东明隔黄河相望,我家就在黄河所处豆腐腰的位置,小时候常遭水灾。夏天没有吃的,我们还可以去河滩挖野菜,到堤沟里去摸鱼,到了冬天就不行了,找不到吃的,夜里饿得睡不着觉,母亲就给我们讲城里人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知道,母亲根本就没去过县城,等母亲真的能去县城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家搬到长垣县城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想着早点把父母一起搬到城里,遗憾的是,父母还是在搬迁之前离世了,终没有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一觉醒来,我站在楼上俯视远处的万家灯火,心起波澜,会想起父母生前的模样,会想到他们伤心的时候,也会想到他们的微笑。
曾经的长垣,“春天喝不上糊涂,冬天穿不上棉裤,十里八乡见不着瓦屋,小伙子娶不上媳妇”。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级领导的正确引导下,短短几十年,长垣人拼出了“中国防腐蚀之都”、“中国起重机械名城”、“中国卫生材料生产基地”和“中国厨师之乡”四张金字名片,20年,经济总量硬是翻了17倍,一跃脱胎为新时代大陆的小香港。
富了的长垣人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确立了“水绿阡陌、竹韵蒲城”的发展思路,投入巨资实施“畅通水脉、以润破题、以水润城”的城乡生态水系建设工程。天然文岩渠百里画廊、九龙湿地公园、三善园·明察园水系公园、王家潭千亩湿地公园等游园相继开园,给每一位普通民众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
难怪妻子在四川她娘家人面前骄傲地说:扳指头数数,全国免费坐公交的城市有几个?只有俺长垣。她故意把“长垣”的后音拖得老长,听的人无不啧啧称赞。最后她还补充说,一到秋天,满大街玛瑙一样的海棠果随便你摘,在俺长垣,只要你想做,没有找不到的工作,起重设备厂都是上千家,还有几百家卫材厂,超市饭店常经常挂牌招人,方圆临县的人都往俺长垣跑……
从外面回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村里转转,遇到年轻人打打招呼,遇到年长的唠唠家常。如今回去,已经看不到村庄了,前年全村整体从黄河滩区迁入了城里,老村已经复耕了。但我还是要回去,夏天看麦浪翻滚,秋天看玉蜀黍葳蕤蓬勃。尽管看到的不是我家的,是别人流转的,我还是要来,哪怕就是站在路边看看,心里也是踏实的。不来,总觉得心里欠欠的,还不好受。
我知道,我的根已深深扎在这片土地上,就是将来有一天死了,我的灵魂也要变成一朵云,飘在长垣的上空,俯视长垣一路高歌猛进、如火如荼、繁荣昌盛……
母亲与长垣县城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与父亲不和,他们经常吵吵闹闹的,其实,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什么大事情。那时,我哥还在北京当兵,我和两个姐姐总是站在父亲一边,一同指责母亲,评母亲的不是,看着母亲被气得哭天喊地,指着我们骂,我们心里很舒服,很解气。母亲虽气,但到了做饭时候,她照样做饭,只是把风箱拉得咵嗒咵嗒响,我们在厨房旁边还能听到母亲抽泣声呢。
听邻居四奶讲,我们父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吵架,她听母亲说深夜我母亲醒来的时候,床上就不见了父亲,而且不止一次。母亲质问我父亲深更半夜去哪里了,我父亲说去地里转转,看看有没有人偷庄稼,我母亲听了,总是心存疑虑。后来母亲才知道,我父亲当时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夜里要到区上开会。大跃进年代,我父亲是生产队长,要深翻土地,我父亲还要检查别人的深挖情况,看有没有作假的,我父亲那一份,母亲还得替他干,母亲的手磨出了血,回到家就找父亲闹。
父母亲一路走来,都是在吵吵闹闹中度过的。到了晚年,母亲患了糖尿病,眼睛也得了白内障,是父亲寸步不离,把母亲照顾的无微不至,每到做饭前,父亲总要先问母亲想吃啥。
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去一趟长垣县城。在她的心目中,县城一定很大,高楼大厦很多,柏油路很宽,人很多,很热闹。其实,我们住在黄河边上,到县城也就50多里路,搭公共汽车几块钱,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农闲了,父亲说带母亲去县城走一趟,回来住我大姐家里,我大姐家到县城才几里的路程,母亲说,去城柳弄啥了(我们乡里人把县城说成“城柳”),没事没非的。
平时,母亲天天在家忙,总有忙不完的事儿。
空闲了,母亲就盘着腿纺棉花,我在旁边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看书,我喜欢用别针播煤油灯的灯花,每次播时,母亲总是不会忘了嘱咐我把灯头压小点,那样灯能省油。那时,邻居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母亲常拿人家给我做榜样,说人家一辈子脱离苦海了,再不受苦受累了,成公家人了。我做完作业,就上床睡觉,往往,一觉醒来,还能听到嘤嘤的纺车声。母亲用纺出的线再织成布,染成蓝色或黑色做衣裳。那年,母亲用蓝色布给我做了一件上衣,穿到学校被很多同学耻笑,笑我都啥年代了,还穿老土布。我回家脱下来说啥也不穿,母亲说,穷没根富没苗,咱现在穷,不能穷一辈子呀,你好好念书考上大学,看谁还敢笑话你。
母亲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韩金镯,也许,姥爷给母亲起这样的名字,是想让母亲将来穿金戴银,富贵一生的,可哪曾想,母亲一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母亲不识字,但母亲平时会很多口头禅,遇到与邻居有点小矛盾,母亲会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不如近邻,遇到谁做恶事,她会说什么邪不压正了,身正不怕影子歪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在我两个姐姐身上用的最多的,每天一大早就把姐姐从床上喊起来下地干活。大姐出嫁了,农闲的时候,大姐想接母亲去她家里住几天,母亲说啥也不去。大姐走了,母亲给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母亲第一次去县城,是她眼睛得了白内障,要到县城做手术,当时是在县城南关郭氏眼科做的,记得手术前母亲很紧张,手不停的颤抖,父亲在旁边一直开导她。手术完吃了一碗饺子就搭公共汽车回家了,母亲第一次进城,啥也没有看清楚,更没有在城里逛。
等带母亲经常去城里,已经是母亲身患糖尿病的后期了。
说真的,只怪我们做子女的平时没有把母亲的事情当回事,平时很少把母亲的念想放在心上,母亲的身体也没有给她检查过。平时母亲身体不舒服就熬,实在熬不过了才在村里或乡医院拿点药,母亲平时从来没有给我们要求过啥,总怕给儿女带麻烦,等她老人家倒在病床,已无力回天。
像千万个母亲一样普通,母亲一生也没有离开过生养她的黄河,每逢春天来临的时候,偌大的黄河滩到处都留下了母亲挖野菜的足迹,冬天的早晨,东方的天空刚泛鱼肚白,母亲纤小的身影已经踏着白霜在河滩晃动,她把捡拾大雁的粪背回家当猪的口粮。
河滩养育了母亲,也养育了我们一家人。最后,母亲把自己也永远交给了黄河滩。
母亲走的时候,我连最后一句话也没有听到她说。当时,春节刚过,我正在四川一个电厂组织防腐施工,妻子打来电话告诉我母亲病危的一些情况时,已经很完了,赶不上飞机,我就买了当晚回家的火车票。第二天到家天已经黑了,风卷着纸屑、尘土满大街乱飞。我看到我们家门口围了很多人,我打了个寒颤,心一下收紧了,我预感到事情的不妙,回到屋里,一眼就看到母亲已静静的在床上躺着,任凭我跪在她的床前怎么大声哭喊也不答应我了,哥哭泣着对我说,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眼睛都没有合上。
我知道,母亲肯定也是想看我最后一眼,不看,她不瞑目。
我心悔呀。想想,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养大,几个儿女连老人小小的心愿都没能实现。扪心自问,我们做儿女的心里真的会没有遗憾?人一旦走了即使扇自己一百个耳光又有什么用?
我的心在滴血。
我真希望,母亲是暂时离开我们的,暂时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还会回来的。即便不回来,她去的那个地方,一定能让母亲安享尊荣,再无病痛,是一个幸福的世界……
小 祝
自从工地上从老家新来了一个小伙,我的担心开始多了起来。
小伙子岁数不大,身体瘦的像麻杆一样,干活没说的,勤快细心又利索,就是不合群,不爱说话。晚上吃了夜饭,一个人坐在工棚旁边的土冈上,火红的夕阳把他蹲着的身影拉得修长,两只白鹭从他头顶飞过,他面向家乡的方向发呆,两行泪水顺着脸颊像虫子一样往下爬。
那天,太阳还在西边土山上的树尖上晃悠,被汗水浸透的衬衫裹在我的身上,气冲冲地跑回到工棚,把刚燃起的烟猛抽两口又恨恨地摔在地上,我被气疯了一样,还在为下午工地的事情耿耿于怀。谁不气呢,作为乙方,我们虽然站在弱者的一方,就该受甲方拿捏吗?他们不高兴了随便一歪嘴,你施工的不足就出来了,而且让你尴尬得无话可说,就说下午工序验收的事情吧,甲方施工员手拿一节折断的钢锯条,在我们刷过油漆的管道上用锯条刮,挂掉了就视为不合格,天下有这样验收的吗,他说他们就是这样验收,厂里上过会的,他要为他们的项目质量负责。路边细密的柳枝里发出阵阵蝉鸣,看着眼前这个比自行车高不了多少的施工员,我怒火中烧,牙齿碰得吱吱响。
我正在气头上,新来的小伙也不知啥时候站在了我的面前,他摩挲着自己的手指头,嘴涨了半天才说,老板,给你商量个事儿。我心里正烦着呢,现在的工人难缠,在家给老板讲工资,在外给老板讲吃住,你语气稍微重了点,当即就走人。曾有一位同行老板说,现在的工人,都抱着侥幸心理,此地不留爷,自由又留爷处,得像祖宗供着。我用眼睛的余光斜视了一下眼,沉默了半天问,啥事?他说,工地上使用的电动工具能不能包给我修?包月或包个数。我还以为啥事呢,平时工人使用的工具没人保养,经常正在施工就坏了,误工误事,有人主动提出承包的事情,我便爽快地答应了。
平时,工人下班不是喝酒就是玩手机刷视频,只有新来的这个小伙晚上摆弄那些工地上除锈用的角磨机,有时,一直到深夜,蚊子围在他四周向他挑衅,开始不停的偷袭,后来干脆轮番轰炸。为一个月能多挣200块钱,小伙子不容易啊,我暗暗注意上了这个名叫小祝的小伙,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创业的时候。
甲方为了要节约成本,拉工地一车锈蚀严重的二手管道让我们做防腐处理,还要求我们把管道打磨得见金属光泽验收合格了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工人嫌脏,不愿意干这费力不讨好的活,如果非要让他们干,要不就双倍工资,要不就打行李走人。甲方给的工期又短,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小祝找到我,要承包,他要一个月的工钱。别的工人都说他傻,暗地里刚他给我多要点儿。
小祝想把同村的老王拉进一起干,老王干了很多年的防腐,属于老油条了。他劝小祝不要接烫手山芋,天热不说,最关键是活难做,甲方质量要求又严,划不来,不如就干日工轻松。
老王还找到我,劝我不要包给小祝,说他不知道深浅,说小祝活人不易,命像曲曲菜一样苦。他还问我,你不认识邻村咱老大队的祝凉粉?他是老祝的儿子。
我咋不认识老祝呢,老祝的老井凉粉吃起来滑润劲道,名扬我们黄河滩。还知道他开三马车过河拉红薯,翻车砸断了双腿,媳妇家里带着女儿外出打工,再没有回来。多亏小祝父子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奶奶照顾。岁月不饶人,现在,小祝的老奶奶已瘫痪在床了。
老王说,小祝这孩子是个孝子,他想多挣些钱给他父亲按个假肢,到时家里有他父亲照顾他就可以安心在外面挣钱了。他现在就想多挣钱,只要能挣到钱,吃再多的苦他都不怕,小小年纪他心比天高呢。
最后,活还是给小祝包着干了。
小祝起早贪黑,手里角磨机不停地飞转着,把管道上弄得火花飞溅,铁锈抹粘在他工作衣上与汗水和成了锈泥,他脸上裸露部分也变成了铁锈色。
不到两个礼拜小祝就完成了任务,我也高兴,还给他多加了一半的工钱。
人熟了就没了隔阂,有一天晚上小祝来到我的住处悄悄告诉我说,在他心里,他一点儿也不恨他的妈妈,他也想念他的姐姐,他将来挣了钱要去把他的妈妈和姐姐找回来,他盼着有一天自己能和别的家庭一样,一家人在一起亲亲热热团团圆圆的。
又干了一段时间,小祝回家了。还甭说,这个小祝,久了不见还真叫人念想。我微信问他,过了多久他回我说他正在郑州给他父亲装假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