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用散文创作聚集更多的乡土共识
第五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日前公布,江苏作家周荣池榜上有名。作为扎根于基层的青年作家,他以自己所在的村庄南角墩为原点,深入里下河平原的现场,将大运河地理与历史的双重空间进行延伸,创作了多部作品,其中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周荣池以乡土为对象的创作直击城乡发展的现状,在聚力以散文为主要形式的表达中,体现了一个基层作家致力新乡土散文写作的执着追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就乡土散文写作的现状与作家个体的选择与走向,表达了自己的实践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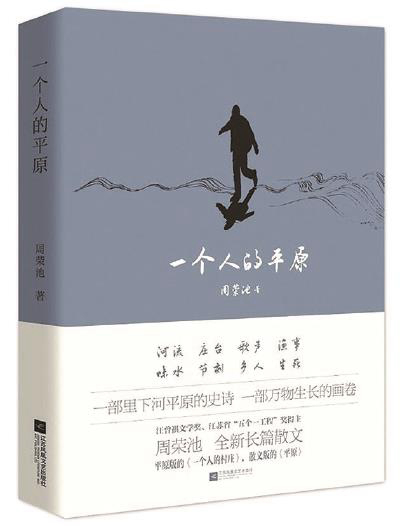
选择做困难的事情
更有价值
记者:一直以来你的写作围绕着乡土题材进行,包括散文、小说、散文诗乃至评论创作,不难发现,你这几年的写作更倾力于散文写作。
周荣池:以我个人对文学现状的理解,在诸多文体写作中,散文是一种被应用最为广泛而对其创作与研究相对失范与缺位的文体。我们可能走在一条最为宽阔的道路上,但它的方向、边界和秩序也是最为令人担心的。我在自己的散文集《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的后记《散文写作的“危险性”》中,提出过这样的想法:“自媒体缺乏学理的规范和约束,基层写作往往也存在‘失范’甚至‘放肆’的情形——什么人都在写,什么事情都在写,什么时候都可以写,让文学尤其是散文写作处于一种狂欢而不知自律、警醒和规范的状态。”也许我对于散文过度的焦虑本身也是一种问题,但我愿意用个体的努力将认识到的问题进行放大和解剖,试图分析和解决一些问题。这种姿态无异于是“大路上的逆行”,我也没有完全期待或者声明自己能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如果通过努力只能证明“此路不通”,可能也是对散文写作实践的一种有效尝试。这种实践或许有些执拗,然而就像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样会遇见各种困难和问题,正是因为存在困难以及去解决困难的过程,才让我们的选择和努力更加有价值。否则,我们的写作势必因为随波逐流而变得平凡甚至庸常,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的“警醒”和某种“野心”。
记者:事实上,你的创作也起源于散文,你觉得这个起点对你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周荣池:我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选择散文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式,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抉择,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为我早年读书的某些缺陷,我的生活储备和文学准备相对于许多专业作家而言是有明显缺陷的。我所在的平原生活和文化的资源相对匮乏,就像是平原的地形一样平淡无奇,没有高大山峦的壮阔,没有极端气象的对抗,也缺少极度苦难的逼迫,这样的生活资源中要构建奇崛、深邃以及动人的文学场景,对于一个人而言当然是“不幸”的。文学上的“不幸”反而是因为生活中有“幸运”,因为故事往往肇始于“事故”。同时,在自身的文学准备上,我因为早期匮乏的文学教育和自身贫瘠的文学秉赋,写作难以进入更为专业特别是更具“特质”的风貌。所以,选择散文这一文体并决心恪守这一现状,对我而言并非完全“自愿”,算是某种求而不得后的“自实其果”。
记者:你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些实绩,这包括你出版的六部散文集以及获得的八个专业散文奖项,可你的一些访谈和自身写作中一直在声明“散文写作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是哪些?
周荣池:以我自己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教训来看,眼下的散文创作存在这样几个具体的问题。一是专业写作者对于散文文体的重视程度缺位。我们总是以为有大量的散文存在就是某种繁荣,但这种繁荣是令人心虚的。我们缺乏某种专业态度和自律精神,只把它的某种便利性作为前置或者潜意识,对于如何去善待和研究还远远不够。二是我们对语言这一基本问题还缺乏像其他文体一样的严肃和专业精神。我们期待更加严谨、诗性和优美的散文语言,这是不争的事实。第三,以我自身以往的一些写作为例,在散文自身的题材发掘上也有认知上的缺陷,大量的精力花在乡土题材写作上,却又没有脱离回忆、观望以及沉湎的语境。对于城镇化、城市化以及更为宽阔的散文写作视野,探索得还不够深入,这一点上来讲确实存在深切的“危险性”。
“现代化”最可能解决
乡土写作的问题
记者:你所说的“危险性”,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写作的一种反观,因为你的散文主要聚焦于你所熟悉的乡土,具体而言,它是何种危险?
周荣池:我们写作者常常有某种幻觉,因为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和实践,特别是创作和发表了一定量的文本就觉得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甚至王国,这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感动。一个人书写自己熟悉的场景这是一种必然选择,因为个体深切的生活经验和体会,特别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写作往往显得恳切而真诚。然而,这并非是我们一直要写熟悉事物的确切理由。当然,对于一个还处于准备期或者实验期的写作者而言,把熟悉的物事和情景写得熟练与精彩,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操练和改进的必要过程。写作当然是需要不断实践和纠错的。但是,在技术进入某种醇熟之后,不断的调适甚至革命性的改变也是需要的,否则将面对重复自己的“危险性”。所以,眷恋过去的场景,更多的是为了最终的“离开”,从而锤炼自己有不断新变的决心和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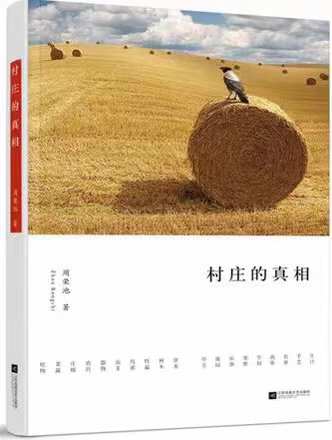
记者:在你的乡土散文创作中,“离开”的意识最早产生于何时?而“新变”又体现在何处?
周荣池:以我并不漫长的写作生涯来看,我对于自己散文写作的反观和不满,还是“觉醒”得比较早的。一开始我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其必要性,只能说是某种敏感与自觉。但当我手上的文本越来越多,喜悦却越来越稀薄,我才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种意识,明确地讲是从《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系列散文开始的,这就像是一个隐喻:我写得太多了,村庄都不愿意再对我发声,根本原因是我写得太多却没有写好,我对乡土过于沉湎而缺乏反思,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因为现实生活场景的变化,我对于城市生活与过往乡土的事实(事实上它对我而言已经不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引发了自身的焦虑和恐慌,我一度面临一种无法找到答案的问句:我所写的一切还存在并被需要吗?也由此,我迫切地感受到了变化的必要性。
记者:所谓“新变与离开”,或许由你后来推出的《大地的角落》系列散文可以一窥,你在其中不断地在讲“现代化”问题,这种现代化显然具有复杂的内涵。
周荣池:2023年我参加了鲁院43期的高研班,除了听取一系列文学讲座之外,更大的收获是我真正在一线城市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我这个期间面对的城市,和自己平常生活的城市在现代化条件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即便是在超大规模的一线城市,我们仍然面临着乡土的现实问题以及对乡土的反思。当我站在人流涌动的城市天桥上,看到脚下的车水马龙,我突然惊醒,这些人包括我自己,无不是一面在果断地背离故乡,同时又在深情地向往着故乡。从那一刻起,我就对“大地的角落”系列散文做了策略和技术上的调整,换一个城市中的视角去看乡土世界,这让我得到了更多的启迪:我们对于已经到来的现代化,应该更深刻地去解析它,也更多的去拥抱和阐释它,因为“现代化”最可能解决我们乡土写作的问题。
更多的写作
应该是“一个人”的
记者:你的写作越发地体现“一个人”的情绪和认知,如你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所体现的那样,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的写作与你所看重的“现代化”之间,它们的关系建构必然需要作家的努力。
周荣池:我们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明显固化的思维,或者说是被“暗示”了的观念和情绪。写作者作为个体,看上去充满了个性和自由,但事实上我们又是在从众和重复。自由有时候非但不是特点,还可能是形式和包袱。比如我们写乡村,总是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厚古薄今”的情绪。可是村庄还真的回得去吗?我们还真的想回去吗?如果我们能回去,那眼下的现实还成立吗?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自设的幻境中,也许因为发表和出版的便利,就以为我们所作出的努力都存在并且成立,甚至成为一种骄傲的经典情绪和认知,可是当我们的肉身回到乡土,一切早就不再是当年的样子。最重要的是,“想当初”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那一切为什么又会消失或者被取代?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我们真正回到现代化程度惊人的农村,一切就不攻自破。所以,我觉得写作更应该体现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更应该是“一个人的”——这样的话即便是误判,也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光亮。
记者:当我们回到乡土的载体,也就是一个具体的村庄,它们对于我们大量的书写而言,确实是显得沉默的。你的散文集《村庄对我守口如瓶》是村庄的失语,还是一代人或者写作者的失语?
周荣池:“守口如瓶”这个词是我的某种矫情或者一种策略。村庄并没有失语,同时它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在城镇化、城市化乃至全球化的多重语境中,卑微而又敏感的村庄其实内心有千言万语需要表达。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物理空间上的乡村,在城市中也明显地存在于众多的细节和角落。因为人还是向往乡土故地的人,所以城市反而更像是一个个巨大的村庄,统治这些村庄的思维、情绪和办法很多依旧是乡土的。我说“守口如瓶”,是因为乡土对我们的发言保持沉默,不是因为我们的失语,恰恰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呓语”令现实感到不满。作为写作者,我们不能罔顾这些重要的现实和事实。
记者:系列散文《大地的角落》,似乎表达着你更为明确的回归和退缩,是不是可以说它是你对乡土进行大规模写作之后某种深刻的踞守抑或是反思?
周荣池:我的“退缩”并非因为我觉得自己说明白了乡土问题,更不是觉得我们今天的散文写作理解和解决了大多数的农村问题。相反,我对自身的乡土散文写作面临的众多问题越发感到不安和警惕,因为自感能力不及又不敢总是游离失所,所以便退守到更为具体的角落和细节上,用各个击破的方式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这一个系列的写作将陆续推出,从规模上来讲它是“庞大的”,但从精神内质上来说它其实仍然是零碎而具体的。这也许更和一个人的写作认识和精力有巨大的牵连。人的年龄见长,就更愿意做具体而可行的事情。但我自然是会一直踞守在乡土写作的平原上,将一个个的角落作为阵地。会不会一直是“南角墩”这样的具体村落也并不那么重要,它更可能只是一个具体的标识或者符号。我更想做的是用散文这样的形式,努力地聚拢起更多的共识与共情,形成一个更为诗意而可靠的共同故乡——它存在于过往,生长于当下,也应该永生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