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山:安静地写、认真地写,写下去就是一切
记者:“诗和远方”是当下很流行的一个概念,您也曾写过“行走和写作是一生的事情”。十八岁出门远行、二十岁入川读书、二十四岁南京深造、二十七岁谋生杭州、三十三岁远赴新疆……您的人生经历似乎也在践行这一理念,能谈谈远方或行走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卢山: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里写道:“我整个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梦,这个梦,由我每天散步时分章分段地写。”散步构成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一生。
于我而言,行走和写作构成了我生命的某种“散步”。人生的精彩之处在于未知的可能和无限,在于那种“在路上”的险峻和壮丽风景,而写作就是我的精神履历表,构成了我丰富的人生镜像。
从故乡安徽石梁河畔到成都求学,从成都北上金陵南京深造,再次南下杭州谋生成家,最后又一腔孤勇前往塔里木取经,用赵思运教授的话“大河拐大弯”——这些年诗歌记录了生活的奔突现场和心绪的辗转反侧,形成了个人的生命诗学。
故乡的石梁河是我写作的起点,我的文字里永远站立着河边上的那棵大柳树;成都和南京宠爱了那个不可一世的白衣少年,誓言和牢骚漫天飞舞;杭州山水安顿了我躁动的青春,并在一地鸡毛的职业困顿中给予我深刻的教诲和温暖的佑护;新疆塔里木为我的生命赋能,“天山赠我一轮王昌龄的月亮”,释放出了那只被生活囚禁的猛虎,得以暂时驰骋在塔里木的星空下,瞬间扩大了我的诗歌版图。
我承认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这些年在学业和职业上也曾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生活将会多么无趣,甚至是一种慢性自杀,至少是对生命和才华的一种辜负。远方永远在诱惑着我,呼喊着我,催促我上路。远方的山水里蕴藏着我写作的巨大能量和因子。所以,即使诗人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 一无所有”,我也会划着我的断桨继续向着新的星辰大海出发。
记者: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杭州和新疆是您人生轨迹中两个重要的节点。两地自古以来,也都是诗歌的热土,不同的是杭州的诗歌更偏向山水人文,西域则以豪迈的边塞诗为主。这两种诗歌传统,您是如何继承并融合的?
卢山:我的诗歌写作是那种精神地理学的,文字里可以挤出甘苦和眼泪。美国诗人、评论家简·赫斯费尔德说:“只有足够深入的凝视存在,你才能最终觉醒于万物之中。”我为存在发言。我的存在就是我的风格。地理位移的转变、风俗环境的变化,势必会对一个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山水、人文、风物、经验都会促成新的视野、刺激新的体验、形成新的诗歌美学。我显然是巨大的受益者。
我曾在西湖的宝石山下工作过几年,月明花满枝,楼台深翠微,被江南山水人文豢养教育,我尽情呼吸着湖山的气流,诗歌里流淌着缱绻神思和湖光山色。几年里,陆续写作了数百首江南题材的诗歌,出版了诗集《湖山的礼物》和《宝石山居图》。从宝石山来到天山,从西湖来到塔里木河,被辽阔的塔克拉玛干收养,天地为我赋能,我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没有大地就没有大文章。一次奔赴云层之上的远行,带给我写作的巨大风暴。来到天山脚下、沙漠之门、塔河之源,我的诗歌写作和人生迎来了一种深长开阔的表达。我在诗歌里写道:“当我一个转身,登上了西去的云层/翻越一座白雪皑皑的新大陆,降落在塔里木河畔。/我写诗,天山赠我一轮王昌龄的月亮;/在深秋的湖畔,我与几万棵老不死的胡杨抱在一起痛哭。/塔里木的地火穿越历史的岩缝,燃烧着我和唐朝的经卷。/天山在上,我口含一轮落日坠入那无限永恒的苍茫。/在每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我身体里西湖的波浪/一次次覆盖我辽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失眠。”
塔里木本土诗人老点说,皖北故土的石梁河通向了塔里木河,宝石山连绵着天山,古今的明月,他乡的明月亦成了卢山诗中的明月。就这样,一个心中奔涌着山川河流的诗人,在西域大地上赢得了升华。
我觉得江南和西北两种文化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滋养和映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江南和西北竟然在我的身上毫无违和感?可能我的身体里栖居着西湖,也流淌着塔里木河,它们同时找到了我;或者说一个人的性格体质、文化修养也是多元的,就像写山水田园诗出名的王维来到了西北,也忽然写出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佳作。一个人的生命要与山水建立一种联系。尤其是一个写作者,这些山水几乎要生长成为我们生命的骨骼,融进身体的血液,成为我们笔下永恒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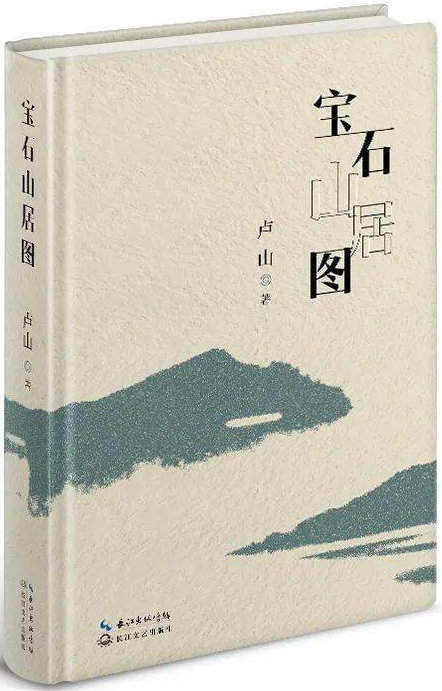
《宝石山居图》卢山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记者:您曾为杭州写下《三十岁》《湖山的礼物》《宝石山居图》(“杭州三部曲”),西域归来之后,是否会再写杭州?如果会,侧重点是什么?会有什么不同?
卢山:我的“杭州三部曲”记录了一个外地青年只身闯荡江南的心路历程,在从青春意气走向三十而立的过程中,杭州这座美好的城市给了我很多馈赠和滋养。湖山的气流潜移默化的影响了那个倔强的少年,江南文化遗产和它的美学辐射力带我走进了诗歌的幽深腹地。三十岁时我游走于这绮丽的湖山,耽搁于一座饱满的夏天,人世间有多少酣畅淋漓就有多少辗转反侧——这几乎就是写诗和生活的秘诀。
即使在去新疆工作期间,我也从未真正的离开江南。我曾告诉朋友,我是把西湖和宝石山装进口袋里带到塔里木的,我要用江南的雨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种植十万株荷花。现在我又再次回到魂牵梦绕的江南,回到苏东坡和白居易诗词里的湖山胜景,但是我觉得自己不一样了,这次我把雪山、塔里木河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带回来了。我在诗歌《归来者》里写到:我回来了!口袋装着塔克拉玛干/手里牵着塔里木河,我回来了/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牧羊人/雪山、戈壁、白杨树/红柳、胡杨、巴扎和麻扎/都被我带回来了/在我的身体里重新组合、生长/接受一场江南细雨的问候/被西湖的荷花与明月抚摸。
杭州是我的福地。在十年前刚到杭州工作的时候,我在散文《遇见杭州》里说“在这座城市,我甚至都不知道脚下的街道究竟通往何处,也不清楚背后流淌着怎样的河流”,虽然像一张旧报纸般迷惘,但我坚信“一个精灵陷入一片陌生的花草,它们还需要彼此熟悉。是的,我和这座城市的爱情才刚刚开始……”
如今“江湖夜雨十年灯”,我的血液里已经到处流淌着西湖、运河和钱塘江,我们的爱情也修成了正果。
感恩江南再次接纳了我。江南永远是我写作的源泉和宝地,我和杭州也会有说不完的故事。回到江南后,对于新的写作而言,我在梳理这几年走过的山河,抚平这些尖叫的河流和火焰,正努力去实现诗人沈苇老师对我的期待:“完成江南与西域并置、水与沙合奏的写作愿景”。
经历了这些年生活的绮丽山水与诗歌的纷乱现场,我曾试图在江南的湖山之间建立起生命的庙宇,在词语的波浪里打捞出一个安然的人世,但今天如果再写江南,可能已经“看山不是山”了,肯定会更多的生命体验和命运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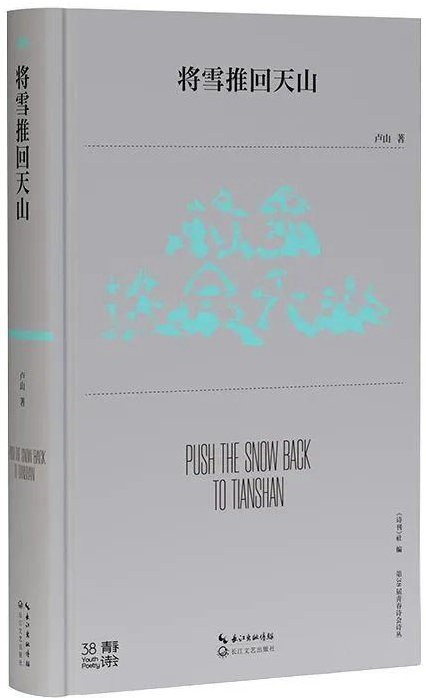
《将雪推回天山》 卢山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记者:聊聊您最新的诗集《将雪推回天山》。其中,既频频出现天山、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自然奇观,又包含烈日、风沙、胡杨、野马等浓厚地域色彩的意向,镜头感特别强。赵思运教授归纳为“奇观化抒情”,这是您刻意为之吗?
卢山:赵思运老师概括的“奇观化抒情”,我非常认同,但我的文本里呈现出这种风格的写作肯定不是刻意为之的。在这里特别感谢赵老师对我写作的关注,十年来一直承蒙他的鼓励和恩惠。他之前对我的写作提出“诗歌地理学”,现在又概括出“奇观化抒情”,非常精准且具有见地。向赵思运老师致敬!
诗人沈苇说:“新疆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
新疆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世界文化融合的地区,面对塔里木的寂静与辽阔、神圣与庄严,我要交出怎样的诗篇来换取我的“通行证”?每天供养着我的是——漫无边际的骆驼刺与芨芨草,苍茫浑厚的盐碱地和戈壁滩,在夕阳下燃烧着的胡杨和红柳,如唐朝遗失的经卷。置身于这样的自然和文化语境中,我大部分的时候变成一条沉默的塔里木河,在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里,内部凝结着来自雪山的巨大风暴。塔克拉玛干里藏着天地的巨大能量,手心捧着一抔沙,捡起戈壁滩上的一块石头,我都能感受到它们那从遥远地心穿越而来的——热烈而滚烫的表达。塔里木,赋予我强大的视野、格局和气场,打通了我身体里的诗歌甬道,释放了一条澎湃的塔里木河。
几年来,我被这些大地的精灵吸附着,燃烧着……可以说,西域大地抓住了我,激发了我,打通了我写作的任督二脉,赐予我大声歌唱的喉咙。西部大地的辽阔、壮美和孤绝,根本不需要你刻意去寻找修辞,也无所谓你添油加醋,你能描述和纪录你看到的冰山一角,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记者:您也提到过,无论西域还是江南,都是李白、王昌龄、岑参、苏轼等先人留下诗篇的地方。中国古代诗歌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卢山:中国古代诗歌是我们这一代代诗人的精神源头和写作富矿,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貌似古往今来优秀的诗人都曾去过西域,也留下了经典的诗篇。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等等;包括现当代的诗人艾青、章德益、杨牧、周涛、昌耀等,不都是在西部写出了生命里最为主要的诗篇?
如何在诗歌里锻造精神的内核,建立一座众神栖居的昆仑山?我在努力修炼诗歌的气场。一个心中没有湖山和家国的人,他的格局是无法和西北大地的气场相契合的。你看岑参的天山,王昌龄的月亮,野蛮生长的塔里木河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些胜过多少个喋喋不休的文学大师啊?
当然,江南也是如此。杭州是半城烟火半城诗,苏轼、白居易、辛弃疾、陆游等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更是我辈写作者不断攀登的高峰。
记者:有人说,诗人常常是孤独寂寞的群体。近期您的作品受到了不少关注,获得了第七届中国(海宁)·徐志摩诗歌奖、2023李白诗歌奖新锐奖,并上榜“浙江青年文学之星·秋季榜”。您怎么看待这种关注?在您看来,当下的社会,如何让诗歌再“热”起来?
卢山:因为各种原因,我也曾沉潜了两三年,关起门来默默写作。写作就是一切,其他的获奖之类的都是一种点缀吧。在我即将迈向不惑之年时,获得这几个奖项,我相信这是缪斯女神对我孜孜不倦、苦心孤诣、无怨无悔的二十年诗歌写作的,一个善意的回馈和鼓励。从中学时发表的第一首小诗开始,写作诗歌已经二十年了,虽没有多大建树和成就,但至少我勇敢的选择了一条路,坚定的走出了一条路。
这些年,我跨越大山大河,闯过风沙狂雨,诗歌是我航行的灯塔、风暴里的避难所,也是我相濡以沫的爱人、生死与共的兄弟,更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和双亲。我写故我在,我写所以我得以我是我。荣耀是短暂的,而写作之夜是无比漫长的。这是一个开始,也只能是一个开始。谢谢诗歌,让我这个笨拙的乡村少年,得以和大家同行!
最后用伟大诗人博尔赫斯的几句诗歌和大家共勉:“众神给了其他人无尽的光荣,铭文、钱币上的名字、纪念碑、忠于职守的史学家,对于你,暗中的朋友,我们只知道你在一个傍晚听见了夜莺。”愿以缪斯的名义,“夜莺的歌声”与我们永远同在!
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今天,互联网、自媒体多元化传播的语境中,人们似乎已经不需要真正的诗歌了,因为音乐、电影、游戏等可以消解精神的贫乏,甚至网剧、短视频等都被认为是精神生活。真正的诗歌是有阅读门槛的,也是在筛选自己的读者,所以让诗歌“热”起来确实有难度,好像在今天也不现实。
我也听到很多抱怨,今天的诗歌怎么读不懂了,是诗人太高深,还是读者太浅薄?读者反映,现在的一些诗歌,有的凌虚高蹈云里雾里,有的废话连篇不知所云,结果只能让人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久而久之,给诗歌的传播建起了一座座围墙,而诗人们也都住进了遥远的孤岛。当下,诗歌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仿佛只有诗人还在读诗、写诗,诗集大多在诗人之间互赠,制造小范围的“孤芳自赏”,形成了某种狭隘的“闭环传播”。
诗歌的式微是各种原因吧。时代的大背景大环境不说,诗人的创作风格、题材以及向大众敞开的通道等,读者文学素养不高、内心浮躁等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真正能坐下来读诗的人好像也不多了。但不管乱云飞渡,还是安静地写、认真地写,写下去,就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