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光汉|金龙贺岁·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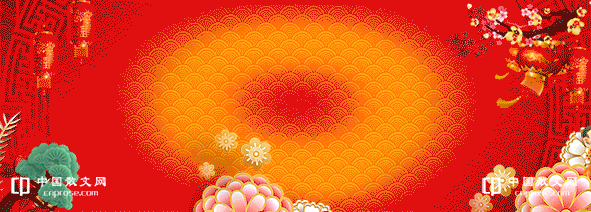
闵光汉|金龙贺岁
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作家简历
★
闵光汉 男,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学学历。散文《君子之花》获第三届“三亚杯”金奖。
君子之花
入秋以后,天气转凉的同时草木也加快了凋零,曾经的大红大紫不知到哪里去了,剩下的似乎只有墨绿与枯黄。午后在楼下的园中漫步,走到临江的一条小路的转角处,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走近一看,只见几片绿叶簇拥着一丛金黄的花蕊。这不是桂花吗?走了没几步,又是一股香味,又是一棵桂树。转完大半个园子才发现它们固然分散于四处,却也大多三五成群,难怪近来每天早晨敞开门窗,总有一股氛芳的气息,伴随着略显凉意的微风飘来,让我混浊了一个夜晚的头脑有了几分清新。
在这个有着近千人的园子里,我也住了约十年,尽管每年的秋天都闻得到桂花的味道,却总是不当回事,当然也就不曾留心过它们的数量的多少。桂花生于桂树,桂树与桂花是母与子的关系,很多人虽乐见桂花,却不屑于桂树,原因大约是桂树不但没有“帅哥”高大的骨架,而且也缺乏“伟人”傲世的风姿,在几百棵乔木的“王国”中,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一群”。园中的银杏虽不足十棵,却大多围以护栏,植于空旷的中心地段,每一棵都将笔直的身躯傲岸地矗立于白云蓝天,仿佛古人所谓“孤映之高霞,独举之明月”,令那些向上仰视的眼睛里溢满了渴望。即便是与桂树相邻的朴树,初看固然憨态十足,细细打量却让人诧异枝干的婀娜与姿态的优雅。这样看来,形象不佳的桂树为人所疏忽也就在情里之中了。我每日漫步于园中,看来看去的,也不过是草木中的“帅哥美女”而已。
园中茉莉的命运与桂树也有些类似。江南水乡的民歌《好一朵茉莉花》,为无数痴男与怨女所倾心,那调子从歌手的双唇一出口,旋律的涟漪便浸润了“粉丝”们早己一动不动的眼睛,而那软玉般的音色所氤氲的袅袅气息,更使得那些年轻的心悸动不己。然而,茉莉的花蕊既不硕大饱满,色彩也不娇艳热烈,实在难以牵挂住人们目光的依恋。但有着淡雅幽香的茉莉花,却把花期由初夏的温馨绵延至了深秋的嫩寒,于是一年中近一半的光阴也就有滋有味了。与茉莉花相比,萌发于初秋的桂花却几乎不露痕迹,不但视之既乏形,而且嗅之亦寡味。但随着中秋的临近,它们的花蕊却日益由稀疏而茂密。当细微的花蕊从叶下绵延到叶上,点状的金黄色便缀成了形状各异的碎片,原本阔大的墨绿色叶片似乎狭小于一双看不见的手的收敛。比茉莉花期短暂得多的桂花,不但开在枝头时灿烂辉煌,即便凋零于枝下也好似给泥土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当人们从枝下走过的时候,便在一个仿佛上下缀满了黄金的世界里恍惚了自己的双眼。
也许,我今天如此关注桂花是有原因的。今天,我恰巧读到了《论语正义》中一段孔子语录:“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心里有所触动,便在空白处写下了眉批:“王阳明之‘知’,实源于孔子之‘文’,而‘行’则与孔子一脉相承。‘行’重于‘文’,是由孔子所奠定的‘君子人格’,‘知行合一’,便是‘躬行君子’。王阳明以其‘心学’回溯到了孔子的初心”。正是在写下了这段话后,我才到园子中散步,而在散步之际才从一场厄梦般的混沌中清醒起来:桂花才是“行”重于“文”的花中君子。
说到《论语》,说到孔子,便难免会想到“七十二贤人”之一的闵子骞。据家中的那本《闵氏宗谱》记载,闵子骞为我的“七世祖”。在“孔门四科”中,“德行”居首,颜回排在第一,闵子骞紧随其后。闵子骞以一已之寒,成全家之暖的举动,温暖了天下无数中国人的冬天。其实,不只是他的“孝”常人很难做到,就是他的“廉”也未必是“达人”所能达到的。他曾是为任一方的高官,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却终因不满于官场的贪婪与腐败,而远离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的家园,携妻负子,拖家带口,到齐国做了一个教书为生的“臭老九”。也许,只有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标准,才能衡量出闵子骞这一举动的意义。闵子骞去逝约一千五百年后,在济南担任“秘书长”的苏辙撰写了《齐州闵子祠记》,而他远在异地的兄长苏轼则以“苏体”作了书写,然后立碑于祠。此后近一千年内,闵子祠多次重修,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仍大致保持着原有的风貌。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闵子祠却被当作“四旧”而捣为了废墟。多年前我曾到过济南,想一窥被毁灭的破败,然后在长着青草的坟前流下几滴眼泪,也算是对祖先的祭奠。但到了济南,便不免把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等名胜转转。济南还是辛弃疾与李清照的老家。我一直以为,苏轼、辛弃疾、李清照之于宋词,相当于李白、杜甫、王维之于唐诗,足以代表宋代文学的成就。苏轼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其时代特征反倒不那么突出。倒是辛弃疾抑扬顿挫的长短句,让人联想到了殷墟青铜器上那些饕餮纹的狞历。诞生于血与火的华夏先民,也曾拥有不屈的血性。将辛词与唐诗相比,李白“壮”而不“悲”,杜甫则“悲”而不“壮”,唯有“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才将“悲”与“壮”在一件作品中融为了一体。辛词所以令人绝倒,正是由于它在国破家亡的关头,将刚柔相济的“君子人格”在金戈铁马的战场再一次作了淬炼。更加足以与唐诗争奇的是,身为弱女子的李清照,虽然孤身流落于江南,竞然也以“生当作人杰”的雄心,写下了那么多流传千古的名篇。与李清照相比,柳永有其“俗”而无其“雅”,秦观则有其“雅”而无其“俗”。宋词中,将“雅俗共赏”发挥到极至的唯李清照一人。东方女子所独有的“婉约美”,经李清照将“写意”化为了“工笔”后,才第一次“惊艳”世人混浊于麻木的目光。“金陵十二钗”,哪一个不是李清照的“转世”?从她们纤笔下流转出来的,正是李词低徊的余韵,绕梁的愁绪。李词无疑为《红楼梦》的今生作足了前世的准备。然而,这两位词人的故居都是不久前才完工的仿古建筑,那样一种经反复涂抹所堆砌的油彩的浮华,却不对我的味口。于是,我独自来到了位于城郊的一座村庄内,但见一棵满是枯枝败叶的古树,歪歪斜斜地立在一堵乱砖破瓦前。那时的闵子祠仍处在漫长的“重修”中而“不对外开放”。从“五四”时起,“孝”即饱受攻击,以“孝”闻名的闵子骞,自然会被一只只铁拳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几年后的“批林批孔”,更使得他的老师遭遇到了举国上下的声讨。不过,近些年来不但老师转了“运”,作为学生的闵子骞的祠也己修缮完毕,并且还重新开放了。
也许,为了纪念他我明天就应该来到他的墓前;但更有可能,仅仅因为无从目睹苏氏兄弟的那块碑而永不再去。然而只有我自己明白,内心无形的怀想,胜过了身外有形的丰碑。平凡而普通的闵子骞,也仿佛这秋天的桂树,既不能以秋叶与春柳争绿,更难以瘦蕊与肥桃竞红,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却总有一泓月光的碧玉,从墨色斑驳的天幕的缝隙流泻而出,于是桂树的枝枚叶叶也笼罩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翡翠绿。而那一簇簇隐隐约约的金黄,也仿佛秋雾般弥漫着阵阵醇香。闵子骞不正是一簇这样的君子之花吗?
风雨木兰山
六月的第一个早晨,我利用周末来到了位于市郊的木兰山。下车后不久,就飘起了雨。这时,天气不仅凉快了,而且空气也湿润了。抬头向上仰望,木兰山在蒸腾的云雾中模模糊糊。云雾之于木兰山,并不只是增添了它的神秘,也赋予了它灵气。木兰山海拔虽不足六百米,林立的山峰却错落有致,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金顶”所在的主峰,更是一柱擎天。或许,正是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山势,佛道二教才在此既彼此疏离,又相互呼应。木兰山寺庙大多兴建于隋唐,鼎盛于明清。每当“庙会”之际,湖北周边数省的“老表”、“幺妹”们便跋山涉水,云集于此,由山脚而山顶一路烧香敬佛,从他们手掌上升腾而起的烟雾,曾经弥漫了木兰山的一方天空。据《木兰山志》记载,当时香客之多,不下百万。即便是到了解放前,不乏“香客”的木兰山也曾店铺栉比,有着“小汉口”的美称。不过解放后“信教”被视作封建迷信,木兰山也为人们疏远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七宫八观三十六殿大多未能逃脱“四旧”的厄运,一千余尊神像或被“斩首”,或遭“车裂”,仿佛重新演义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浩劫”。好在.“文革”结束以后开始了“重建”,不但庙宇大多得到了修葺,而且新塑的神像也己各就各位了。
我到的第一站是位于山脚的那座桥。桥只是一座小桥,桥下的河床上却有溪水流淌。桥的两端,立着若干白墙黑瓦的房屋,顺着河的两岸排开。因了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木兰山不仅多了几分空灵,而且也有了几分烟火气。然而,雨中却不见一个人影。我的内心变得空荡了起来,于是加快了上山“朝拜”的脚步。一条公路由山脚蜿蜒到山顶,乘车也不过几分钟。但我既然自认是“香客”而非“游客”,就多了一份虔诚心。于是便远公路而近“古道”。一边走,便一边想起在五台山“朝拜”的经历。那是十多年前,在五台山菩萨顶的大雄宝殿的门外,我曾目睹一个来自西藏的汉子,一步一跪拜地沿一百零八级台阶匍匐而上。那是一个临近黑夜的傍晚,游人散去后的寺庙外已显得空寂,一轮西沉的夕阳将透过“火烧云”的光斜斜地洒在他赭红的袈裟上。一群白鸽忽然从寺庙的屋檐上腾空而起,在半空中缤纷着几十双翅膀。不可思议的是,竞然有一根翎羽如雪花般由上而下地飘逸到了他的身上。汉子止住他的攀援,以双唇噙住白羽,然后继续向前。那一刻,雪山与草地似乎在他身后遥远,红墙与碧瓦则在他的眼前俯近。时间之水被空间凝固为冰,屏住呼吸的我,一边注视着他一起一伏的身影,一边侧耳倾听从殿内传来的《南无阿米陀佛》的乐音。众僧光润如琉璃的合唱,也仿佛基督教教堂响起的美声,同样歌颂着天堂般的圣洁与光辉,伟大与不朽。神情恍惚的我,几乎迷乱了自己的脚步。现在,我在木兰山古道的青石板走了不过百来米,位于山脚的第一座寺庙准提阁便出现在了眼前。尚未进大雄宝殿,就有诵经声与钟鼓之声由传来。
我立于大雄宝殿的门外,但见释迦牟尼塑像的两侧分别立着几个身着袈裟的僧人,他们敲钟,击鼓,诵读着谁也听懂的“嗡嗡”声。于是,钟的金声,鼓的木声,人类嗓门的肉声,将清脆与浑厚,绚烂与冲淡,铿锵与柔软叠加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僧人们还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而折腰俯首。大雄宝殿门槛内,有一对中年男女也不时双膝落垫。他们是木兰山村的农民,男的在外赚了几个钱,奈何因近亲结婚产下的唯一女儿竞有些疯颠,每日在村里摇晃着幽灵般的身影。这次以千元做此“佛事”,意在为女儿祈福。当今做“佛事”者寥寥,何况“古道”己因公路修到山顶而废弃,准提阁也因此形同虚。准提阁位于“古道”旁边的低坡上,而“古道”为人们朝拜的必由之路,它作为木兰山“第一庙”,其地位之重要,不容小觑。准提阁始建于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是那一年,北宋的两位皇帝被掳,北宋也因此灭亡。一破一立,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吗?
离开“准提阁”后我继续沿“古道”而上。走了一会儿后,见一石桥旁立一巨石,石上刻有“好汉坡”三字。从此处起,山势由平缓而陡峭,身下的双腿也仿佛由硬朗而疲软。攀登约数十米后,见一古寺立于道旁,寺门上“川心灵官殿”五字赫然凸显。殿门紧闭,寺旁一土屋的门倒是敞开着,我尚未进屋,就有一阵旋转的风雨将几片落叶甩落到了土屋斑驳的墙壁上。靠近正面墙壁的一张床边,蜷缩着一副身着袈裟的老头的身影。他似乎己经进入了睡眠,恍惚于自己的梦境,完全没有觉察到一双陌生脚步的进入。我轻声在他身边唤了两个字:“师傅”,他这才将埋入胸脯的头抬了起来。这是一张核桃般的老人的脸。我拿了一个方凳在他旁边坐下,看着那张脸上的写着的岁月。短暂的寒喧过后,老僧便为我答疑解惑:
“川心灵官殿”之于宗教,类似于“公安局”之于人间,如果说“准提阁”为扬善之处的话,那么“川心灵官殿”则为惩恶之所。群峰顶上的宫观依山而立,宛如天宇之群星。木兰山寺庙三个不同的层级,分别象征着人间之苦、地狱之恶、天堂之尽善尽美。木兰山古道由缓而陡,则预示着西方黄金世界之超越高远。
环顾这间几乎仅仅只能容纳一张床的小屋,我诧异于他的处境。他却坦然道:今生所以受此煎熬,实由于前世作孹所致,乃罪有应得,不应有非份之想。我对他的身世一无所知,但他以“罪孹”定性自己的人生却令我诧异。但无论如何,他那颗为了善而受苦的心灵,却并不多见。按照世俗的标准,老僧的人生是失败了,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有可能是一个失败者,而一个“成功者”反倒可能输掉他的人生。
难道与这老僧厮守终日的仅仅只是“苦难”吗?我转身望着门外那片的槐树林,再次与“老僧”聊了起来。这时,他的脸色不但变得开朗了许多,甚至有了几分怡然自得。据他说,在那些晴朗的日子里,呼吸到鼻孔里的空气都是香甜的,尤其是到了中秋时节,阵阵秋风便把浓得化不开的槐香漫了过来,这时就觉得清气上扬,浊气消散,而出窍之魂灵,也在槐花的芳香中随风荡漾……
没有人知道,宗教之“善”与自然之“美”,是如何以一只左手与一只右手将这个沦落于深渊的人拯救。其实,“木兰山文化”,就在于这二者的融合,人们来到这里,一面欣赏风光,一面思索人生。但真正能够悟透“木兰山文化”的人又在哪里?“游客”取代了“香客”,轿车的车轮取代了人们的双腿,到山顶几乎无须走路了,但无须付出的获得总是享受对劳动的否定。“古道”的陡峭险峻是绕不开的,没有这样的“苦难行军”,人生就缺少了战胜困苦的“高峰体验”。
沿着“好汉坡”继续往上登数百级台阶,“华严阁”便在风雨中依稀可辨了。在“华严阁”之上为“天街”,“天街”之上更有“金顶”。只有抵达到了“金顶”,一部建筑的交响乐才在高峰中终结。再加一把劲,我就能够置身于群峰之巅,从“绝顶”之上,俯视“众山”之小。然而,隐约在远方的雷声却由“嗡嗡”变作“轰轰”了。这时,我的身后传来了“老僧”的那拉长嗓音的呼唤,虽然听不大清楚意思,却能感觉到那一份急切。显然,一场骤雨正在酝酿中。于是,我转过身去,由上而下,一步一台阶地返回到了山下。刚到山脚的那座小桥旁,风雨便猛烈起来,我不得不赶紧乘车返回市内了。
玉 兰
缭绕的烟雾依稀缭绕着天鹅湖古木的参天
恍惚于昨夜梦境的睡美人在今晨的花园惺松着眼睑
当这个春天的阳光把那些灰暗的面庞涂抹得金黄
传说中的仙子就在不见一片绿叶的梢头踮起了脚尖
天空以它蔚蓝的透明隐匿着神秘隐匿着深邃
岁月将一滴冰川的水流淌成了千万条河流的潋滟
无数人类的仰望穿越阳光和云层所嶙峋的花岗岩
只是为了搜巡远离人间的仙境以一步登天
然而,小仙女们却痴迷于人间而遗忘了九天之上的家园
春天,春天,这个迫不及待穿过冬季而到来的春天
将整个星际的美全都在地球的花季中轮回
一只小提琴的弦乐由开放的峰巅盘旋至凋谢的深渊
另一把长号的管乐从黑暗的幽谷升腾起缤纷的光焰
一丝花香浮沉在了两片花瓣的褶裥
另一缕微风在花蕊中氤氲着细语轻言
被薰醉于枝桠的光滑与柔软的小仙女们
将那纤细的身段层叠为了重瓣的妩媚
于是,曾经的天鹅湖不再是天堂中唯一的伊甸园
当花蕾绽放为花辮
人间的玉兰也就转世为了天堂里的天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