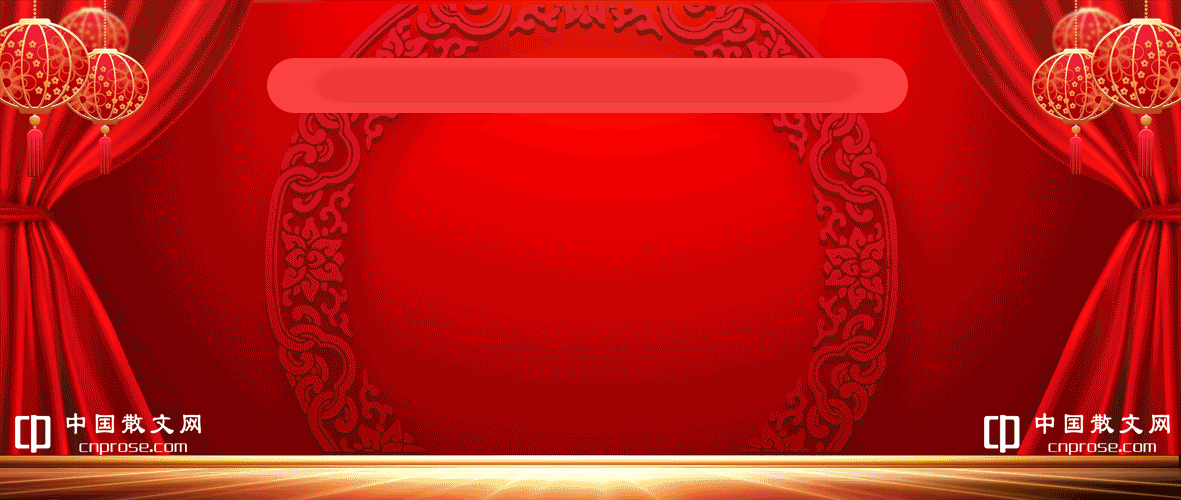【2023国庆特刊丨当代作家 赵敏 作品展】

艺 术 简 历
赵敏 生于上世纪7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教师。
作 品 展 示
端午与“守常”
端午紧跟着夏至,顶着大日头,火辣辣地扑面而来。
2023,河北省的中考作文题目《守常》,争议颇多,我倒觉得很有点意思,就借着端午说说这“守常”吧。
朋友送了粽子,包得小巧精致,碧绿的苇叶,有棱有角。嘱我泡在水里,味道更好。剥开苇叶,先有清香扑鼻——苇叶、糯米裹着着蜜枣红豆,接连吃了俩,凉凉甜甜糯糯,心下满足“嗯,过节了,守着习俗循着惯例,觉得很圆满。
过节必要应景,吃就是一宗。像初一的饺子中秋的月饼,非要和“节”搭配,才是那个味儿。倒不是这天的粽子饺子月饼,平常吃不起、吃不到,而是因为,这日子里边有着情怀、情结,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老礼儿、老规矩,这节和这吃,也是“守常”了。
说到“守常”,便由不得有人会想到食腐不化,会想到抱残守缺、冥顽不灵等等。闯将的情怀,总是激进的,总想打破常规的。年岁渐长越来越能理解:时代大潮泥沙俱下,总是要破坏点啥,打倒些啥,似乎才能摧枯拉朽、勇往直前。
就拿过节来说,“没味儿”这样的话似乎习惯挂在嘴边,所以传统节日,往往不如洋节热闹,五颜六色的锡纸包个苹果,批发处理的玫瑰,不知从何时起,拼凑出不伦不类的欢乐气氛——浓浓的莫名味儿。
你要真问,过节到底是个啥味儿?我相信很多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其实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的宗教化不同,更多的意义是:这片土地的人,生生不息地通过某种仪式与天地、自然的交流与沟通,这个“常”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这个“常”就守不得吗?
譬如今日端午,朋友圈各种强调,不能说快乐,要“安康”。我们且不说因为诗人,端午应不应该“快乐”,单从“Dragon Boat Festival”这个词,你就知道,这节凭啥不能快乐!守这个“常”也是快乐的!
我生在北方长在北方,记忆中春节后最盼的就是“五月节”。阳光与生机同时蓬蓬勃勃,口腹之欲总是过节最大的追求。北方不产糯米,包粽子用的是黄米,最古老的“黍”。我妈在大盆里泡上金灿灿黄米那天,我就开始兴奋——快过节了。
我妈包的粽子,板板正正,个儿大饱满。地上放一张方桌,我妈坐在矮凳上,身旁是提前泡好的黄米、苇叶、马莲、大枣。几片苇叶平铺两层,折成锥形,捞一把泡软的黄米,攥干按紧实;从桌下另一个盆里摸出几粒大枣,塞进黄米中,再攥一把黄米盖住;苇叶折过来,包住米,裹得紧紧;用晒干又泡软的马莲草捆扎结实,一个四个角的鼓胀饱满的粽子成了。我在这时候也跃跃欲试,但是不管是叶子还是米,都格外不听话,散了一桌子之后就会被我妈唠叨着,赶到边上去,我这跃跃欲试的目的还有一个,趁机摸几粒大枣塞嘴里。我至今没守住这包粽子的“常”,是一大遗憾。
过节这一天,必须早起,早到可能刚睡着,便被村里四面八方的呼叫声喊醒——“薅艾(我家乡说麦)蒿去喽!”这一喊,大人孩子,男的女的,都跟挖宝一样,呼啦啦齐刷刷,摸着黑上了山,顶着星星、趟着露水,不管不顾。孟仲交接的夏夜,如果采得满怀满抱的艾蒿,那必是风调雨顺了,孩子大人的喧闹背后,是一年共同的喜悦和希冀。大人还要嘱咐要用山泉水洗洗眼睛,不闹眼病。
黄米粽子、阳光下带着露珠的艾蒿,飘出自然给予的,没一丝工业味道的清香;家家户户,屋檐下桃枝吊着的五彩纸葫芦;呼朋引伴的孩子,胸前坠着丝线的荷包、手腕上系着的五彩绳,将这夏日的节日渲染得一派欢乐。
应该是值得乐的。春耕早毕,锄过一遍的黄土地,齐刷刷的庄稼苗,也表示得像天地致以感谢,用勤劳的人们最朴实的欢乐,表示一代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守着这份最真诚、最质朴、也是最要紧的“常”。
如今身在异乡,城市没有黄土地、没有家家户户门前艾蒿飘香的真诚、质朴。庆幸的是孩子放假直接回了姥姥家,我昨天电话拜托我妈,务必今早喊醒她,去采一把山里的艾蒿,也算替我“守常”了。
窗子上的牵牛花
阳台的窗子上,一朵牵牛花,俏生生地开了。
紫色的花瓣,颤巍巍如同蛋清,吹弹可破——这样的词儿,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给牵牛花用上,如同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牵牛花会开在我的窗子上,它来得太不经意也太意外。
今年夏季酷热,我阳台的花儿死了七七八八,只有北阳台的黄瓜,占尽了炎炎夏日所有的风光。虽然家门之外别有风景,可是禁不住灼灼的热啊,哪里有触手可及的绿,能让你瞬间平心静气,更何况,一伸手还能摸出个嘎嘣脆的嫩黄瓜!
尝到第一口自己种出来的脆爽后,我便热衷于各种播种:苦瓜、丝瓜、豆角、辣椒......小有收获,大多失败,却也乐此不疲。偶然发现一包赠送的牵牛花种子,便顺手塞几粒进了阳台边上的空花盆里,浇花时也偶尔给它们一点水喝,漫不经心的。
牵牛花太普通,小时候家乡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篱笆上,一片一片的哪哪儿都是。蓝紫的,粉白的,直往你的眼睛里扑,躲都躲不开。它原本也不是需要人刻意精心的花儿,野生蔓长,蓬勃恣意,和露水一样,湿漉漉沉甸甸地旺盛到深秋。没有人会在家里种一棵牵牛花,所以我就是那么漫不精心地种下了它的种子——我以前竟没有想过它也会结出种子。
至于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一点点爬上窗子,我几乎没有留意。我忙着给蓝雪花剪枝,忙着种下了旱金莲,酢浆草,忙着扦插叫玛格丽特的小花花。甚至我的黄瓜丝瓜苦瓜辣椒们终于露出颓败的枯黄,我也没有认真想过,去看一看已经悄悄爬到窗顶的藤蔓。
它太不出众,叶子貌不惊人,沿着角角落落的缝隙,一点点地用力,如同攀岩一般地努力寻找、落脚、抓牢。我想它如此用力,一定是拼命寻找太阳和自由的空气吧。它本属于田野:阳光的狂野田垄的自由;空气的自然泥土的芬芳;鸟儿的鸣唱牛羊的呜咽,狂风暴雨耐它何?它、它们依然会在某个清晨齐刷刷地吹响色彩艳丽的喇叭,尽管这生命之乐只有一朝,不要紧,第二天,又是一拨!
阳台真正是委屈它了。我如此不经心,错过了它的成长,错过了一季生命的青春时光,如同幼年时,从没经心热爱过一朵牵牛花。清凉的傍晚,千百计的花苞中间,我随意地摘下一把,一个一个地放在唇间,一吹,“噗”,一个皱皱巴巴的小喇叭“开”了,随手一扔,继续吹下一个,直到我嘴巴累了,也烦了。没有一个牵牛花的同伴曾因为我的轻慢而放弃第二天清晨的绽放,如同今天清晨,并不因为阳台的不适宜而放弃的那一朵,它就俏生生地绽放在窗子上,对着外面的蓝天白云,阳光秋风,滴滴答答地吹响它生命的小喇叭。
我仍然记得,家乡的所有牵牛花,统称为“打碗花”,高的矮的红的白的大的小的,都叫“打碗花”。我曾经悄悄地把它带回家,藏在碗柜里,发现它并有能把碗打碎的本事,好天真的我,好善良的花儿。
今天,此刻,它就开在我的窗子上,我们彼此注视,如同——久别重逢。
种瓜得瓜
我迷恋种植,甚于迷恋养宠物。
梁实秋曾感叹爱花容易,也不敢自称“花痴”,既无良田,又无体力更无闲暇,想拥有一间花房,谈何容易!更别说如鲁迅先生,吐两口血,恹恹地由侍儿扶着到阶下看秋海棠。富贵闲人永远是相生相伴。
当然,梁实秋先生可以感叹,鲁迅先生可以贵恙,我都没资格。我小时候是极其厌恶耕种劳作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苦断断是受不住。倒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或者“草盛豆苗稀”,让我错觉在物质条件和技术上都比较不那么严苛,于是斗室之内、方寸空间也让我生出妄想来。
还有一个原因,我养的猫和狗在我身边渐渐老去,让我生出对生命无常的无奈无力与悲凉。再看草木,尽管“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但总还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仿佛生命可以复制。心里生出与生命轮回做见证的喜悦,似乎可以聊以自慰。奢侈一点还可以发点类似“白发黄花相牵挽,付予旁人冷眼看”的无病呻吟。
我总是满怀希望播种,或者买来小苗,也不是没有收获,阳台飘窗,还是色彩不断的。可是没有阳光雨露和风细雨,总是不能有姹紫嫣红开遍的盛大辉煌。为了不辜负我,花儿们也大都会勉为其难地开上一两朵,傻一点的开一大片,那会让我搜肠刮肚想赞美之辞。
几乎所有的花儿都熬不过夏天,我以前是难以想象“开到荼蘼花事了”,罪魁祸首与夏天有关。这么旺盛的阳光丰沛的雨水,如何能就花事了了?几次收获一堆空花盆之后,认命罢!这也如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总在初起时,要不怎么有“人生若只如初见呢?”若为辞树花烦忧,倒是辜负了当初种花的心。
于是我又尝试种点黄瓜辣椒之类的蔬菜,以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撒种就能种出个阳台陶渊明。种子买了很多,土也买了很多——土是需要花钱买的,这真是完全对儿时不喜稼穑的背叛,甚至肥也要买,这就不能详述了。
总之,几番折腾,我在阳台上收获过几条黄瓜,几条丝瓜苦瓜——辣椒和苦瓜收获得最多,我想大抵世间总是苦辣易得的缘故吧。大多数种子要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泥土里,要么长出小苗没几天,逐渐萎蔫继而夭折。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背诵陶渊明,我种的是诗意——自我安慰总是最有效的涂抹失败的方法。
某天早晨发现小区门口一群附近村里的老人,脚前堆着自家地里产的黄瓜辣椒豆角茄子……一块钱两块钱几块钱,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我做了一件纯粹败家的事。
种瓜并不一定得瓜。尽管心血,并不曾少用一点,投入也超出几倍,如果计算成本进去,那是真真儿的傻子!种瓜得瓜,那也得在有地且不是盐碱地的前提下,那种下去的瓜种子也不能是某某地产的假种子,这些都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前提啊!更不要说风调雨顺加持了,丰收的喜悦需要多大的造化,多完美的成全。
我阳台外的小苗又在迎风招展,我已不再执着希冀丰收。我种的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种子,也不曾辜负它们生长的每个瞬间,至于收获大都是苦瓜与辣椒,那也不是我的错,我终究无愧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