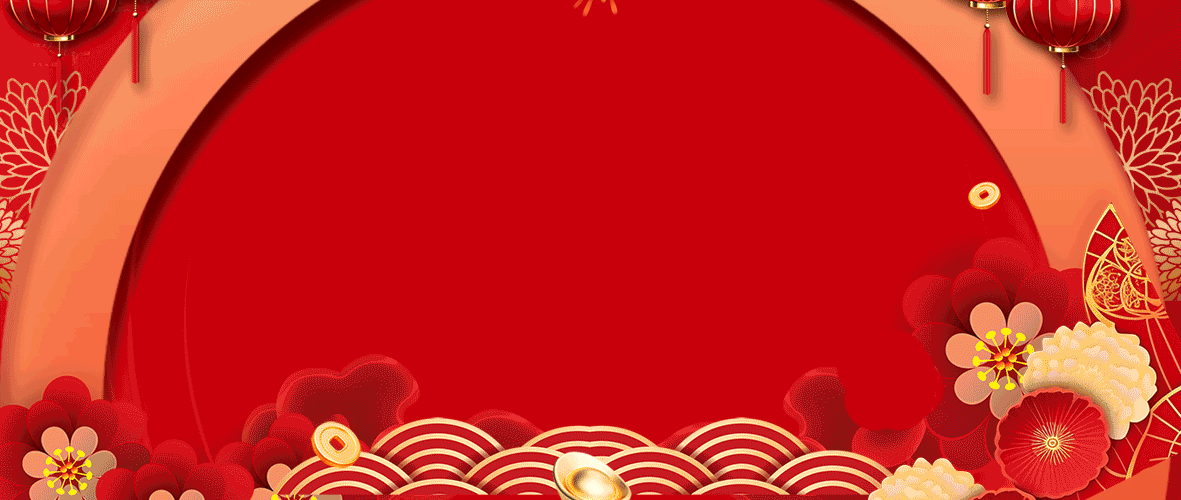【2025新春人物丨当代作家耿清瑞作品年刊】
2025新春人物
当代作家 耿清瑞 作品年刊
2025新春人物简历
XIN CHUN REN WU JIAN LI
耿清瑞 大学学历,山东金乡人。历任中学教师、检察官、县司法局副局长、县委610办公室主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安监局局长、县住建局局长,现任金乡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省级以上报刊及网络文学平台发表散文200余篇,荣获山东省首届检察文化“金徽”奖、第四届“三亚杯”当代华语文学大赛金奖和“2024年度最美散文奖”等,出版《耿清瑞散文小说集》和散文集《那一抹永远的乡愁》、《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堂屋阳光》。
作 品 年 刊
ZUO PIN NIAN KAN
秋夜里的突围
秋夜,似乎更像秋天里枯黄而杂乱的藤蔓,在睡不着的时候总是悄悄地缠磨你、撩拨你,让内心深处那条本不想触摸的弦断断续续地颤动着,甚至鸣响着。
在年轻时的那些记忆里,记得有好些个秋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种被命运所围困、所压抑的感觉滋生出一种杀出重围的欲望和冲动。其实,命运的藩篱哪有那么容易撞破?有人终起一生竭尽全力也未必能够冲出牢笼。好在那时年轻气盛,毕竟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连突围的勇气都没有,何谈冲出命运的桎梏?
记得那年的深秋,夜已经很深了,深得有些空洞,有些望不到底。而周围似乎都睡熟了,除了安静还是安静,安静得让人无法入眠。辗转反侧了好久,终于听到了动静,刚刚醒来的秋虫在窃窃私语。我还真的有些怜悯它们,因为很快就会霜寒露冷,估计它们的好日子也不多了,它们是何等的留恋啊!或许在作最后的道别吧。可那时想,做一只秋虫也很不错,虽然它们的生命简单而短促,但没有希望也便没有了失望,没有欲望也就没有失落,省去了诸多麻烦,也省去了诸多苦累。按说那年我才是高二的学生,正值异想天开的年龄,不该这么沮丧,更不该这么悲观。或许因为即将面临的高考,感觉到自己前途堪忧;或许因为这学期的几次数学考试都未达到老师的预期,总被老师认为“瘸腿”;也或许因为无尽无休的繁重劳动,感觉不到人生的半点希望和快乐。这些竟让一颗年轻而活泼的心变得多愁善感。我在暗夜里睁大眼睛,窗外漆黑一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虽然白天的农活很累,甚至感到腰酸背痛,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儿困意。抚摸着肩膀上被拉砘子的麻绳勒出的血印,还有手掌里被铁锨杠磨破的血泡,心里五味杂陈,真的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土里刨食。眼看高二的秋假已接近尾声,再有两天就要开学,可一地的农活还有很多很多。想着年迈的父母,感觉自己愧对他们。
类似这样的秋夜还有很多,有时睡不着就干脆起床出去走走。记得那个初秋的夜晚,燥热而郁闷。当时又停电了,如豆的油灯燃起一片昏黄的光晕,让周围的空气越发显得沉闷。一个人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又心事重重,既有对个人前途的担忧,也有对未来的迷茫,还有青春的孤独和失落,于是叫上发小小胖一起来到村外。走在田间小道上,秋庄稼还在旺盛地生长,夜色下泛着浓浓的黑绿,两边的玉米秸秆又密又稠,有种沉重的压抑感。这平原地像深邃的海洋,一眼望不到边际,如果在哪里能找个高坡,登高望远,直抒胸臆,或许还可透透气,抑或还能心旷神怡。但跑了好多路,庄稼连着庄稼,层层叠叠,密密麻麻,也没找到一处高坡。小胖不解,问我找那玩意干嘛,还不如掰个棒子找地方烧着吃。我内心好笑,我说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都这么胖了还吃?他说那你心里在想什么?找那高地又干什么?想凉快还是想看远处的东西?其实已经很久了,我俩总想不到一块去。忽然想起曾经学过的课文《陈涉世家》,脑海里竟涌出那句“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不过,转念一想,也难怪,人家小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他常说,种好地,多挣钱,娶个好媳妇。人各有志,勿施于人啊。
还记得一次,也是秋天的夜晚,就是高三毕业的那阵子,跟着大哥骑自行车去济宁抗生素厂买药。大哥在村里开卫生室,一箱药批发价比镇上药店便宜10块钱,一次可带两箱,车票钱够路上的饭钱,一趟可赚十几块钱。早晨6点动身,夜晚12点回来,往返260里路。也去过河南商丘,先骑自行车到单县,然后再坐车去商丘。大多顾不上吃中午饭,到下午回到单县再吃午饭。大哥很大方,我俩多是喝羊肉汤吃壮馍。他说挣钱就是为了花钱,光挣不花,掉了白搭。骑车回来时也是夜晚,毕竟秋天了,凉风拂面,虽有些许的惬意,可心里依然七上八下,担心自己高考的成绩不够理想,担心能否被心仪的学校录取。那种忧虑,那种无奈,那种郁闷,一如心上压了一块石头。可能自己给自己赌气,双脚快速狠劲地蹬着脚踏板,感觉口腔里涌出一股热热的气体。自行车在黑色的柏油路上飞奔,似乎要穿过浓浓的黑夜,撞开前方命运的铁幕。
后来在等待毕业分配的日子,更要捱过一个个难熬的秋夜。那天在城里找人打探分配的消息,一整天也没着落,心里忐忑不已,直到傍晚还独自在城里大街上踯躅,看到街旁楼窗里透出温柔的灯光,眼睛里竟然有些湿湿的感觉。离开城区返程回家,肚子突然叫了,才想起早晨出来,一天都未曾吃饭。骑行近三十里,透过夜幕隐约看见公路东边有一座大院子,那是本镇的一处中学。忽然想起我初中的老师正在那里担任校长,就突发奇想地过去找他,看能不能临时代个课,也算找个临时工作,至少可挣点零花钱。于是拐下了公路,摸黑向那座学校奔去。那是条小路,走着走着前边没有路了,一条宽深的沟渠挡住了去路(现在想应该是走错路了)。好在沟渠的坡度不大,沟底也没有水,我先把自行车放下去,人再下到沟底,然后扛着车子爬上那一面坡。过了沟渠,又路过一段坑洼不平的土路,终于来到学校大门前。可学校里黑灯瞎火,只有门岗亮着一只白炽灯泡。门岗看见我,惊呆地愣住了,我这才想起刚才过沟渠时弄了一身泥土。赶忙向他解释,他立刻变得热情起来,说学校放农忙假还没开学,校长及老师都回家种地去了,你晚一星期再来吧。还说,你回去不用爬沟渠了,往北走有座桥可以通过。我慌忙道谢,失望地往回走,因为心里堵得慌,所以也就忘记了饥饿。但一个星期后我并没有再来,因为县里分配了工作,我到镇中学上班去了。
或许没人能够理解一个中学生当时的心境,也或许没人能够体验一个农村孩子那种左冲右突却又困顿迷茫的感觉。直至多年之后,我想起那段经历还依然唏嘘不已。有人说那是与命运的抗争,可我认为那是一种挣扎,一种竭尽全力的突围。
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或许是万千游子的共同心愿,更是在家父母的最大期盼。
我女儿也不例外,因为远在青岛,加上平时工作太忙,好久没回家了。这次她和女婿一起回家过年,简直让我们欣喜若狂。去年他们新婚,按风俗婚后第一年要在婆家过年,然后就可以一家一年的轮流过年。
今年轮到在我们家过年。刚过腊八,妻子就开始张罗女儿回家过年的事宜,给女儿晒被子、换床单、收拾房间,角角落落都彻底打扫了一遍,忙的不亦乐乎。过了腊月二十,妻子说女儿女婿回家过年,要把家里布置的漂亮一点,她跑遍了县城的鲜花市场,精心挑选了几盆鲜花,经她这么一布置,家里果然增添了不少节日的氛围。女儿来的前一天,她又开始忙着蒸馒头,还包了好多豆包。豆包比较麻烦,先是做豆馅,把大枣、红小豆、豇豆、地瓜等煮好倒碎掺在一起。为了口感更好,孩子80多岁的姥姥戴着老花镜,把红枣一个一个地剪掉枣核,豆馅经过一个晚上的工夫才做好。第二天妻子和了发面和孩子的姥姥包了一天,期间分了几份给来串门的亲戚,几乎分了一大半。豆包分为两种,一种白面的,一种黄色黍子面的。黍子面的更好吃,软软糯糯的,亲戚们都夸做的好吃,妻子自然做的带劲,总之,家里洋溢着过年的喜气。
腊月二十九中午,孩子下班之后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途,期间我们一直或电话或微信联系,好在那天路况不错没有堵车,仅用5个小时就顺利到家。我原想去城东高速路口去接,无奈女儿坚决不同意。我和妻子早早的跑到小区大门外,当我们看见那辆熟悉的车子时心里禁不住猛地一阵高兴,赶紧小跑着迎上去。到了车库,打开车门,最先冲出来和我亲热的是孩子养的宠物“甜筒”。“甜筒”扑上来,亲热地用“两手”抓我的衣服,微微地张着嘴巴“呵呵”地“傻笑着”,不住地亲吻我的鞋子和裤腿。这时,我心里仿佛有块石头瞬间落了地,心也踏实了,一种满足、快乐、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两个孩子光顾着回家,中午也没吃好。将行李放好,妻子赶紧端出早已做好的饭菜。看着满桌子的饭菜,又看着两个孩子,说实话我真的好激动好高兴,我说今晚给你俩接风,咱们得喝点。作家冯骥才曾说过“酒是餐桌上的仙液”,过年了哪能不喝点酒?两个孩子连忙慌着倒酒,我们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我和妻子一直在絮絮叨叨地问这问那,两个孩子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孩子姥姥不停地给孩子夹菜。我想无论是孩子还是当父母的,都希望回家过年,都会有“回家真好”的感觉。女儿的一句“我们在外都当了一年的大人了,终于可以回家当几天孩子了”,让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热流,乖儿啊,在父母心中你们永远都是孩子!同时心底的深处又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孩子独自在外多不容易,他们身上该有多大的压力啊!远离父母,远离家乡,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操劳,所有的重担都要自己去扛,所有的委屈都要自己消解。现在回家了,所有的重担都可以卸下,所有的压力都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向父母倾诉。正如网友所说:“离家,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忙碌;想家,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孤独;回家,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快乐和幸福。”
孩子回家过年,虽然邀请的饭局很多,但两个孩子很懂事,为了多陪我们只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年夜饭我们在她舅家吃的,她舅舅几天前就写好了菜谱,头天晚上打扫卫生到深夜,除夕晚上她舅舅、舅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孩子和她表哥表嫂谈论着各自的工作和对未来的规划,自然也喝了不少酒。春节那天,女儿女婿一改往日假期睡懒觉的习惯,早早地起来吃了水饺,跟我们一起外出拜年。大年初二回老家去看她伯父伯母姑姑姑父。在老家每年的初二都是亲戚聚会的日子,这次女儿女婿回来更显隆重。大哥从年前就开始准备,专门请了厨师,初一下午就开始起火做菜,初二中午坐了满满当当的5大桌,热闹和喜庆的气氛溢满老家庭院。当然,过年少不了发红包,虽然孩子们工作了,也成家了,可回到家仍然是孩子,长辈都要给压岁钱。
孩子在家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除夕、春节、初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很快就到了初四。早晨八点半,孩子收拾好行装要去婆家了,她妈妈和姥姥总想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带给孩子,女儿女婿说了几次“装不下了”,她妈妈才肯罢休。我默默地帮孩子往车上装东西,这时的心情比起孩子回来时可谓千差万别,那种不舍、那种留恋、那种牵挂,或许只有当了父母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看着孩子的车出了地下车库,我和妻子又开车追了出去,还不想让孩子知道我们在后面送她。因路上车太多,一直追到高速路口也没能看到孩子那辆车的影子。妻子埋怨我开车太慢没有追上孩子,其实,我们已经老了,或许永远也赶不上孩子的脚步了。
我们只好掉头回来,心里一下子空荡荡的……
孩子回去了,年也就过完了。每年春节后孩子离家时总是依依难舍,那种失落感甚至要存续好久好久。现在想起来,很留恋孩子上大学的那会,那时年假较长,可以过了元宵节返校。而今不同了,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孩子有孩子的事业,他们不可能长期伴随在父母身边,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来去匆匆,像掏把火一样匆忙,更有一些心疼,像掏了自己的心一样。
想想看,每年有多少人回家过年?幸运的还能开车回家,还有多少人要乘飞机、赶高铁、挤火车,还要换乘,还要转站,还要下了火车坐汽车,甚至要再坐三轮或马车,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回家过年。我侄子每年都带着一家人从遥远的内蒙通辽开车回来,连续16个小时的车程,几乎不吃饭不休息。还有的路程更远更不方便,但他们乐此不疲,年年如此,为的是不再把想家的泪水装进信笺,不再用因特网与亲人交谈,将过年团聚视为最大的幸福,用过年团聚作为最美好的祝福。
回家过年,其实就是一种情怀,一种亲情,一种幸福,一种乡恋,让那缕被异乡月色浸泡的思念找到寄托,让那颗梦牵魂萦的乡恋之心得到存放。
我想在残荷上写一首诗
我家小区的北门外有一条宽宽的水沟,常年水流不断,无论深浅只是从未有过干涸,更让人心动的还是水里生长的那些绿荷。
我记得今年三、四月份沿着沟边漫步,看见水面浮着一小片荷叶,正是“荷叶犹开最小钱”之时。几天后再次路过,那荷叶已蓬勃舒展离开水面,正积极的向上生长,就像撑开的一把小伞。再后来,水面又长出几片荷叶,虽不敢与杨万里的“接天莲叶”相提并论,但也似有尽情蔓延之势。
五黄六月,在一个蛙声如潮的月夜,我发现荷叶越来越多,叶面也越来越大,团团的鲜绿在月华下簇拥在一起,晶莹的露珠像粒粒珍珠在叶心动情的滑动,那是绿色的梦幻,那是神奇的童话。这荷不知是沾染了皎洁的月光,还是被如潮的蛙鸣唤醒,很快就有一支含苞欲放的荷箭高高擎起,白中带着粉红,仿佛一盏高雅的花灯,它的静美、它的清雅、它的高洁、它的脱俗,真的让人无以言说,足足能让周边的水草噤声,让旁边的树木闭口。
荷虽如李商隐所言“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怎奈夏去秋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红藕香残雨簟秋。转眼又到初冬,北风萧瑟,寒霜普降,鲜亮的绿色正从脉经里渐渐褪去,整个的小绿伞慢慢干枯,这时的它既无夺人之态,又无取悦之色,更无阿谀之势。如若临水俯瞰,夕阳西下,水自东流,浮影残妆。此时此刻,让人既无怨语,也无闲愁,唯有心疼那残荷的苍凉与孤独。
但残荷不残,它在寒风中挺立着铮铮傲骨,叶虽枯,香自留,斗风雨,抗雪霜。残荷经历过春的萌发,夏的繁盛,秋的磨练,冬的考验,它感知四季的冷暖,遍阅岁月的沧桑。它是成熟的、含蓄的、内敛的,最重要的是它依旧在美丽着枯枝残梗、芬芳着清水淤泥、营养着莲与藕。
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美丽的花儿即使凋谢了也是美丽的,碧绿的荷叶即使干枯了也还是静好的。
我好想好想在残荷上写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