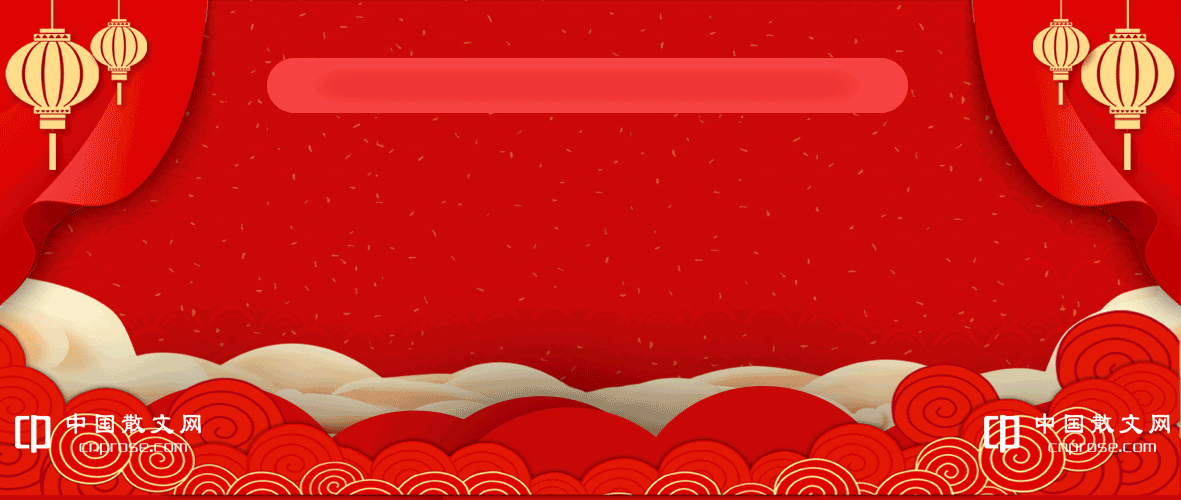【新中国75周年特刊丨当代作家 石英 国庆展】
当代作家
石英 作品展
1949-2024

作家简历
ZUO JIA JIAN LI
石英,当代文学大家,副部级待遇。原名石恒基,笔名荧光。1935年8月18日出生,山东龙口人。中共党员。是享誉中国文坛的“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杂文随笔等多栖作家”。被誉为“红色作家”“文学常青树”。少年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做机要密码电报工作,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新港》月刊编辑,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协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散文网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各种文学著作80多部,逾1800万字。其中包括文学传记《吉鸿昌》,长篇小说《火漫银滩》《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血雨》《密码》《公开潜伏》《人性伏击》《人性磁场》等,散文集《当代散文名家文库·石英卷》《石英散文选》《石英游记散文选》《石英美文选》《老兵大家丛书·石英卷——钟情无悔》《母爱》《生命之旅》等,诗集《故乡的星星》《爱情·生活》《当代正气歌》《石英精短诗选》《石英蜀地缘》《石英回眸齐鲁》等,杂文随笔集《石英杂文随笔选》《文史与人生》《古往今来》等,文艺评论集《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怎样写好散文》《文心的奋鸣》等。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均获天津市鲁迅文学奖,散文《武夷山的雨》获天津市作品一等奖,《厦门风韵》获中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等。
祖国万岁
国庆作品展
GUO QING ZUO PIN ZHAN
“女侠”洪兰
剑侠、侠客这类词儿,在金庸小说中肯定是常见的,只可惜在下读金大侠的作品不多,倒是参军前在故乡时读了不少晚清和民国期间出版的公案、剑侠小说,那里面的侠客之类的人物有的也算活灵活现,至少在当时也给了我很大影响。虽说那些剑侠的生活和性格很有虚幻色彩,但现实生活中我的确也遇到过具有侠肝义胆的真实人物,他们那种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和行为,给青少年时期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长达数年我个人和家庭遭受恶势力欺凌时,这种侠性人物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遏了恶徒们的凶焰;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有一簇代表光明的微火给了我相当的安慰——在敌伪统治下暗无天日的年月中,肯定是这样的。
我青少年时期有幸遇到的侠性人物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男侠”邢广明,他比我大三岁,是我东邻家的独子。他身强力壮,话语不多,却生性主持正义,恶霸之类的“少爷”及帮凶们大都惧他三分,他与我一起上学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位就是“女侠”洪兰,她是本村首富的二小姐。她家主要的人丁大都在天津经商,她本来也在天津上学,只是在城市学校放寒暑假时才回家乡度假。因为我们乡村学校放的是麦假和秋收假,时间不一致,她才利用在乡期间,来我们小学插班听课,借以“补习”。洪兰比我大五岁,当时我十一二岁,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总爱穿一件蓝色的阴丹士林大褂,白力士鞋,戴一只发卡,面容端正白皙,时常透着一种庄严。看得出,她对恶少和帮凶们妒忌我学习成绩好、家长老实无助而百般凌辱我的行为早就怒目而视,但可能是出于“客位”不便多加干预。但在邢广明告诉我,洪兰常在班主任老师甚至校长那里表达她心中的不平,揭露恶徒们的种种恶行,只是由于老师们也慑于恶少们家长的淫威而不敢正面加以管束。终于有一天,当恶少和为虎作伥的帮凶们对我进行群殴,在我的脸上抹秽物时(当时邢广明因为在家忙农活未来上学),“女侠”洪兰爆发了,她当即一拍课桌,手指恶徒们大声喝斥:“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坏,你们这样仗势欺压良善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敢管你们天也会管你们的!你们这样恶下去注定是没有好结果的!”
恶徒们在她厉声喝斥下一时有点被惊呆了,但缓过神儿来后,对洪兰污言秽语相加,一派下流嘴脸。洪兰一跺脚,大跨步地离开了课堂,我清楚地听到,她踏着深秋时节飘落的树叶,一去不回头地走了,永远地离去了……
过了些日子,贫农户老梁(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本村第一个秘密党员)告诉我母亲:洪兰没有回天津,而是独自去南山根据地当了女八路。
后来,八路军开过来,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不消说,我满含热泪地投身革命,欺压我的恶少们大都随家长逃至“美蒋”盘踞的青岛。我参军后,多少年也未听到“女侠”洪兰的任何讯息,直到1954年秋天我回乡探望父母,老党员老梁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洪兰所在单位,来村里了解洪兰的家庭情况,并介绍了她参加革命后的表现。她在野战军中一直担任主治军医,开始学的是内科,但她后来坚决要求做外科医生,因为她看到有太多的伤员需要救治,她要为他们做手术,救活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战胜敌人的力量。后来在实战中历练,她成为她所在那个军的“一把救命刀”,不光是抢救和医治伤员,紧要关头,这位“女侠”性子的军医也是一挺机枪,一门炮。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中,由于部队日日夜夜阻击敌人,伤亡很大,一名负伤经洪兰刚刚救活过来的机枪射手在敌方炮击下牺牲,敌军趁机蜂拥而上。情急之下,洪兰端起那名烈士的机枪,突突突……敌军应声倒下一片,他们被这个猛然出现的“女共军”打懵了。孰不知洪兰平时摸过各种枪械,入朝鲜后,轻重机枪、卡宾枪、汤姆逊冲锋枪乃至迫击炮,她都向老兵学习过,都使得挺溜。(溜,方言土语中“麻利熟练”的意思。)在洪兰和余下的战士“不要命的硬顶”之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成功地掩护了大部队安全北撤。由于在非常关头下的破格表现,洪兰医生被部队领导机关特记一等功。但洪兰医生也因右臂负重伤而被同志抢下火线,并转至东北后方医院治疗。军医院在研究对她的治疗方案时,曾有过截肢的动议。洪兰得知后,苦苦恳求有关领导和大夫们尽力保住她胳膊,她说我还要给我们的同志做手术呢。为此她竟嚎啕大哭起来。据说,这是她平生的两个“第一次”:一是苦苦恳求别人,一是嚎啕大哭。为此领导还请来了地方医院的外科“大拿”,大家集思广益,小心翼翼地保住了她的胳膊,也保住了许多生命和健康。洪兰千谢万谢拯救了她的同行。康复后她转业到一家军工保密单位医院工作。但她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做人风格,从不表功居功,绝大数人都不知道她在十年军旅生涯中,是一位立过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多次三等功而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功臣。平时她除了在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德技兼优之外,还自愿地加入慈善事业,在逢年过节时,给相识和不相识的贫困善良人寄点钱去。她这样做,出发点也极为朴素:我的待遇不低,多余了没用,让它多发挥点作用吧。其实她个人的生活非常节俭,人们说没见她添置过什么新衣裳。
老梁在转述时,还特别提到一桩有趣的事:这件事我乍听颇感意外,原来洪兰当年在军中虽然是正营级,待遇还可以,却因为她的家庭出身,在入党问题上几度“卡壳”。1954年深秋,军工单位的地次“彻底”的外调解开了这个疙瘩。当时外调人员问老梁洪兰参军前的表现。老梁的回答坚决明确:“她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这没错。可人家上几辈就是正经的买卖人,从来没欺负过谁,一句话,没做过孽缺过德。不是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吗?那就看她本人。她年少在家乡时就很正,跟共产党、八路军有缘,说实在话,比我这个老贫农老党员的革命性儿半点也不差!“革命性儿”,在我们老家一带,这种语言场合是带儿化的。
据说就是经过这次外调,洪兰的入党问题算是解决了。从十七八岁到将近而立之年,也算经历了十年长征。但不管怎样,终于实现了她人生的一桩夙愿。
待到我九十年代最后一次还乡时,老梁已然过世,也巧,所幸又遇到了在内蒙与洪兰见过面的老梁的儿子。他于六十年代以技术工人身份去支援内蒙古建设,在一次去医院查体时,偶然碰上其父经常念叨的洪兰姑娘。洪兰当时也大感意外,她说,这是离乡二十多年来头一回遇到真正的老乡(同县还是同村)。在交谈中,小梁告诉她:“咱们村的石恒基后来也参军了,你们不是也认识吗?”(石恒基是我原来的名字)。洪兰听到这个信息显得特高兴,立马问他:“在啥地方工作?”小梁说:“好像是机要部门,具体啥单位我也不清楚。”所以尽管洪兰得知我亦参军,她并没有与我联系,那年代又没有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类寻人途径;再说小梁说我在机要部门已足以打消洪兰主动联系的念头,像她这样性格的人,是绝对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其实小梁并不清楚,其时我早已离开机要部门报考了大学,甚至已毕业到文学编辑部门工作了。
小梁说他也曾对洪兰提过她为啥不回家乡看看。一提起这点,洪兰脸色骤变,显露出一种相当复杂的表情,最后她还是吐了句话:“那里有我心里抹不去的痛。”小梁当时不晓,但我能够想到:在村校“补习”时那班恶少们的嘴脸和无耻行径,在她心底留下了太深的刻痕;还有由于她的仗义执言而遭到恶言秽语的辱骂,她可能还很难忘记。如确乎如此,那么在这位“侠女”开阔的胸怀中也还有一个柔弱的角落……
在此后几年发生的“风暴”中,小梁说也有人在医院门口给洪兰贴大字报,炮轰她坚持施善行为是“假仁假义、封建余孽”等等,但洪兰从容应对,她对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但那以后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小梁去医院看病,洪兰的同事告诉他,洪大夫歇病假在家。至于她的家庭子女等情况,小梁一点也没有涉及,是他不肯说,还是洪兰从来也未对他透露过,不得而知。
其实就在我最后这次回乡时,小梁已年届五旬,退休在家。由于他从内蒙古回来也有数年,我估计他对洪兰的近况也不见得详知。但当我问起时,他欲吐又止,最后他对我讲了实话:最近与内蒙古那边的老朋友通电话,他们有的说洪大夫已经走了,小梁解释说:“因为我怕传言不准,所以刚才没有对你说。”我觉得不是不说,而是像洪兰这样难得的大好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走了……
她这年应该是七十岁,如“是”的话,未免也太匆促了。
自从她走后,几十年间始终未见一面,这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但她作为“侠女”的形象,绝不会因此而磨灭。而且,正因有此人真实存在过,我则坚定不移地认为世上确有侠性人物。
从《文赋》想到三国名将子孙陆机
我是195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大约在1957年春季,我们的中国文学史课讲到魏晋南北朝阶段,任课老师为王达津教授。
文学史中也掺杂着文艺理论的讲授(我们尽管有文艺理论的专课,但那是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涉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内容极少)。我记得这一阶段主要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而钟嵘的《诗品》则是数语带过,没有展开来讲。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应该说是比较稀缺的,所以仅有的几篇(部)便格外引起重视。陆机的《文赋》是赋体文论,记得王教授在讲课中不自觉地还加以吟诵。陆机本身就是诗人,也写散文作品,所以其创作经验比较丰富,涉猎的内容很广泛。从作家创作过程、兴起及可能遇到的问题,优长与弊病,构思感兴,独创与应关注之点,以及对文体、风格的分析等等,均有一定见地。较之曹丕的《典论•论文》阐述更为详尽,为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肯定有借鉴意义。
不知为何,当时我在听讲《文赋》时,不自觉地想到了它的作者的形象:似乎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材适中的一位文秀男士,而且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王中戊联系起来:身穿一件浅蓝色大褂,留短分发,脚上一双半旧的黄白相间的皮鞋,风度儒雅,却不体弱。这种不无荒诞的形象联想一直到《文赋》讲过后仍在继续……
其实,我联想中的这两个人相距一千六百余年,而且其身份没有任何相同之点。陆家为当时江南士族,世居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陆机之祖父陆逊,为孙权时东吴名将,在公元222年的彝陵决战中大获全胜,甚至直接导致蜀汉皇帝命丧白帝城。在此之前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并截杀关羽之役,其实也有陆逊从中谋划。此后陆逊一直镇守武昌(今鄂州),长期任荆州牧直至花甲之年去世。其人不仅富有将略之才,且思想缜密,亦有文质,与其有关的多个成语流传于世,如“忍辱负重”等便是。其子陆抗(陆机之父)亦为东吴名将,长期扼守长江防线与西晋大将军羊祜相抗衡,曾多次击退晋军东进之举。在此期间,陆抗还追杀了西陵督叛将步阐。受东吴当局长期信任,为荆州牧,大将军。
可以想见,假如陆逊父子这样谋略过人的名将在世,公元280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那样的局面将不可能实现。只可惜东吴好远毕竟已经结束,西晋军浩荡东下之时,陆逊已离世35年,而陆抗则刚刚去世6年,但昔日那种势均力敌的形势毕竟已不复存在!
陆机、陆云兄弟尽管在东吴也曾做过牙门将之类,但已无其先祖、先父那种自来具备的军事胜才。吴亡后,不得不相信(亦存很大幻想)。司马氏对亡国遗臣的“宽厚”之举,兄弟俩在居家苦读诗书数年后,相谐赶赴洛阳,投奔司马氏政权,且一段时间文各有所躁动,被称为“二陆”。大致相同时间,尚有张载与其张协、张亢而号称“三张”,所谓“三张”与“二陆”结局不同在于:张载等目睹西晋当局表面奢华盛事,实则乱局一堆,杀机四伏,于是称疾告归,得以免遭大劫。而陆机兄弟也许血液中仍含有先人“出人头地”的基因,颇想在不同槽中多享想几口嗟来之食,还想在政略与兵戎方面也展现一番,一个机会(也是陷阱)是:司马氏自窝乱,八王之间相互撕咬,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义,而任陆机为“后将军”和“河北大都督”。至于当时陆机是咋想的,恐怕被绑架的成分很大,硬着头皮也要应召,结果可想而知。本质上属于一介文士,却要去带兵冲锋陷阵,既非当年先祖先父之“本行”,又非处于东吴自家的大环境,败局几乎是早就等在那里;再加上谗言吹主子司马颖耳朵里,八王哪个不是阴谋家加血腥遗传基因造就的胚胎,这位成都王正没处撒气,“杀”字一旦出口,便如一股黑风吹断擅长骈体文的头颈,陆机连同胞弟陆云很轻易地成为魏晋时期嗜杀成风的又一宗祭品,悲夫!
陆机乃至二陆的命运,有那个时期大环境之必然,也不能完全排斥他们本人行事中的教训。假若他们的先祖陆逊、陆抗地下有知,会不会为故国之不存与子孙的横遭司马氏之“屠戮”而顿足捶胸乃至唏嘘挥泪?
当然,这个屠戮者的司马氏当局也谈不上真正的美妙。一个从来是以阴谋起家以血腥互虐成性的司马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事业中其荒淫其无论应毫不争议的排在冠亚军之列,我国的史书上不乏对所谓晋武帝司马炎的记述,其后宫佳丽达万人之数,如“羊车投草”之类的成语皆出于此。而晋惠帝之后贾南风(司马氏宠臣贾充之女),更是一个淫虐乱政的典型,她挑动八王互弑并擅权多年,最后当然也必然死于他人之手。
但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个似乎难以理解的特异现象:西晋政权的建立既然如此荒纵无伦,却能在攻伐大业上取得表面统一中国之局面,而且产生过有如邓艾(艾伐蜀时虽属曹魏,然军政大权已皆为司马氏所掌控)、羊祜、杜预、王濬等这样一些战略家和一流名将。此种现象,亦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回光返照”,它说明在强势政权统治集团的逆光笼罩下,较短时间内迸出了一种超常的诱惑力与影响力,造就出某些不俗的人才和时代业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是仅有的情况。然而——多么残酷的“然而”,也就是在昙花一现之后,晋武帝之后的惠帝,怀帝,愍帝之流,不是作为一个呆瓜被人糊里糊涂地毒死,就是被匈奴等外族入侵者当成一个“青衣”(晋杯帝即曾被逼青衣行酒)饭桶被蹂躏而死。而且死时相对都较年轻,昭示着西晋四十余年的迭宕生态,此刻还去哪里呼唤晋初那副名将迭出的局面?
在这点上,不能不说到司马睿的东晋偏安江南,还使中华大地东南一隅显现出尚较温润的几缕阳光。
说了这么多,似乎疏离了文题中的人物陆机。不,当我们再翻阅他的“文艺理论”著作《文赋》时,起码暂时忘却了他生存年代那个大环境,不再嗅到任何血腥味,而且不禁吟诵文中之要点:作文之由,一感于物,一本于学。而所难者,在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也。然。
关于秦良玉
那还是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大约在过年前后),在故乡我姥姥家玩,看到她炕头边的墙上贴着一张戎装的女英雄像,骑一匹白马,手持兵器,是刀还是枪记不准了。我问姥姥这位女将军是谁?她说叫秦良玉,是三百年前的人物。
姥姥和姥爷都生于清咸丰年间,那时他们都是八十出头的年纪,就在那之后不久都相继辞世。从那以后有好几年,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女英雄的画像之类,直到1944年秋天,我们那一片地方已开始“变天”,村小学进行了重大改革,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被聘来教学,有一位号称“大饱学”的战老师据说啥事皆通。我突然想起几年前在姥姥家初识的秦良玉来,便斗胆问他这个人物的相关情况,战老师很快就回答了我。他说这位巾帼英雄是四川忠县一带石柱的明朝士官(好像叫宣抚使)的妻子,文武双全,所带的兵叫“白杆兵”(更具体的情况估计他也不清楚),其中女兵也不少。后来她丈夫病故,她又被明朝当局任命接替其夫的职位。记得当时我听到此节后就有一个想法:明朝当局怎么如此不歧视女性,还能命她代夫领兵?战老师还说:那时明朝已处于末期,后金(清)和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等从不同方面打击这个垂危的封建王朝,明当局已呈招架不住之势。可这个秦良玉的立场扔一如既往,亲率她的“白杆兵”从四川远道而来,参与保卫北京,硬抗满清军;另一方面,她对农民起义军亦绝不合作,在四川本土与张献忠军势不两立,直到她七十多岁明亡后此立场亦未改变……
在战老师的述说中,我至少听出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他依然肯定秦良玉是位巾帼英雄,在抗后金(清)这点上是位值得赞赏的,但对她死保一个垂危的封建王朝好像就有点不识时务,更重要的是她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也不符合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至死不变,这就有点问题了。
由此我便明白了几年中没想通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位实实在在的巾帼英雄,反不如大半只活跃于戏曲、民间传说中的穆桂英、花木兰那么出名,那么被鼓吹得火爆,原来这个秦良玉有如此多的“局限性”啊!
事情又过了几十年,前几年我不经意间从报纸上得知:实力雄厚的重庆京剧院隆重排演了大型京剧《秦良玉》,由文武兼备,唱念做打齐全的尚派旦角担纲,成功地突现了三百多年前的一位巾帼英雄复杂而丰满的艺术形象。如果不是得知首轮演出已然结束,我真想专程去往重庆观瞻这场难得的演出。从这次公开露演亦不难看出: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淘滤,对于秦良玉这个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已渐超理性和全面,其走向与我多年来的思考线路应该说是大致相接近的。
但我对此仍不满足,疫情发生的前一年,我趁去重庆参加笔会的机会,抽空赶赴忠县和石柱一带实地访察一番,直接交谈的人士有二、三十位,职业、身份也是方方面面,但对我的寻访无不热诚配合,他们对三百年前这位非凡的“乡亲”不仅毫不生疏,而且无不表现出深深的自豪。在寻访中,他们向我提供了不少我原先不详知的情节,而且强调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三百多年没有多少辈数,一代代地传下来,没有胡编乱造,虚头把脑的东西。”他们引为骄傲的,就是这个“真”。有位教师模样的长者还显现出相当高的分析水平:“对于一位封建时代的人物,哪管她是一位女杰,也不能以今天我们某种思想标准来要求她,譬如说,她之所以始终尽忠于当时的明朝当局,是因为出于她个人的良心和职守的责任。既然她和她的属下食的是明朝的俸禄,就要忠于职守,为保卫江山不惜一切代价,而不能当缩头乌龟。”还有年轻的“知情者”(先辈们的谆谆遗教)含着热泪对我讲:“秦良玉这个人还有一个突出性格,就是对于任何持强凌弱的恶势力从不买账,而且就是要面对面,枪对枪,刀对刀地决一雌雄。她曾两次率军北上勇赴国难,一次是天启元年(1621),一次是崇祯三年(1630),面对不可一世的后金骁骑半点不怵,至少在当时都把对手击退了。”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其中有位来自天津的技术工人,当他得知我曾在天津工作、生活了多年,便带着调侃的口吻说:“这位秦良玉就像天津人说的越是面对横茬的家伙就更不尿他”。
当我提及秦良玉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时,那位老师模样的长者说:“凡事都得以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谓秦良玉对农民起义军主要就是对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一节。真实的情况是:张献忠不仅仅是严厉镇压地主,富有者的反抗,他们对普通农民只要不那么顺从地缴粮纳款也是毫不手软的。在这种情况下,秦良玉怎么可能与他们亲密合作或是开门迎客呢?她在石柱本土筑隘扎寨以保土安民的做法,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另一位中年女性也插嘴说:“李自成、张献忠与明军厮杀,最后还不是为了夺取龙墩坐朝廷?而秦良玉却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她最后这一句显然是话里有话,意指有的农民起义军最终还是为了改朝换代,而不可能有其它无私的目的。而且还有一点,他们尽量不与清军发生正面对抗。
最后,大家的谈话集中到一点:当时的情势是后金(清)骁骑虎视眈眈,有席卷中华大地之势,各路农民起义大军风起云涌,最终目标还是指向紫金城明朝中枢;或暂时绕弯占领要地建立政权(如张献忠入川)。而秦良玉的基本选择是:抗击后金虎狼之师,以尽职责,同时又相对规避和防御所谓农民起义军,至少是不合作不与之为伍而已。至于最终结果如何,也不是她一个区区弱女子(她再顽强,就当时金局力量对比而言,本质上仍属于弱者一方)说了算的。
为此,我怀着某种惆怅心情,写了一首也算七律的诗作,这里只引用后四句:
心怜庶众琴常咽,剑指骁凶刃自鸣。
晚岁任它南或北,依然梦里点雄兵。
热烈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