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春特刊|中国作家 王录升 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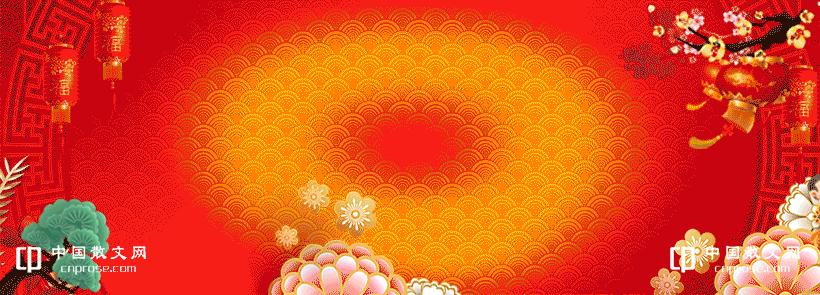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
—— 王录升 作品展 ——
作家简历
★
王录升 笔名金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丹东市作家协会顾问。先后从事过高校教学、行政管理、机关党建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鸭丫诗社”发起人,与人合编改革开放初期首部大学生诗歌专集《大学生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表诗歌800余首。诗作曾被《诗刊》《当代诗歌》《诗神》《诗潮》《诗歌月刊》《鸭绿江》《满族文学》以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媒体等五十余家媒体选用,并被翻译至美国、英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先后5次获得省及以上诗歌奖项。著有诗集《三套车》(三人集、辽宁大学出版社)、《金黄的生命河》(人民日报出版社)、《经过》(万卷出版公司)。
民 间
有时窄,有时宽
有时近,有时远
有时苦,有时甜
泥做的众生
水绘的屋檐
拴不住蜿蜒的地平线
草有草的族谱
牛有牛的方言
每一块土都落过草鞭
烈酒呛透胸膛
杯与盏结伴走动
有长有短的筷子蘸着咸淡
每一声召唤都听得见
被烟火呛到的缄默
一定是心愿
出走的风
什么样的推手
长过我的一生
长过我在人世间
存放的路程
从树叶上跌下来的
不仅有雨水,尘埃
还有风
穿过人间的袖口和墙缝
有时轻,有时重
有时热,有时冷
透明和不透明
裹挟我的懵懂
没有入口不会阻隔关切
没有出口也不会影响透明
用不同的漩涡握住
拴着风筝的纤绳
我与风的拥抱从未被打断
风带走是是非非,留下真诚
不断流的宗族
总是跟在风的迁徙之中
跟一场风赛跑
胜出的只有那些经幡
它们执掌着甜酸苦辣
放手了疼痛
我是人民
不是泥土在呼吸
而是在地下匍匐行进的草根
不是山脉在起伏
而是石头群不肯平复的兴奋
我就站在这里
就像气旋里的砂砾
琐事缠身的蜜蜂
套着亲近的知了
一切与节气有关的来往
都是我的亲戚
我也转身下马
驾驭城市的灰尘
我占领街巷角落
让月色熏香灵魂
我敞亮着向生活微笑
做风雨的知音
我是人民
从来不知道我是掉队的人
我的身后还有人民
还有耶稣和达尔文
我衍生灵魂
我是不需要化缘的神
我不需要尊称
我的前生和来世都是人民
我在平静的光阴里痊愈
只有人民才有的累累伤痕
枫树湾
把静寂让给生动
只有秋天,枫树湾才如此火红
它们从低温开始燃烧
一片片枫叶,追撵天空
蓝天侧身向远
让一切可能尽情驰骋
房屋坝埂和苟活缩小了
在道路一头,拴紧了真诚
秋天和夏天顺利毕业了
如期而至的新课程
写进了监护,休耕和滴灌
枫叶用鲜红感恩,致敬
北山和南山扛起了自信
枫树湾的红不再凋零
大地卸下了千年沉重
只为此刻,步履轻盈
马头琴
手工打造的马头立在琴上
抻起来乡音
两根弦像抽马的鞭子
夹着嘶鸣和兴奋
风暴和林荫合成了短调和长调
掠过连绵的丘陵和弥雾
无垠的草原成为空旷的音箱
呼应着粗犷的高亢和厚重的低沉
无须谱曲填词
起身于羽毛和草根,一声声
由近到远,由远到近
铸就了不死的灵魂
泥的写意
泥是一群小动物
它们群居
搂着好天气,坏天气
泥是一团好兄弟
可扁可圆,可薄可厚
耐得住摔打,忍得住敲击
泥塑却很狡猾
把不沾水做成品牌
把不愿意洗当做荣誉
粘上人身的泥
绝不愿意上墙
也在厅堂里走来走去
只有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老伙计
时常用泥敷伤口
把痛在泥里痊愈
花开的声音
我问过许多人
一朵花到底有多深沉
花瓣总是羞涩不语
一滴滴清澈融入花信
一朵花领唱,带起了一片
舞台就这样在泥土里扎根
生命的音符在弯弯曲曲流淌
拴住自由快乐的清贫
不是所有的花都清香
淡雅的叶子也有皱纹
既使在风暴中跌倒
也绝不去沾染风尘
花打开的世界
在山谷里有回音
它们的迎亲队伍
正在穿过森林
除 草
跟着飞鸟的草籽一定是快乐的
与跟风不同
它们与鸟有一致的跑道
总要向空地方张望
不知道命运里早有着落
每个缝隙都能包容心跳
草不是坏孩子
在田里孵化的芽孢,不知道
什么时候,得罪过锄头
一片片秧苗丰满了羽毛
草,被排挤
只能在山涧荒滩祈祷
杀死草的也叫药
开这样荒唐的玩笑,竟然
没有人心惊肉跳
走在马路上的一群鸭子
上马路之前
它们肯定开过会
一个个呱呱叫好
要去的地方
肯定比这段马路长
一大群鸭子上了马路
排着队
不是去交养路费
无论什么车都缩短了犹豫
在翅膀面前减速
嘴唇怎么也硬不过鸭嘴
冷了有棚子住
饿了有人喂
鸭子离开这美好光阴
我看要后悔
只有此刻
我们都在同一条道上
下了道
鸭子在岸上水里两栖
还会飞
而我不会
上坡,下坡
不是上坡,就是下坡
只有草从来不斜着
不是上坡,就是下坡
门前只有这一条路
父母从来没有直着过
我对上坡,下坡,没有权力选择
草叶厚厚地堆在上坡路上
堵着雨,还想再活,直到烂了
比我的父母还拧,等
太阳下坡了,我儿时的球
就在那一刻丢了
田字格
从来没数过
一个田子本里
有多少个田字格
阳光也没数过
油灯也没数过
镶嵌在童年里的这些数
一定多过我的风筝
和商店里的玩具汽车
被固定的规格一定疼
大了容易漏神
小了装不下叮嘱
一个挨着一个的笔划
把童年挤出了皱褶
如果一个格是一所学校
或者能置放一张课桌
该有多好
格局大了
可以藏下许多小动作
假如春天是一个格
铧犁是一支支笔
比铧犁跑的更远的
一群群秧苗
就是夏天和秋天的祖国
橡皮擦
既然断不了与纸和笔的瓜葛
就在它们之间安家
白纸要白,铅笔要黑
它要一份告白的差事
在桌面上跑龙套
有时被捏住,有时被放下
在歪扭的字里行间行走
时常疼的说不出话
辈分更高的胶皮
在奔跑的轮胎上
它们用扬起的灰尘
在道路上作画
而小小橡皮的重重心事
是擦完自己的一辈子
也不知道,被擦掉的字里
有没有奔腾的千里马
打滑梯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款游戏
要刺激并快乐着
就去打滑梯
小时候的滑梯不属于人工
石子,土块甚至瓦砾
经常不怀好意
打滑梯的念头
有时潜伏在草垛上
有时萌发在小雨里
大人们的重心很高
他们更忌惮放手
怎么让心事安全着地
无所顾及的那些人
也让滑梯烦恼
破损的规则坏了游戏的名誉
我曾错误地认为
这种势能只有滑梯才有
不知道我的大地时常心律不齐
我的妈妈不打滑梯
只有她肯让我跌倒后
再爬上去
滚铁环
我从小就爱滚硬的圆
比如铁环,空心的没有负担
雨雪从来没有拒绝它肤浅的印痕
滚着滚着离家越来越远
长大后长了满身肉
我差一点变成实心的圆
滚着滚着滚不动了
回不到空心的少年
纳鞋底
扎痛我一辈子的那根针
那时,就在母亲手里
贯穿鞋底的神经布线
穿过针鼻
面糊干巴又倔强
没有筋骨,却让碎布硬气
母亲用针一次次扎破僵持
让希望露出端倪
灯油就要被熬干了
灯芯发出了滋滋委屈
母亲的发际线在抬高
皱纹不断下移
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带着母亲的体温启程
路上的那些石头
再也无法硌痛想象力
步 行
无穷尽的道路,一定绕在齿轮上
有谷底,也有山峰
最远的路标,一定嵌在基因里
奔波或躺平,早已被命运锁定
最难登顶的山峰,一定是自己
只有直立的骨头,能够抵住疼痛
影子里的泡沫,有聚有散
只有步行,才看得分明
转 身
一只蚂蚁把细节藏在身体里
慢慢向我靠近,我看不到它的表情
和它的足印
我在秋风里落单,大地很深沉
一片片金黄的落叶
在沟沟坎坎依偎着树根
此刻,我转过身
想给蚂蚁带路,我身后的房屋宽敞
客厅里空无一人
相互觊觎了内心深处
才知道,孤独不分大小
天与地的根,叫信任
动工了
向城市行进的方式不同
这个山脚,用上了动工
城市的气息从不远处来
电扇更热,火炕更冷
许多城里人来呼吸新鲜空气
村长已经被拉扯进城
莽撞的挖掘机
户口也在城里
动物不用动工这个词
地瓜土豆喊疼痛,没有用
所有的墙头树杈
都挂着标语
大致是水泥来了
比山洪更无情
这座山头也要被削平了
以后证明这里曾经有座山
只有看照片
还有施工证
我想收养那些沙子
就在昨天,我扫走了阳台上的沙子
我不知道它们在哪个地方拐弯
用微小的固执和胆量,爬回楼上
没有人种过沙子,但是沙子到处生长
月色里,阳光下,楼宇中
虽然没有翅膀,不与任何节气较量
我与沙子的灵魂相似
沙子并不知道,我们语言不通
相同的是都经过风霜,没有荫凉
如今我依然在漂流
用最柔软的足底,诠释坚强
哪里有沙子,哪里就是家乡
我想收养那些沙子,怕它们被深埋
我知道它们有呼吸,不屑与腐叶纠缠
我不怕眼睛里有沙子,只要同时还有光亮
我 要
我要快快地老,快快地蜕壳
然后返青,从头选择怎么活
我要斑驳的时光,不再颠簸
疤痕里燃烧着爱过和被爱过
我要一条大道,把它裁成几条小路
给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
我要躺着,化成一条河
让骨骼变成流动的石子
我要用煮饭的高温,烧死灶里的火
让灰烬回头,魂归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