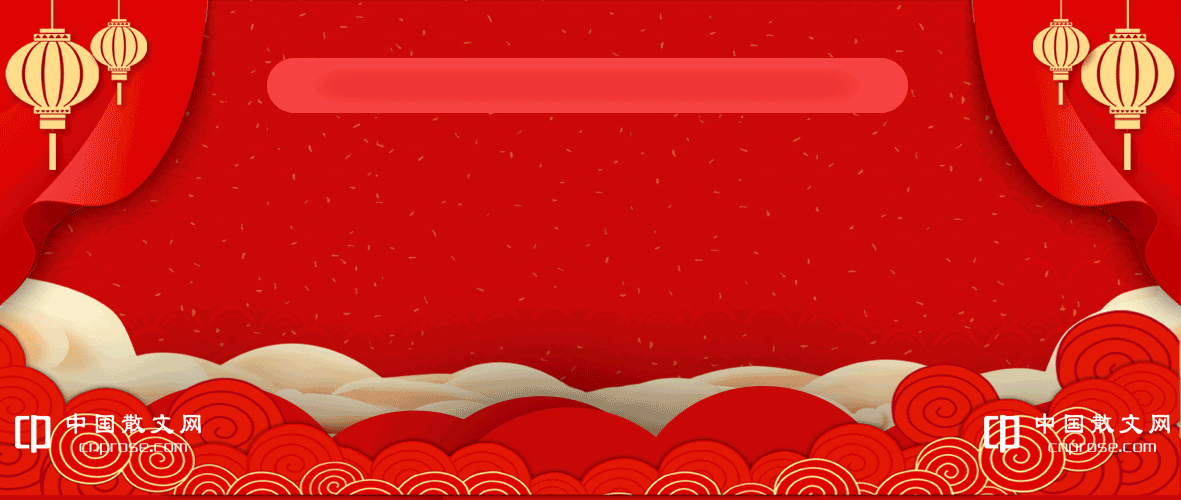【新中国75周年特刊丨当代作家 朱大路 国庆作品展】
当代作家
朱大路 国庆作品展
作家简历
ZUO JIA JIAN LI
朱大路 上海人,1947年出生,1965年进《文汇报》社,2007年退休。其中,在“笔会”副刊编杂文20年。高级编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组委会副会长,上海浦东新区杂文学会会长。著有散文杂文集《乡音的色彩》等三本,报告文学集《盲流梦》,传记集《上海笑星传奇》,长篇小说《上海爷叔》等四本,主编《杂文300篇》等三本。先后参加全国各种散文、杂文大赛,七次获得一等奖,四次获得金奖。
祖国万岁
国庆作品展
GUO QING ZUO PIN ZHAN
凉
热烘烘的天,有人却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那是网上,“某大咖”谈“文化的发展”时,感叹以往的不少文化正滑行在“凉”的路上,并说了一句自以为“很残酷”的话——“现在50后、60后、70后甚至80后喜欢的文化,未来可能很快会被90后、00后终结。”
噢,是借用“凉”字,感叹文化的衰退和消亡!
什么样的文化形式呢?“玉石、翡翠”,“文玩、手串”,年轻人没兴趣了;“邮票,古书籍,已经在凉的路上”;“紫砂壶,喝茶文化”,“目前看来比较危险”;“大多数的戏曲、地方戏”,“大部分会无限接近于消亡”;“国画”,“有凉的趋势”;“象棋,年轻人玩的越来越少了,游戏取而代之”;“养鸽子、养鸟,被其他宠物取代”;“中式家具,贵重木材家具,其实现在已经凉了”;“电视台节目,全面凉”……
刚读完这些文字,打开手机,我又瞧见一则新闻——“上海爷叔35年无休,守护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表明纸媒在走下坡路,“报刊销售亭”全面变凉;顾客们只能从这家最后的门店,寻找“纸质回忆”。
我心寂寂,惘然若失。
对象棋的兴盛,吾辈记忆犹新。七十年代,我们报社的象棋爱好者,以各种方式,过一把象棋瘾。有一天,跑体育的老记者,请来了中国象棋一代宗师、多届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胡荣华,与报社的六位选手下“盲棋”。这回,可让我开眼界啦——“盲棋”,就是胡荣华面对墙壁、不看棋盘,用话说出每一步棋的下法,轮流同六位选手开战。半小时过去了,六盘棋格局大变,面容殊异,可胡荣华对各盘棋走成什么样,了然于胸,从容应对。最精彩的是,当其中一位选手走了某步棋时,胡荣华好心提醒道:“这一步走不得,走了你要输的!”让他悔棋重走。记得,比赛结果,胡荣华赢了五盘,和了一盘。我听到身旁一位老编辑连连点头,赞曰:“绝了!”
如今,此等盛况,不复存在。
集邮也如此。六十年代初,我们都是集邮爱好者,课余,捧着集邮簿,去集邮公司,看新出了哪些盖销票,有中意的,随时买进。还同周围的集邮发烧友,互通有无,交换盖销票。那年代,学校鼓励学俄语的学生,同苏联赤塔孤儿院的孤儿们通信,以促进俄语学习。孤儿们竟然也是集邮爱好者,随信寄来几张苏联邮票,大家没见过,视为珍品,放在集邮簿内,互相炫耀。
这样的集邮发烧友,今天,至少在我眼中,是越来越少了。想一想,我自己的集邮簿,也不知扔到哪个角落了。
至于地方戏曲——以昆曲为例——本来就是阳春白雪。六百余年的传承,磕磕绊绊,不容易,有点“曲高和寡”的腔调。文学性强,唱词或意气闲雅,风韵绵长,或深博辽远,直奔日月,或幽邃蜿蜒,以见闺情。现代以俞振飞为代表,振兴了昆山地区诞生的这一剧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俞振飞仍以耄耋之年,为昆曲振兴,劳神费心。他受到昆曲粉丝们的拥戴。尊崇他,便是尊崇昆曲。有一次,我参加有俞振飞出席的有关昆曲活动,回程中,与他同乘一辆小汽车,目睹了他受欢迎的情景。
相比较,从80后到00后,还有多少昆曲粉丝?会不会,六百余年的昆曲,从此沿下坡路,滑到谷底?一股凉意,从背脊,到脚跟,直贯下来。
当然,放眼望去,有一些文化样式,不仅不凉,还挺有热度。诗歌——没凉!新诗的爱好者,创作者,在人群中时有冒头;各种长诗,短诗,犹如野地的花,春雨一洒,秋雨一灌,一堆堆,一簇簇,使劲绽放。还有,旧体诗词,也劲头正猛,并不因形式古旧,格律束缚,而让尝试者望而生畏。中华诗词学会的倡导,多次诗词大赛的磨砺,让构思精到、功力渐深的作品,屡现水面。我的微信群,独多诗歌发烧友,兴致勃勃,晒各自的新作,收取赞语,期待反馈。即使疫情期间,上午做核酸,下午依然探讨诗词。有时围绕“旧体诗,格律主要还是意境主要”的命题,喋喋争论,乐此不疲。我过去的一位老同事,八十多岁,住养老院了,却是三百六十五天,每日创作一首旧体词,比如立夏到了,写一首《眉峰碧》,诵咏“夏到蓬浓屏,墙角蛙跳影”;大暑来了,填一阕《唐多令》,吟哦“天帝舞火龙,时令大暑逢”,还准时发入我的微信,让我过一把古诗词之瘾。
小说——没凉!我定期收到上海出版的《思南文学选刊》,里面,每期都选载小说——来自全国各地文学刊物里的,从《人民文学》《收获》《作家》,到《钟山》《芙蓉》《四川文学》,应有尽有,且是精选,百里挑一;遴择之当,足见识力之锐。小说上品,已是粲然可观,作为基底的大众创作,队伍绝对更加庞大。“小说凉了”,乃是伪命题一个。
杂文——凉了?表面看,出版社——口子收紧了,有的社,一年一度的小说选、诗歌选、散文选、随笔选,均按时推出,唯独——杂文选缺席。你说操弄杂文的角儿,腹腔内啥滋味?但杂文家的韧性就在这里:面对冷落,他们偏让个体写作方兴未艾,偏让各地年会此起彼伏。“我们的杂文向太阳”——全国杂文界的一位领导人,早就亮出宣言了。想想看,太阳底下的杂文,能凉得下来吗?
至于纸媒,尤其是报纸,面对新媒体形式的日益繁盛,有少数关门歇业,是真的,但只要深刻理解报纸的职能,办得出色,有声音,富文采,信息量大,让芸芸众生感到缺不了它,肯掏钱订阅,且坐得下来,耐心翻读,就不会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口味。太爷爷热衷的玩意儿,第N代子孙也要全盘接收?你不看看窗外的云山,已历经几度春秋?总不能让00后的清新型帅哥,去跳唐朝的胡腾舞、去玩战国的投壶、去写南北朝的骈文。同理,民国时期老妇人痴迷的掷骰子夺“状元签”玩法,也吸引不了装束时髦的当代超女。
时代朝前走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顺时应变的,自然会热气烔烔;撑不下来的,只好让它凉去。对那些有价值、无市场的文化形式,主动扶植,不使其凉下去,这——也是一种妥妥的“文化凉热观”!
情感注入
文学评论,怎样才能像文学作品本身那样,讨人喜欢?
有学者开出了处方:“论家强烈的情感注入,会使评论增加单靠逻辑和理性力量所达不到的生气、活力和魅力。”
呵,情感注入——还必须是强烈的!
我的记忆之窗,突然打开,回望到2006年5月7日,在江苏常熟沙家浜举行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
“沙家浜”三字,太吸引眼球了,京剧中——阳澄湖,芦苇荡;郭建光,沙奶奶;还有,阿庆嫂同胡传魁、刁德一的“智斗”,给我们留下一代人的记忆。在江南水乡,讨论西北文学,也很别致。许多知名学者,作家,都来了,贾平凹本人自然不会缺席。
我作为报社记者采访,全程参加了。
学术研讨会,顾名思义——学术味,逻辑性,理性力量——样样不能缺,但这回,我分明在耿直的学术味中,捕捉到了评论者的情感注入。
举其中几例。
比如,学者陈晓明注入的情感,是“复杂”。他说——“我对贾平凹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始终是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废都》的出版,是中国文学的视点。”“《废都》表示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重新出场,对社会发表看法。”“我今天依然对《废都》保持了批评。”“贾平凹从古籍文化中找到补充。”“贾是有裂痕的。”“《废都》张贴在历史之墙上,一旦揭下来,就破碎不堪。”“为何没有给贾以关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他还说:“《秦腔》恰恰与《废都》放在一起,才显出力量。”“其他作品没有与《废都》构成对话,只有《秦腔》与《废都》构成对话。”“《秦腔》是乡土叙事历史的终结,几乎没有叙事,看到乡土中国的散乱局面。”
作家叶兆言发言,因为是同行,彼此理解甘苦,深得个中三昧,所以用了“庆幸”、“羡慕”两个词:“我有一段写作很不顺利,看了贾的作品,他也不是很顺,很长时间不被人理解。”“为他感到庆幸,在20世纪,能写很长时间。”“作家成名前,成名很困难,但成名后,能不停地写,是很值得羡慕的。郭沫若过了五十大寿,变成郭老。茅盾后来变成茅公。我认为给贾平凹封个号是应该的。我至今依然喜欢《废都》,老天爷给他机会,写了这样一本书。”
作家苏童的情感注入,我听得出来,是“高兴”。他娓娓说道:“我们几个有点‘一小撮’的味道。为贾感到高兴。”“他写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烧,水在沸腾。这壶水持续了我很长时间对贾的印象。”“贾平凹作品是非常开拓的,最让人尊敬的是,声音都是嘟囔,非常个人、私人的,个人世界非常强大。”“作家一种是健康、向上的,一种是有病的。平凹是病态和健康非常完美的结合。他是内心散发出的,能支撑很长时间。对《高老庄》《白夜》是评论不够的。外界注意力的脱节对他来说是好的外在环境。向平凹学习、致敬。”
作家范小青,则明明白白,在讨论中注入了“得意”二字。她说:“读《秦腔》时很得意,这是不太多的,是有一种会意。历史与现实,人与事的把握极其到位。语言上讲,是很经典,无论从哪一页看,都能看下去。”“不是我写的,但觉得得意。”
学者栾梅健,在回顾现代文学史后,情感上注入了“喜悦”二字。他这样回顾道——“鲁迅是乡土文学的起点,是在那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的一片破败的景象里。鲁迅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故乡的画面,闰土的精神上的贫困。这是高峰、起点。后来迎来了新农村的生活,赵树理是代表。在党的领导下,农民欢天喜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家庄的变迁》展示明朗的农村,是第二个高峰。赵树理是单纯地歌颂。文革,乡土文学的第三个代表是以高晓声为代表,李顺大等一系列形象说明农民心灵受摧残。”“农村衰败,作家对农村隔膜了,面对农村巨大变化,看不到真正的好作品,在这种背景下,看到《秦腔》,有一种喜悦。”“在工业化冲击下,农村破败的当口,《秦腔》把农村艺术性地展示出来。《秦腔》与《故乡》《李家庄的变迁》《陈奂生上城》相比美,《秦腔》是第四个阶段。”
学者丁帆,一上来就讲:“当‘伤痕文学’盛行时,贾平凹写了《满月儿》;当莫伸写《窗口》时,贾平凹写了《二月杏》。”我听上去,他对贾平凹的“与众不同”,情感上特别认可,对《废都》的偏爱,观点上尤其执著。他这样说:“我认为,从文学史角度、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秦腔》不如《废都》。”“《废都》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很特殊的。”“对《废都》,大家只看到性,但脱了性的外衣,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阳痿问题。”他坚持认为:“作家在作品中的价值判断,没有对错,只是为时代提供了什么。所以《废都》是20世纪下半叶不可逾越的大作品。应从文学史上看贾平凹提供了什么。”
学者南帆,则对贾平凹的文人气息情有独钟。“我以为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不恰切,更倾向于用‘文人’这个词。”他说,“理工科知识分子有基本理念,西方社会训练出来的。但贾平凹的叙述策略中,中国文人的气宇是非常明显的,他的书法、绘画也是如此。平凹有很多‘文人’背景,恢复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趣味,‘笔记体’趣味很明显,更可归纳到‘文人’范畴,如《废都》与昆德拉作品的性趣味就不一样。”
学者孙郁,褒贬分明——先肯定“迷人之处”,继而否定“遗憾之处”。请听他的表述:“平凹作品的主人公有一种失败感,有一种鲁迅的传统,内心有黑暗,承认自己不行,无能。孙犁开始对他企盼,从平凹语言找到了一种质感,中国语言的灵动感。但后来平凹把恶毒、丑恶的东西弄到了作品中。”“《秦腔》有许多龌龊的东西,失败感,挫折感。”“关心病态是他最迷人之处。”然而,“遗憾之处:快乐在地下,没有飞起来。”“去国外洗过脑子的,写的东西飞起来,精神有灵动。”“在乡土长大的,虽没有洗过脑子,但也认为传统叙述方式有点问题。”“平凹有能量,有信息量,但没有飞起来。”
学者王尧,我听出他带有一点尊崇的心情。他那诚恳的语句,是这样组装的:“愿意称贾平凹为伟大的作家。”“我没有完全读懂《秦腔》。面对平凹那么多作品,面对混沌世界,一下子想不清楚。”“《浮躁》有历史叙述,后记写得特别好,后记表明他是散文大家。”“贾的作品中有许多被现代性压抑的东西。”“旧式文人的东西是我们文人的底色,聊以自慰的许多东西恰是文人化的东西。”
学者谢有顺的情感注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对批评家本身进行反思——“《废都》把无聊写得这么透彻,因而反思批评家,把道德作武器往往很粗暴,让人不可理喻!”
听完众人富有情感的评论,我看见贾平凹放下手中勤于记录的笔,抬起头来,思索一下,用浓重的陕西口音说:“批评都有道理,都是建设性的东西。写作是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不写也没事做。”“新时期浪涛特别多,自己老是慢一步,写出来老争议,给自己带来慌乱,但引起思考,是好事,对自己大有作用。梳理梳理,想想都有道理,回去好好琢磨。”
哦,注入情感的文学评论,拨动了被评论者的心弦!
会议结束,与会者们坐着多条小船,穿梭在芦苇荡,听水声哗哗,闻芦花芳香,望岸柳成行,感受“沙家浜”的历史氛围。我呢,坐在船里,心心念念:回去把那些飘溢着魅力的评论,写入报道……
沿途这一站
人生沿途,处处能看风景,也时时需要过关。
风景固然秀丽,过关却不轻松。达观知命者,便把过关也视为一道风景,开阔视野,洞见症结,陶冶素质,熬炼智慧。
有不少人,走着走着,来到沿途这一站了。
先来瞧瞧这里的风景吧——大厅里,一排桌子,摆得整齐,端庄,还带点威严。桌子后边坐着的人,西装笔挺,腰板笔直,代表着某公司人事部门的形象。一般人,是不会来这里的,唯有从网上给该公司投了简历,公司看了简历上的年龄、学历,特别是在外资企业工作过的经历,并且,从电话里听了英语表达的水平,认为可来面谈者,方能踏进此地。
面试——人生紧要的一步。跨得过去,别有洞天;栽了跟头,另谋出路。
有人淡定自若。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如履薄冰。有人百爪挠心。
“请先读一下你的自我介绍!”西装笔挺者开口了。参加面试者清了清喉咙,念起来,仿佛语文课上朗读课文,字正腔圆。
“你为何要换工作?”又问。
于是答以跳槽的理由。
接下来,问答题的内容就纷繁复杂了——问你以前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什么;问你引以为骄傲的主要业绩是什么;问你遇见过哪些有挑战的困难项目,又是如何去解决的;问你的强项和优势是什么,哪些方面需要提高;问你的想法中,在外资企业工作需要哪些素质;问你为何团队精神重要,请给些例子;问你如果加入我公司,会带来哪些贡献;与其他人比,你有什么突出之处,为何我们要选择你······
这比外语的口试难多了。我学生时期,学俄语,俄语口试是参加过的,无非是在学过的俄语句式中,挑一些考考你,回答得相当从容,还得到了口试老师的口头肯定——“阿特利奇那”(俄语:优)。职场面试,你即使把所有可能面临的试题,准备得周周全全——像编织一张没有缝隙的大网——却仍然有鱼,甚至大鱼,漏出网外,让你防不胜防。
有可能,让你卯不对榫,答非所问。
有可能,让你张口结舌,呆若木鸡。
像“在外资企业工作需要哪些素质”,真是见仁见智的,你把人类的优秀品质,包括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的“逆境的美德是坚忍”之类都搬出来,高大上是有了,但如果缺少了“团队合作精神”、“精益求精精神”之类,恐怕依然会扣分的,毕竟,西装笔挺者要的,是特定于他们公司的,与弗朗西斯·培根没有多大关系。
面试,长可一小时,短则五、六分钟。前者,可理解为有希望,需反复权衡、细细掂掇;后者,可理解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明显不合要求,立马走人。当然,临场应答自如,超常发挥,言简意赅,切中肯綮,赢得人事部门青睐,无须拖延时间,当场决定转给业务部门面试,再给老板面试,也不是不可能。
假如几个关口,面试都通过,就能签劳动合同。自然,三个月的试用期是免不了的。试用满意了,才能转正。
认真一点的公司,还会拨打电话,或者派人,去试用者以前的单位,做背景调查,核实核实——他说的话,是不是有哪句白的说成黑、黑的说成白;他自称拎得起来的强项,会不会偏偏是塌落下去的弱项······
人生沿途的这一站,比高速公路收费站,风景更独特。对高级白领的招收,面试更严苛——英语流利,电脑相当熟悉,对微软办公室软件都要熟稔,长相端庄(不能明说),表达能力强,沟通技巧好,善于倾听,说话有条理,对事物具备开放态度,不能小气,不能自以为是,要接纳别人意见,随时愿意学习新东西······
自然界,有风有雨,有雷暴。职场里,有喜有乐,有烦恼。反复考察,最后招进来的,也有变卦的,公司要裁掉他,他与公司打官司,说加班费没付,说裁人必须赔钱。有的风格高,原公司当经理,到本公司屈尊干主任级别,说“没关系,不在乎职位,关键看公司好不好”。到签合同了,说一声——“对不起,不来了!”
人生海海,潮涨潮落,云聚云散。优秀人才难以招到,来了又去了。“海归”派最吃香,几家公司同时去面试,挑一家收入最高者去投奔。老外回国去没工作,来上海干活就工资高,条件好,来了不想回去,而本地人又在成长,有的气量小的老外就排挤下面的人。有的老外不聪明,没素质,但老板却是他们本国人,就帮他们说话。
我的外甥女——严格说,是我妻子的外甥女——英语流利,做这种公司人事部门的经理,是绰绰有余的。如今,她在加拿大多伦多,做着房屋中介,这一口英语,足以让她得益终生了。
我这辈子,无须面试了。就像汽车,轮子滚动,往前驶去,身后那一站的风飙霈泽,少有兴致再去观赏了。
热烈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