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我从策兰自己的语言中来翻译策兰
记者:你的诗集《与此同时:新诗和诗选》由约翰·巴尔科姆(John Balcom)译成英文,将于2025年秋季由阿罗史密斯出版社出版。祝贺你!它得到了诗人亚瑟·施、简·赫斯菲尔德、罗珊娜·沃伦和弗雷斯特·甘德等人的高度赞扬,我也加入了其中。通过诗歌的艺术,你的作品超越了你的诗歌所在的黑暗历史的经历。阅读你的诗歌和翻译既是一种精神的经历,也是一种文学乐趣。柯盖特大学亚洲研究主任约翰·克雷斯比(John Crespi)教授说:“王家新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作为评论家和翻译家,对当代中国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家新的诗歌声音以其严肃、清晰和坚定而引人注目,它探讨了个人与历史、命运、文化传承和人性的关系。”
你的诗涉及许多文学和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奥登、策兰、杜甫、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多多、凯尔泰斯、米沃什等人,而这个名单还在继续。你还将叶芝、曼德尔施塔姆、策兰等人的诗歌翻译成中文,向国际文学界致敬。是什么特别吸引你去看这些诗人?它们在中国是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吗,就像它们在美国一样?
王家新:在文学的历史上,诗人们总是在相互寻找,这在杜甫与李白的时代早就开始了,只不过到了现代,中国诗人的寻找越过了传统的语言文化边界。至于是什么特别吸引我去看这些诗人,这里我想起了阿赫玛托娃,在她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不是别人,是但丁成为她的守护神。下面为她的一节诗:
对你,俄语有点不够,
而在所有其他语言中你最想
知道的,是上升与下降如何急转,
以及我们会为恐惧,还有良心
付出多少代价。
读了这样的诗,就不难理解我们的寻找和选择。显然,除了诗歌的艺术,在根本上,正是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自己在“上升与下降”之间“急转”的命运把我推向了这样一些诗人。我曾说过,在我遇到策兰之前,在我身上可能就携带着一个策兰,或者说策兰的创伤就内在于我们的身体,不然即使读了他的诗,我们也会与他错过。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翻译他们的作品(我并非一个职业翻译家),并在我的诗中与他们展开对话。与他们的相遇,首先出自一种最深刻意义上的生命的“辨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我们的“另一个自己”,甚至可以说,我爱他们胜过爱我自己,不然我不会放下自己的诗去翻译他们。在中国,有诗人说我通过这种有选择的翻译创造了一个我自己的“精神家族”,我想他们可以这么说。如果说这些诗人是星辰,通过我的翻译,它们升上了我的夜空,尽管它们照亮的不止是我一个人。
正是经由这种最深刻意义上的翻译,汉语中的奥登,汉语中的策兰、阿赫玛托娃,等等,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就像庞德对中国诗的翻译成为美国现代诗的开端一样。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重塑了一种现代传统,那就是“诗人作为译者”。我认为这不仅对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和文化都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后巴别塔”的时代,只有经过相互的不懈的翻译,我们才能把“巴别塔的诅咒”变成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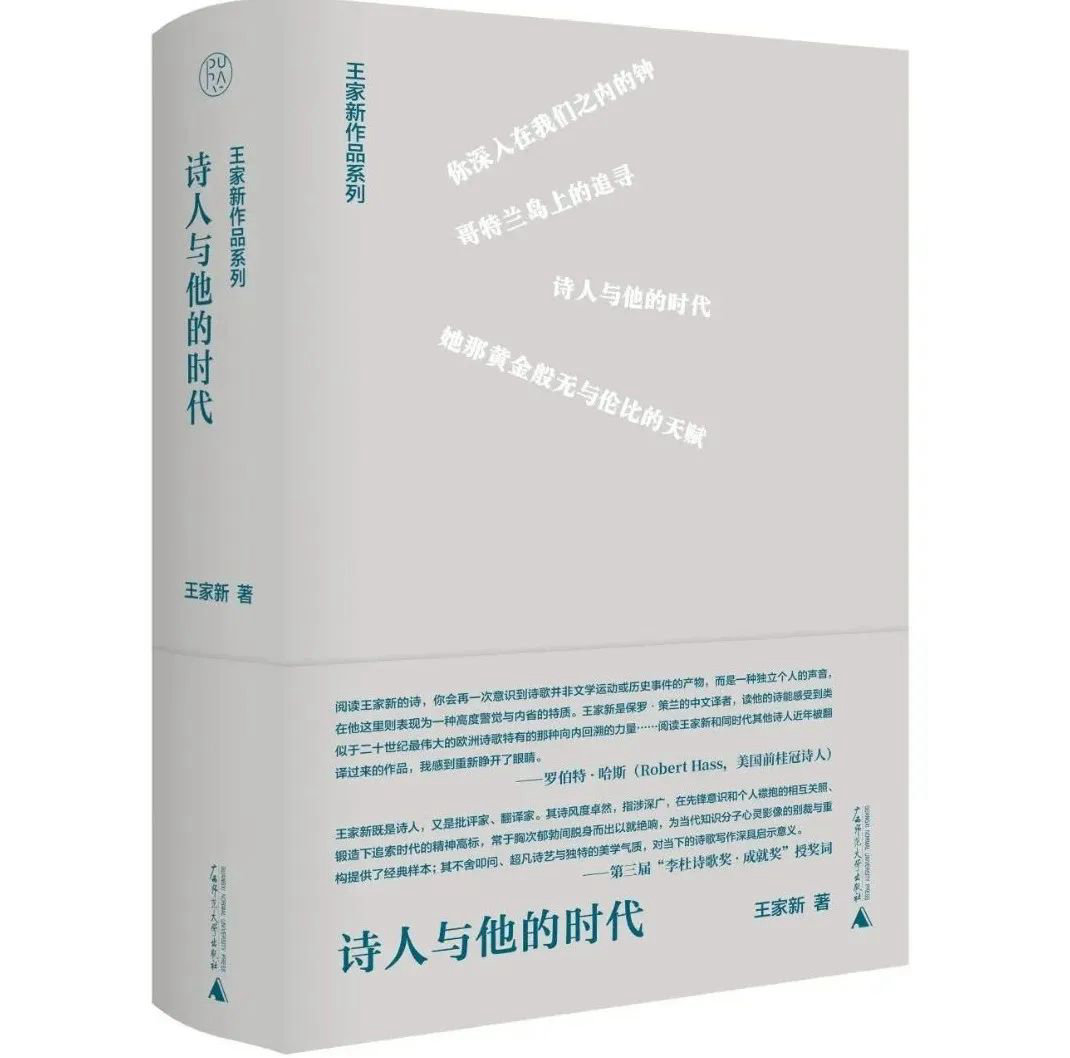
诗人与他的时代(王家新作品系列)
作者:王家新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3-02
2
记者:埃莉萨·加伯特(Elisa Gabbert)在她2025年1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典故大师:诗歌用典的艺术》这篇文章中赞扬了典故的使用。你能谈谈你诗歌中的用典,以及你在标题或正文中引用诗人的名字和作品的选择吗?当你提到简·赫斯菲尔德和阿瑟·施——他们都是当代诗人——以及像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过去时代的诗人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你在指老朋友。美国的垮掉一代诗人就曾这样做过,这种方式是否也出现在中国诗歌传统中?
王家新:说到“用典大师”(“Masters of Allusion”),许多中国古典诗人都是,比如说杜甫或李商隐,如同T.S.艾略特,他们都是“用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康纳德·艾肯评《荒原》语)的诗人。在他们的一首充满多种指涉的诗中,我们甚至得走过全部的文学的历史。
我的诗也常用典,不然你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仅把中国的传统引入现在,我们也是在一个跨语言文化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写作,在一个更广阔深远的文学历史时空下写作。比如我的一首诗《给保罗·策兰:基弗在巴黎的展览》,在这首诗中,我运用了一种时空交叠和意象并置的手法:奥斯威辛的阴影,可怕的气候变化,残酷的仍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等等,诗最后是“我们看不见的黑色太阳群在我们上空燃烧。”
这个“黑色太阳群”的意象,我想人们一读就知道是来自策兰(请注意,策兰“黑色太阳群”用的是复数形式,它比单数的“黑色太阳”更为可怖)。
这样的创作,和人们所讨厌的卖弄典故,炫耀学识不一样。我借助德国艺术家安瑟姆·基弗的展览和策兰的意象,是为了见证我们当下的存在。我的《在老子故里》一诗也是这样,在诗的最后,老子甚至与流亡丹麦时期的德国诗人、戏剧家布莱希特合为了同一个诗人:“如同布莱希特,一边听着/从收音机传来的故国的嚎叫声//一边用一支无用之笔/写下他幸福的流亡日记。”
总的来看,我在诗中用典,是一种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存在对各种文学资源的征用,目的是折射或共同构成一个诗的当下。另外,我还试图在这种用典中体现出某种特殊的诗意转化力,让它成为“创造之手的传递”。
对此,诗人弗雷斯特·甘德(Forrest Gander)看得很清楚,他在为我的《与此同时》写的荐语中一开始就说:“埃兹拉·庞德写道:所有时代都是同时代的。他那一代的主要诗人之一王家新对此表示赞同。”接下来他指出:“然而,尽管王家新的视角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但他的诗歌有一种深刻的个人性,生动独特,在形式上富有冒险精神。”
简·赫斯菲尔德在谈到我的诗时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借助他人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在场,引证历史是为了返回当下。无论我引用杜甫还是策兰,都是为了让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至于在我诗中出现的一些当下和过去时代的诗人,你感到我和他们都像老朋友一样,是这样,这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的建立,在我和他们之间也有一种精神上至深的亲密性。赠友诗(如杜甫的名诗《赠卫八处士》),或是在诗中与另一些诗人对话,这一直是中国诗的传统。我当然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比如我写有一首给伊利亚·卡明斯基和他的诗人妻子凯蒂·法丽斯的《“掰面包”》,该诗源自我们一起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的经历,这之后伊利亚给我来信说:“It is so good to have had the chance to break bread together”。这一下子点燃了我的“灵感”。不是在一起吃饭,而是在一起“掰面包”!我不仅我学到了这种如此美好的表达,我也把它发展成了一种文学隐喻:“我们一起从策兰那里‘掰’/从茨维塔耶娃那里‘掰’/从夏加尔那里‘掰’……”显然,这已和现实中的用餐不一样了,这变成了一种文学共享和相互传递的隐喻。
写出这样一首诗,我要感谢伊利亚。我们从别人的诗中得到激发,但又得像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只借那些可以加倍归还的东西。”
3
记者:你认为这种引用典故的风格(直接称呼,包括文本中的参考文献)对一首诗有什么作用,而不是使用尾注或题词?
王家新:对这个问题,我愿再以《“掰面包”》一诗为例。在诗的最后,我引用了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聋共和国”作为隐喻。《聋共和国》是他的一部广受注目的带有诗剧性质的抒情诗集,我曾把它译成中文出版。这样一个“聋共和国”,也就是“良心共和国”,在当今这个时代,用一位诗人的话说,它“照亮了我们共同的聋哑”。因此,这样的引用就是很有意义的,它增强和扩展了全诗的意义:我们这些在一起“掰面包”的人:“在同一张餐桌上/在那些围拢来的魂灵们的注视下//在一个挂有大红灯笼、人声鼎沸的/‘聋共和国’里……”
因为引用,这样的诗成为一个批评家们所说的“互文本”,但是,它又是自足的。其实,我们在诗中征用其它文本资源,同写入一棵树、一种生活场景并无区别,都是为了成就一首诗。也许,诗的存在是为了进入其他的诗。
引用好了,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所说的“神来之笔”。如我最近写的《航线:致简·赫斯菲尔德》一诗,这首诗从我的一次旅行开始:从东京转机到纽约。过了白令海,进入北美上空后,“我向下看到的,竟是皑皑雪山和冰川……” 这使我受到震撼,然后是我在想象中与住在北加州的诗人朋友简·赫斯菲尔德的对话(也根据我和她的通信):“你是幸运的,你走的是靠北极的北方航线,/不然你会看到满天烟雾。”这烟雾,是噩梦般的南加州山林大火,“圣莫尼卡的居民已被疏散,你知道,它就离布莱希特流亡时住的地方不远……”
诗写到这里,冰与火的“对位”出现了。“哦,布莱希特!从一场烟雾逃向另一场烟雾”。如果人们了解布莱希特在希特勒上台后逃亡的经历,了解纳粹分子的焚书和“水晶之夜”,就可以更多地知道这“烟雾”的意味。
然后仍是想象:“就在你忧心忡忡地察看火势和风向的时候,/我们飞过北海道,飞向阿拉斯加,/仿佛重返冰川纪”,就在飞机上接过一罐日本空姐递来的札幌啤酒时,我想起了我读过的川端康成的《雪国》,而“它的结局是一场冲天大火。”
就这样,我们的航线和我的思绪都穿行在这个世界的冰与火中。正好简在谈论南加州大火的来信中提到“我们生活在燃烧的房子里”。这条佛经(见《法华经》第三章),我在诗中引用了,或者说,我们所经历的全部命运让我在此刻理解了来自佛家经典的启示。燃烧的房子,燃烧的历史和命运,火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与虚无。
因此,“没有幸运的人”(“旁观者的眼睛即使在高空之上/也会被火星灼伤。”),这是在想象中与简的再次对话,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回应:“火舌飞进我们每一个人的房间里,/浓烟要让我们窒息。”我们以为可以逃脱历史和命运,但我们并不能。“浓烟”有着它自己的意志和让我们难以招架的诡计。
显然,这首诗有多条线索,有冰与火的对位,有着现实中的大火与一个旅途中的诗人在历史时空中的穿越,也就在诗的后半部分,一个可能最让人料想不到的细节出现了:“被烧掉一只耳朵的野兔早早就蹦进了/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一首诗里。”
这个细节出自伊丽莎白·毕肖普《犰狳:给罗伯特·洛厄尔》一诗。我翻译过这首诗。美国诗人们一读就会知道它的出处,甚至为此会感到意外的惊喜,比如诗人、翻译家罗珊娜·沃伦(Rosanna Warren)在给我的来信中就谈到这一点:“你的这首新诗很精彩,……还有那只野兔在毕肖普的诗里奇妙而机智的一跳!”
这个引用,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神来之笔”吧,我自己在动笔写这首诗时也没有想到。这个被烧掉一只耳朵的野兔只是毕肖普诗中一个灾难性的细节,我引用了它,但有变化,其意义在新的语境中发生了变化,也许还含有在诗中获得疗伤和庇护的暗示。这就是说,这首诗即使在见证这个可怕的世界时,仍包含着人们所说的“元诗”的因素:一首诗在讲述着它自己的诞生,也在思考着诗与现实,诗人与世界的关系。
而接下来的影射和用典,如格陵兰岛,“一场帝国梦的最边缘”,关注当下美国和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它在说什么,它也是这首诗的现实因素之一。“你的眼睛也就是一场火灾吗”,这是我对中国现代诗人穆旦《诗八首·一》“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的引用。穆旦的这首诗在中国很有名。当然,我的引用有明显变化,它也像特写镜头一样,在骤然间拉近了你与世界的距离。
这一切,直到通向这最后两句:“我的航线永远在/冰与火中穿行。”一首诗至此完成了自身。
我这样具体讲解了这首诗,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也向人们展现在一首诗、一种心智的复杂运作中,它是怎样把一些诗的材料,包括其他一些文本资源有效地纳入到自身的结构中。但是,也有其他一些诗人拒绝讲解自己的诗。比如说策兰的一些诗,甚至很短的诗,都有着多重隐秘的指涉,但他一概不加注,研究者只能从他的个人经历、通信、藏书和历史文献中找出其出处。他只留下诗的文本本身。他只是对读者说:“去读。”
是的,去读,一首诗读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一首诗可能也会通向很多诗。罗珊娜在读这首诗时就联想到罗伯特·弗罗斯特:“它在地理上和道德上都有着巨大的辐射——飞机机翼和雪的烟雾,洛杉矶大火的烟雾,佛教的烟雾,世界末日的火和冰。(罗伯特·弗罗斯特:有人说世界终结于火,有人说会终结于冰……)。谢谢你寄来这首诗。”
罗珊娜联想到的弗罗斯特的这句诗我以前读过,但写这首诗时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也许是因为在中国,在所谓“古老的东方”都有类似的说法,在佛教思想、在川端康成的《雪国》中都包含了这样的启示。也许更重要的,是冰雪与火,一直是我诗中的两个要素,它们不仅是我许多诗中的隐喻,它们构成了我真实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我会在诗的最后这样说“我的航线永远在/冰与火中穿行”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尾,也是一个永不结束的结尾。
4
记者:你把乌克兰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翻译时,你是从乌克兰语翻译的还是从英语翻译的?诗人兼翻译家W.S.默温和母语为原文的人合作,将其翻译成英语。你的过程是什么?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当你翻译的时候,你是逐字翻译还是根据字面意思来把握诗的节奏和语气?
王家新:伊利亚·卡明斯基早年来自乌克兰,但他移民美国后用英语写作,纵然他的英语是一种带着他个人的特殊音调、句法、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英文。他的《聋共和国》,我是从英文原版诗集中翻译的。
至于我翻译的策兰,基本上是参照德文原文、从英译中翻译的。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阅读和翻译策兰,从1991年第一次读到并翻译策兰,到2002年出版策兰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保罗·策兰诗文选》,到 2021年出版一个大型的《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它包括了近400首诗和一些散文和书信)。在最初我一点德语都不懂,后来也学了一些,并同精通德语的朋友合作对我的译文进行一些修订。虽然我强调翻译的创造性,但我并不认同罗伯特·洛厄尔的那种翻译(其实洛厄尔本人并不认为他的《模仿集》是翻译,而是“模仿”)。忠实可靠和精确,仍是我翻译的原则,而且我的翻译也是一种研究性的翻译。我的目标,是不仅要使我的译文在汉语中站住,而且要使它经得起从原文的角度来检验。因此即使在依据英译本翻译时我也很谨慎,我受益于一些英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精湛翻译,但也纠正了一些英译本的错误和译法,比如策兰的一首名诗“koln,am hof”,美国的策兰研究专家和译者费尔斯蒂纳(John Felstiner)译为“科隆,火车站” ,但它应译为“科隆,王宫街”,王宫街一带中世纪以来一直为犹太人的居住地和受难地,虽然它也靠近火车站。再比如英国诗人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Michael Hamburger)翻译的《保罗·策兰诗选》,是第一个在世界上产生影响的英译本。它的意义在于较早、较全面地介绍了策兰诗歌,但是他的翻译有时过于通顺,未能保留策兰的语言特质,比如他译的策兰名诗《花冠》中的一句“our mouths speak the truth”(“我们的嘴说出真实”),但德文原文为“der Mund redet wahr”(“嘴说出真实”),在原诗中主体并不是“我们”,而是“嘴”本身!显然原诗更有分量,也是策兰的特有句法和语言,在策兰的诗中,“嘴”“手”等身体器官往往都具有独立的主体性隐喻意义。
作为一个来自东欧、来自德语社区边缘的犹太人和流亡者,策兰的德语很独特,即使对很多德国人也很陌生和怪异,不仅是句法,大量的词也是他利用德语特性自造的词,在他的后期诗中,甚至充满了“语言的癫狂”。一个策兰的译者对此一定得有充分和深入的了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称策兰创造了一种“移居语言”(migrant language),伊利亚·卡明斯基称策兰创造了一个“策兰尼亚”(“Celania”)的语言国度。策兰自己在与妻子通信时则怀疑德国人会用他的这种德语讲话。所以,当有人问我是从德语还是英语翻译策兰,我的回答是:我从策兰自己的语言中来翻译策兰。这是我作为一个译者对策兰(也是对诗本身的)最根本意义上的忠诚。
一些中国诗人赞赏我的翻译,原因也正在于我翻译出了策兰的语言特质、语言的革命性、异质性和陌生性,翻译出了他作为一个德语流亡犹太诗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与正统的德语本身最隐秘和激烈的搏斗。
我对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翻译“过程”也正是如此。你提到W.S.默温的翻译,我很喜欢他本人的诗,他与人合作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翻译也使我很受益(只不过他有时把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过于“优美化”了)。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翻译诗的常见做法是诗人与学者或语言学家合作,其实这是庞德所开的“先河”,他对中国诗的翻译就是与一位已故汉学家的“合作”。我也研究过美国诗人斯坦利·库尼斯(Stanley Kunitz)与人合作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他对合作者的初译的修订和重译挽救了诗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好诗人参与翻译,为什么阿赫玛托娃本人会说“只有天才才能翻译天才”。阿赫玛托娃自己就是一位译者,她在生命最困难的时候曾与汉学家合作,翻译过中国伟大的流亡诗人屈原的作品。
至于你问到我如何运用汉语这种“有声调的语言”在翻译中创造一种诗的节奏和语气,我在翻译时是这样:首先是进入原诗隐秘的内在起源,咬准其“发音”,然后在汉语中替诗人重写这首诗,不仅如此,还要尽力使它在汉语中达成“更茂盛的绽放”。(这是本雅明谈翻译时的用语)
举个例子,曼德尔施塔姆的《给娜塔雅·施坦碧尔》,是他三年流亡生涯的最后一首诗。施坦碧尔是一位当地年轻女教师,她不顾危险和诗人交往并在后来保存了诗人的大量诗稿。曼德尔施塔姆本人视该诗为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甚至视之为他一生的“遗言”。
我的翻译基本上是直译,但不是那种拘泥式的直译。亚美尼亚的诗人和学者罗伯特(Robert Tsaturyan)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对照俄文原诗和英译分析我对这首诗的翻译。他高度肯定了我的翻译,说我的翻译“是尖锐而扼要的,甚至会感觉到它比原文更接近真实”,比如我的译文中有这样两句:“那抓住她的,在拽着她走,/那激励她的残疾,痉挛的自由。”(施坦碧尔本人腿有点瘸)罗伯特说“痉挛的自由”(“spastic freedom”)在俄文原诗的意思是“被克制的自由”(“restrained freedom”),但是,“如果我们敢于回到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痉挛的自由’可能比‘restrained freedom’更接近现实。”
这首诗的翻译不仅在意象的重写上,我也根据汉语的特性在节奏上做了处理,比如这两句诗的翻译,我把原诗流畅的一句从中断开,并赋予每一个意象和短句以足够的分量,这样在汉语中读起来也更有感情,更带有气场感和节奏感。重要的,是我必须使我的译文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声音相称,使它成为一种有张力的语言。
策兰曾把翻译比作一种危险的摆渡。一位中国诗人曾用这个隐喻来评价我的翻译:“作为一个诗人译者,他在一种最深刻的生命辨认中侧身而行,并以他精确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翻译,让我们在汉语世界里听到了‘那船夫的嚓嚓回声’……”
是的,我自己也喜欢这个说法,诗与翻译,“那船夫的嚓嚓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