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谈曾孝濂先生与博物画的前世今生
曾孝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植物画画家、邮票设计家、博物画画家。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科学画专业委员会主任。职业生涯中,为《中国植物志》等50余部科学著作绘制了2000余幅插图。应邀设计了11套邮票,《杜鹃花》《杉树》《君子兰》荣获全国年度“最佳邮票”。出版有《云南百鸟图》《云南百花图》《曾孝濂药用植物图集》《曾孝濂彩墨画集》《云南花鸟》《极命草木》等画集。(图为曾孝濂画像,徐洋绘于202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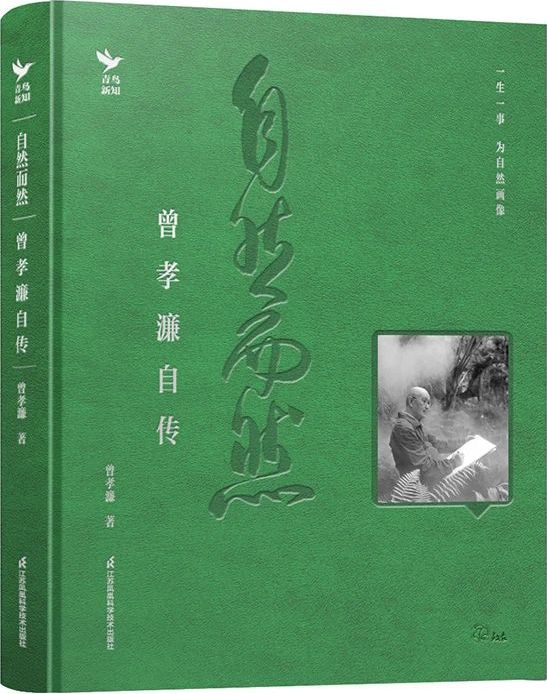
《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曾孝濂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7月第一版
记者:作为博物学文化在中国最重要的倡导者,也作为曾孝濂先生的朋友,先请您谈谈读《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的体会。
刘华杰:我第一时间拿到并阅读了《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的预印本。文如其人,质朴而有丰富的内涵,这部优美的自传为中国植物学史、植物科学画史、博物文化史增加了重要内容。许多年前,出版社曾有人建议,由我为曾先生撰写一部传记——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主题也是我感兴趣的——但因为当时我生病,无法拿出大量精力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就谢绝了。
记者:请谈谈您与曾先生的交往,以及您眼中曾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刘华杰:交往其实很少,时间也不长,但可谓神交。上个世纪我就知道冯澄如、冯晋庸和曾孝濂,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也向别人推荐过。我不会画画,那时对博物学还不太上心,由于领域不同,根本没指望有机会能够见面。第一次见到曾老师非常晚,是2017年2月在北京阜成门桥西南角的“自在博物”书店的一间教室中,宋宝茹女士组织了曾孝濂博物绘画班,我的学生王钊、杨舒娅等也参与了筹办和服务工作,我全程听讲。后来又见过两三次,也通过一次视频电话。最近的一次见面是在苏州,我们连续几天一起参会、参观。“博物学文化杰出贡献奖”评选过程中,在线上也有交流。我的感受是,曾先生智慧、厚道、谦逊。先生对我们晚辈总是爱护、鼓励,循循善诱,从来没有摆资格、拿腔调。先生很宽容,讲述自己的独特经验和技法时,仍然鼓励年轻画家坚持并发展自己的风格。
毫无疑问,曾孝濂是目前中国最伟大的博物画家,当然有人愿意叫科学画家也可以。我认为称博物画更合适,因为先生画的是活生生的宏观对象:动物、植物、鸟类、生态系统等。其绘画与当今自然科学论文中大量存在的科学插图完全不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奥杜邦画的鸟类博物画拍卖价格甚高,我觉得曾先生的绘画也达到了相近的水准,有极高的艺术与科学价值。
我知道,人们还想历史地了解曾孝濂在博物画、生物画或科学画领域的地位。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从容研究,比如做几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据我粗浅了解,中国近现代博物画家大致可以分出五代,各代相对独立,多少有一些重叠。这五代的代表人物分别是:(1)冯澄如(1896-1968),(2)冯晋庸(1925-2019)和冯钟元(1916-2011),(3)曾孝濂(1939- ),(4)杨建昆(1959- ),(5)余天一(1996- )。当然,这只是一种近似描述。之前岭南画派的居巢、居廉、高剑父等没有算入,原因是他们对物种的观察不够仔细,或者用今天的话讲不够科学(比如他们不太在乎物种的分类特征,许多藤本植物的手性画得不对)。
很自然,江湖上流传着冯澄如和曾孝濂地位相比较的种种说法,甚至有的人表现得十分激动,我愿意在此多讲几句。不明真相者愿意目击掐架,或者他们压根不想了解真相,也不管历史是怎样发展来的。首先,冯澄如先生是开山人物,而曾孝濂先生不是,辈分在那里呢。但他们两位都是杰出的画家,成就很大,性质不同。打一个比方,一个是伽利略一个是牛顿。伽利略是近代数理科学的开拓者,他一人同时身体力行经验方法和数理方法,对后世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影响巨大。牛顿是在伽利略基础上做科学(其实是自然哲学)的。如今在普通人那里牛顿名声更大。公平而论,伽利略和牛顿都是一流思想家、数理科学家,都有鲜明的个性,谁排第一第二根本不是个问题。非要笼统排个第一第二,必然阉割历史的丰富性,甚至制造若干麻烦。具体到每个观众,可能各有所爱,但个人爱好不可能改变它们的先后关系和各自的具体成就。的确有个别媒体人,为了吸引眼球,凭自己的一知半解,就写出了雷人的报道,冠以这个第一那个第一之名,明义上是在宣传曾孝濂先生,实则置先生于非常不利之地位,也引起冯先生后人的不满。据我所知,曾孝濂本人从来没有宣称第一或“泰斗”,凡是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是那类人,不会说那类无厘头的话。这类事也令曾孝濂先生很苦恼,先生跟王钊和我都专门说起过,希望澄清一下。就我个人看法,这五代人中,冯澄如和曾孝濂影响最大,都是大师级人物。理由也很好讲,前者是开山者,后者承前启后、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并在新时代将博物画带出了困境。
记者:曾先生自传写到人生经历,但更主要写到他的博物画事业。从195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站,逐步走上手绘植物之路,到改革开放以后在博物画领域大放异彩,再到近年来的“走红”,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几乎是新中国博物画的整个历程。您如何看待曾孝濂一人经历所折射出的这部“中国博物画的历史”?
刘华杰:说到曾先生一生的事业,需要稍展开一点,先把一些概念交待清楚。每种绘画都来源于生活,与认知和审美直接相关,服务于社会的特定群体。“博物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无论哪类,当代国人似乎都比较陌生,这与博物学在当代的地位是相称的,即都被系统地忽视,而实际上却十分需要。公平地讲,博物画要早得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博物画”而无“科学画”。要从多个时空尺度观察,才能看清楚博物学、博物画的性质、地位。与人们的直观印象不同,“博物画”概念相对明确,内涵外延清晰,而“科学画”反而不明确,指称混乱。如果以为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绘画就是“科学画”的话,现在中国人所说的那种画在当代科学中根本不占主流!当代科学论文的确大量使用精美插图,可以说90%以上与宏观物种没有关系,而是有关机制、过程、成果的说明图。不信的话,可以随机抽取100篇当代植物学论文,检查一下其中有多少插图属于一些人所说的科学画。如果讲究名正言顺的话,这些论文中的插图才叫“科学画”,而曾孝濂、马平、杨建昆、张渝等并不画这些。此外,科学史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久!在近代,随着资本扩张和全球物种大交换的进行,以观察、解剖为基础的近代博物学兴起,博物绘画空前繁荣。探险、物种收集及各门分支学科的推进,都需要通过绘画来记录和刻画。那时摄影术和彩色印刷术不发达,手绘和手工复制(铜版画、石板画)是很基本的手段。大家都知道,近现代自然科学横扫全球,科学技术做大做强,现代社会的各阶层各领域人士事后自觉不自觉地会从科学视角出发看待和评价一切事物。在中国,许多人甚至只听说过科学画而不知道博物画。18—19世纪以来,博物画日益服务于自然科学,相关绘画便被一部分人称作“科学画”。各种志书的编撰需要精准的物种插图,这类绘画空前发展。现代中国的此类绘画启动较晚,在美术界也未产生足够的影响,更不用说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了。当动物志、植物志、菌物志出版告一段落,这类绘画也就迅速衰落。要想不消失甚至有所发展,科学画需要复归博物画。这是我个人的梳理,不代表美术史、科学史的共识,但我知道曾孝濂先生赞同这一观点。有一年在北京的图书博览会上我们当面确认过,其自传《自然而然》中也有相关表达。
你说“中国博物画的历史”,我能理解其意思,也很赞成,但我估计许多人不知所云,知道了也未必同意。这都很正常,背景不同,看问题的时空尺度(scales)不同。先生完整见证了近现代中国“与自然物有关”之绘画发展的历程。我用“与自然物有关”的描述,是不想得罪一些人,也是为了让更多不清楚相关历史的普通读者迅速进入状态。简单说曾先生做的工作是画植物标本、植物活体,也画动物(主要是鸟)和菌物。但不是美术工作者一般意义上的绘画,而是接受了现代科学训练特别是植物分类学训练之后,建立在个人对对象细致观察基础上的绘画。这种绘画要求准确反映出对象的分类学特征,这对“舍象”是一项巨大的考验。一方面要舍弃大量信息,一方面要展现关键信息。也就是说对科学和审美提出了严苛的要求。科学性是前提,但不美观也不行。实际上它不是一种死板的工作,而是一项极富创新性的工作。与任何科学探索一样先要“建模”,与任何艺术展现一样要传达美感。博物画要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缺一不可。有的人前者强一些,有的人后者强一些,曾先生则是双强。
曾先生的工作做得非常棒,但之前只是在小圈子中有影响,普通大众不知道,也没有机会知道。那为什么后来变得非常火,各种媒体争相报道?这当然离不开近二十年博物学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复兴的大背景。这个大背景有扎实的物质基础(中国走向小康社会),与诸多学者的大力推动有关,更与各领域无数一线实践者的努力有关。一旦进入良性循环,因果就会互动。最近几十年曾先生的画作主要不直接服务于自然科学,而是服务于广大公众。科学界对曾先生的宣传并不是最卖力的。也很好理解,现在过了编写植物志、动物志的黄金岁月。说得不中听点,以曾先生为代表的“科学画画家”相当程度上被当今科学界所忽略,如果不用更难听的“卸磨杀驴”一词的话。当年的绘画队伍解散了,这是基本事实。但是,也不必悲观、抱怨。曾先生是乐观派,积极行动起来,言传身教,推动了当代博物画的发展。

华山松 1980 年 纸本 毛笔线条+刻刀
记者:中国古代有蔚为大观的花鸟画传统,我们今天谈的博物画与花鸟画有什么不同?李时珍《本草纲目》、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朱橚《救荒本草》等中国古代的植物学名著都有绘图,但似乎未见出色,您觉得原因是什么?西方现代博物画的兴起要远早于中国,以西方为参照系,您如何评价今天中国博物画的发展状况?请您简要谈谈。
刘华杰:花鸟画是广义的博物画。今日的博物画要求与花鸟画有所不同。博物画要求反映对象的分类学特征,而花鸟画通常不这样要求。花鸟画的程式化比较严重,对大自然本身的观察显得不足。当然,这只是一般性评论,有个别例外的。
提及中国古代植物学名著等都有绘图,这很好,就像提及中国古代有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一般。但是,不得不承认,到了后来,人们才发现我们的科技水平非常落后,对大自然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原因是什么?人们立即想到李约瑟问题。其实不必事事都扯上李约瑟问题。历史上,中国不缺少聪明人,智商不低,但是学者终其一生都在做什么?早的不说,明清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有多少人在认真观察自然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地研究?少得很。西方在近现代则非常不同,他们采取经验主义或自然主义策略,扎扎实实地观察、测量、记录,在此基础上推理、交流、批评、前进。“西方近现代博物画”发展得极好,树立了标杆。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放在那里,无需争辩。但并不是没事可做了,也不是说他们的创作水准已达极限,无法再做出新成果,绝对不是。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也不全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他们也吸收了全世界的成果)方式方法,也能创作出同样优美的博物画,特别是对象是西方不曾画过甚至不曾想象过的物种。
说到“今天中国博物画的发展状况”,有两句话。第一,具备一些条件,势头不错,曾先生为此做出了无人能比的贡献。第二,人才培养上缺乏有效的传承体系,未来怎么样,只能走着瞧。我个人的建议是,多举办博物绘画展览和比赛,多办培训班。博物画的发展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服务。

曾孝濂设计的《杉树》特种邮票
记者:您说过更喜欢黑白线条画,为什么呢?
刘华杰:这是个人偏好。黑白线条博物画早期适应于铜版雕版及其复制发展起来,技术相当成熟,应用范围颇广。古典的博物画都尽可能用“排线”表示边界和明暗,这与后来的“打点”方法很不同。前者难度更大,需要事先在头脑中完成某种奇特转换,要有较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和绘画经验积累才可能做好。排线法绘出的博物画确实有非凡之美,与摄影作品区别也最大。博物画并非越像原物就越好,那些画得极像照片的画,可能并不很好,至少我不喜欢,对于展示对象的核心分类特征也有缺陷。曾先生1975年的《木棉》和1976年的《泡桐》是排线法的经典之作,线条简洁、优美,结构清晰。无论是泡桐果实较暗的表面,还是木棉花较明亮的花瓣,曾先生都用独特的线条表现出来,仔细观赏,令人叹服。排线的设计,需要非凡的“舍象”能力和艺术转换功夫,特别考验创造力。而“打点”法,操作相对直接些,容易学习;当然也需要“建模”,即化简对象,但不像“排线”那样复杂。比较而言,排线法容错率低,打点法容错率高。曾老师的徒弟之一田震琼(花老道)的排线功底也非常好,他的钢笔排线加淡彩作品苍劲有力、几无废笔,看起来硬朗,自然而然“入木三分”。一般意义上的黑白线条图,也适合初学者尝试。
记者:近年来,曾先生通过办展、开设绘画班等形式推广博物画、传播博物学,我们也看到,如今,像余天一、李聪颖、裘梦云等一批年轻的博物画家正迅速成长起来,您如何看待或者期待博物画的未来?
刘华杰:曾先生说自己想创作更多作品。时间对于先生自然太宝贵了,但先生愿意拿出一定时间培养年轻人,这是了不起的举动。新时期中国植物画、动物画或者说博物画,每一次重大的活动都有曾先生的身影,先生以创作者、受访人、策划人、导师、顾问、评委等多种身份参与其中。国内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人。另外,作为一面旗帜,曾先生的号召力非常突出,应当高度评价。
记者:在摄影、摄像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博物画的价值是否会有所削弱?
刘华杰:不会,一定意义上,价值还在变大。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考虑,人类会越来越尊重自然物、生态系统,会多种形式地表现、赞美大自然,博物绘画便是其一。坦率讲,论细节,绘画不容易赶上摄影,但是绘画仍然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无论科学还是艺术,在展现大自然时,都是基于某种模型,建模有取舍也有建构,有忽视也有加强。在一定意义上,绘画可以表现得更好。比如图书封面用图,摄影作品通常不如绘画有味道。对于普通人,现在拍照太容易了,不妨试着画一画,这样能够提升观察能力。
记者:作为普通公众,假如读《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而对曾先生、对博物画发生兴趣,您是否可以推荐一些相关的读物给大家呢?
刘华杰:《芳华修远》(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又见芳华》(人民邮电出版社)、《花神之宴》(北京大学出版社)、《花朵与探险:玛丽安娜·诺斯的艺术世界》(中信出版集团)、《探赜索隐:博物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山川纪行》(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西方博物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回归生活的博物绘》(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