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冶:我想写的是一本关于推理文学“元认知”的书
卢冶,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资深推理迷、推理文学研究学者,她曾在《书都》杂志开设“推理+∞”专栏,在“三联中读”开设付费音频专栏《推理的盛宴——与侦探一起发现60次在场证明》《推理小说面面观——敲开侦探之门》。近日,其新书《推理大无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卢冶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解读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前生今世,梳理了推理类型的不同流派和主题,并就推理作家的叙事技巧等做了相关剖析。澎湃新闻就书中内容及中国原创推理发展、推理小说AI写作等问题专访了卢冶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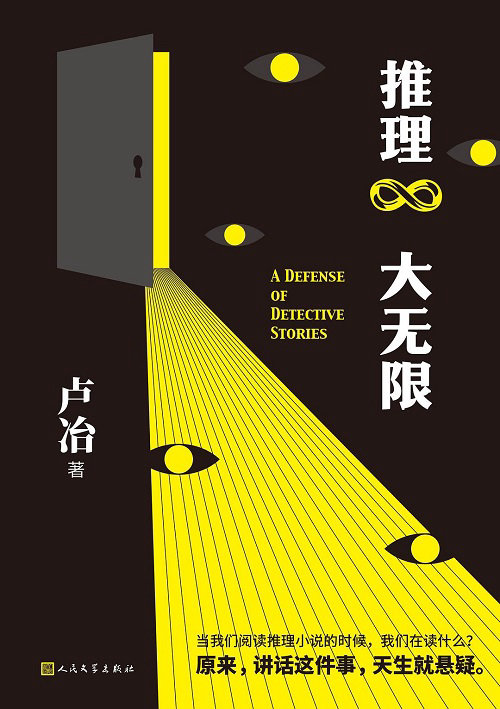
记者:您在书的序言里就开宗明义地说:“本书并非正统的侦探推理文学批评集,也不会提供面面俱到的推理小说介绍”,而是试图解决诸如:我们为什么对推理小说上瘾?如何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精神财富?——这类的问题。在您看来,在持续不退的“推理热”之下,这些问题是不是比单纯的评论或者梳理作品更有价值?而这种解读是不是也有为其辩护、正名的意图在呢?
卢冶:哈哈,的确有一点辩护的意味。在人类对知识的分类当中,有一种知识比较特别:是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我们可以叫它元知识、元认知。元知识关注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它何以被创造出来、又如何影响了我们。用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跳出山来看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写一本关于推理文学的元认知的书,要对它打一个问号,而不是在推理文学内部、理所当然地探讨它的书。单纯的评论或梳理作品,是在推理文学的“山”里,看山是山,关注的是“然”,而非“所以然”。如果读者只是对推理作品的故事本身感兴趣,只想满足看这类故事的爽感,对于自己为何会感兴趣这件事本身不感兴趣,那么如今市面上关于侦探推理文学的文本分析,包括短视频平台上的推理文化科普都已极其丰富,就不需要过多关注这本书了。遗憾的是,因为我准备不足,这本书并没有达到我自己关于元认知的定位,缺欠很是明显,今后,我会努力弥补这遗憾。
记者:谈到推理小说,总是绕不开对本格派和社会派的比较,您在书中谈到,两者理解和再现现实的方式不同,其根本的分歧可能在于侦探的行为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问题最终的“解决”,您能就此略作说明么?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才使得本格派的作家无法被所谓正统文学史青睐?作为本格的拥趸,您觉得这种文学史的选择是否偏颇?
卢冶:这一点在理解上确实有些困难。如果读者想要深入了解我的思路,可以去读一读哲学界的当红“炸子鸡”齐泽克解读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相关著作,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人类面对“现实”时的思维路径。按照这种哲学解读,现实并不总是那么“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在乎客观世界,因为我们从本质上都是活在自己的感受和认知当中。而故事总是在折射我们的一种心态:希望控制和把握些什么,否则就会产生无力感。但什么叫做具有控制力?不同的认知分岔就从这里开始了。有些社会派作家对于现实的认知可能要比本格派天真,因为他们的故事是建立在理想很浪漫但现实很骨感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们认知当中的社会是复杂庞大的网络,而个体是渺小无力的。他们致力于描述的,是渺小个体对庞大社会的抗争所激发出来的颓废浪漫,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诠释,是一种美学,但却会被很多人解读为“更具现实感”。也就是说,当你对现实的认知是建立在这种二元划分的基础上,你就会觉得社会派的描写是更真实的。但为什么我更欣赏本格派的天马行空呢?可能是因为本格派更接近我心中的“元叙事”。对于元叙事来说,并没有一个绝对“现实”作为基底在支撑故事,而是但凡我们能解释什么,能认知什么,就意味着我们的控制力延伸到了哪里,而我们无力解释、有意无意忽略的那些,总是如影相伴。所以本格派不怕把侦探写成万能神,也不怕人物“脱离现实”,因为它的参照系本来就可以不是“那种现实”。
恰恰是由本格派,才发展出当今颇为流行的一种亚类:设定系。只要有一个限定条件,就可以打造一个世界,在其中必然因特定的规则而产生特定的谜团。从本质上来说,这看上去是另开脑洞,但从深层来说,反而可能更接近我们每个人处理现实的方式。
至于文学史的选择是否偏颇?这里有一个悖论:只要是主流,就一定是偏颇的。哈哈。我们对现实的解读,就像纸上的一个点,被无限放大,而我们喜欢把它当成世界本身。这的确是人性的惯性,但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如同古人说的,告诉自己,你所认知的世界,不过是片云点太清,说不定就能发现其他的解读。
记者:在推理小说作家中,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可能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东野圭吾了,在这个汰旧率这么高的小说门类里,您觉得阿加莎为何能一直经典?而东野圭吾又为什么能一直流行呢?
卢冶:可能要补充一点:这两位作家的地位在不少中国读者心中可能是并置的,但在欧美国家或推理文学比较繁荣的日本或许并非如此。不同国家图书市场上所反映的“经典的流行文学有哪些”的差异是非常惊人的,根本不可能找到统一认识的“世界流行文学史”。但如果是从全球知名度来说,东野和阿婆一定是无法相比较的,他的知名度更多是在亚洲打响,其中离不开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日本推理文学的奖项加持和较为频繁的影视改编。从全球来说,至少他还没有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考验——时间是检验文学文本是否能成为经典的一个过硬标准。从因果上来讲,我会说东野跟许多作家一样,是阿婆他们这一代作家的种子传播后开出的新花。东野的流行,实际上也反映了黄金时期推理作家叙事力量的强大。所以我会把这个问题压缩为:阿婆为何足够经典?
作家需要最大限度地与读者共情,这种共情力越强,对读者的摄受力就越强。但共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讨好读者。纯文学作家常常让你不舒服,这恰恰也是共情力的体现。作为通俗作家,阿加莎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让你在舒适中被打动。我们对舒适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对于多数人来说,读起来不费力但有获得感,一点仪式感、氛围感和套路都是舒适的一部分。阿加莎就在这里经营。如果要用绘画来比喻,她的作品常让我想起荷兰当代画家哈勒曼特的静物画:东西很少,但有品味,都是被保养很好的旧物;空间小而静谧,令人觉得很安适。当破案的拼图完整后,它总是能让你想起一些熟悉的、古老的神话或童话,人类的故事早就在那些原型中被写完了。
当你读阿加莎时,你可能想起莎士比亚,但当你读东野时,你会想起阿加莎。将一种原型发挥得淋漓尽致时会发生什么?就像在希腊神话里,当英雄的经历足够精彩,就会被天父宙斯放到天上,成为星座一样。
这就是阿加莎为何会经久不衰——她由学习星座起,直到成为了星座之一。
记者:我们知道,在经典本格中,解谜的形式感非常强,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童谣、人偶这类与儿童相关的意象甚至是小孩子本身常常成为故事里令人恐怖的信号,这是什么心理机制造成的呢?
卢冶:对此,精神分析学、认知心理学,可能都会有很多话要说。我在书中主要是从“自我内部的他者”来解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恐怖谷效应,就是像人而非人。这个角度是很容易理解的。还有一些对大众来讲比较玄幻的讨论,就是儿童角色总与谶语挂钩,因为孩子代表了某些先验性——先于此生的东西。
从大乘佛学中的法相宗(唯识学)的角度来说,人在四十岁以前的遭遇,多数来自前生的等流性,也就是前世因果啦。当然,这是宗教的看法。但大家在平时生活中,也常感叹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小孩子身上的确会有明显的、并非来自于父母遗传或教育或环境的天赋特性,这些带来了小孩不同于老人的宿命感——后者的沧桑是经历了此生积淀的,也就是可以解释、有因可溯的。
——所以儿童身上的神秘之感,是因为它延伸到了科学至今未竟的先验之域。
记者:您在书中多次提到推理小说中传奇与日常性的辩证法,在这个以“传奇”为抓手的文类里,“日常”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应该以怎样的面貌和尺度呈现呢?尤其您提到“日常推理”中,真正的主人公是日常性本身,这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卢冶:如果不是以熟悉撬动陌生,或者用陌生来引发熟悉,那么所有的阅读快感都不可能产生。我们阅读推理小说,是希望对治生活中的无聊、呆板、枯燥、常规,但真正打动我们的,难道会是完全脱离我们所熟悉的人、事、地、物、完全没有认知抓手可言的陌生谜团吗?当然不是!如果有那样一个世界、那样一个案件出现,我们要么会感到不可理喻,要么就不感兴趣——因为感受不到它跟我们自身有何关系。不能建立关系,也就无从建立乐趣。前面也说了,人是意义的动物,解释意味着掌控、熟悉,也就意味着重新回到或建立、修复一个舒适区,也就是说,对人来讲,万事都要回到日常。古人说,穿衣吃饭,无非是道,这个道,就是以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内在观察打量熟悉的日常事务,让熟悉变得陌生,让陌生再转化为熟悉,这就是我们建构意义、追求快乐的主要方式。
日常推理其实就是基于我们的这种心态而产生的:还有哪种新奇能比从我们熟悉的寻常事物中得到的新解释更新奇呢?还有哪种对传奇的追寻能比“我原来不用到远方追寻,我就活在传奇中”的认知更令人振奋呢?所谓日常,如果是“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就不用再哀叹日常的枯燥无聊一地鸡毛,而是像侦探一样,每天都活得兴味盎然了。
记者:您在书的最后专辟一章讨论了侦探推理小说的伦理问题,这其中既有对这个与凶杀犯罪高度纠缠的文类本身的伦理问题的厘清,更谈到了面对社会现状的无力、无解感对这种类型小说解压功能的冲击,包括法外快意恩仇的终结、科层制之下无从追索的恶等等,您觉得这样的社会心理变化给推理小说带来的更多的是创作困局还是新变的契机?
卢冶:是新变的契机。有新的压力,推理的谜团才能前进,才能产生新的动力。人类的文学来自于面对困境时的选择方式,困境不变化,选择就不进化。所以今天的推理文学早就不再遵守早期的那些规则了,侦探一上来就死了和没有侦探的故事比比皆是,但谜题还是能成立。
记者:刚刚也提到了,这些年无论是从影视、小说创作还是出版情况看,国内的“推理热”一直没有退潮,反倒大家的口味是越来越挑剔了,就您的观察而言,原创推理小说整体的创作水准和发展特点如何?与国外,比如日本相比的话,差异或者说差距在哪里?
卢冶:我认为,中国的原创推理发展最大的一个瓶颈,不在于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中国人从来不缺想象力),也不在于对推理文学的经典太熟悉,陷入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之中,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自我设限,在于对这个文类的信念感不够。我们说,演员表演时,需要强大的信念感,文学创作也一样。中国科幻文学已经产生了信念感,而推理文学却没有。尽管推理文化热一直没有退潮,我们有推理书店,有推理游戏,有剧本杀、密室逃生这些商业化的推理悬疑元素,但大众对这类文学一直缺乏一种由尊重、认可产生的信念感。作家得不到读者的尊重,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鼓励(比如推理界的文学奖项的设立不够、社会认知度也不够),也会在创作上随波逐流而非引领大众。归根结底,还是对这个文类的元认知不足,同时,从外部环境来说,推理文学创作和出版的生态环境的确相当艰难,导致作家更担心读者群,担心社会批评,总是束手束脚。这些因素内外夹攻,让推理文学的交流仍然难以离开自我圈层化的活动。而且日系轻小说和游戏在阅读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却也为中国作家的创作带来一定的问题,特别是文风的问题。
我希望中国作家能加深信念感,更多地向中国传统的笔记宝库汲取营养,此外,山川地理,宇宙星辰,历史、国家、家庭、社会、身体、信仰,无不是推理文学创作的题材,不用怕资源枯竭,不必担心读者买账与否,先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别忘了,嗷嗷待哺如我的读者大有人在,推理之门已经在中国打开,场子已经热了,向前走,别回头!
记者:在科幻小说界AI写作、甚至参赛获奖已经屡见不鲜了,而推理小说同样是创意、诡计高消耗的类型文学,对于推理小说AI写作的问题您有怎样的判断呢?
卢冶:我们发明AI是为了让它们为我们服务,这在文学创作上是同理的。如果没有我们与AI对话,它们就无法更新创作模式,所以AI参赛的背后,仍然是人在参赛。我始终认为,心能转境,工具就是工具。一些需要占用内存很多、需要大量重复的操作就交给AI好了。对于推理文学来说,很多时候重点都不是诡计本身,而是诡计被适配在怎样的情境中,与怎样的读者产生互动,所以就算把一些诡计的处理交给AI又能如何?更不必担心AI会取代推理作家(除非AI产生自我感。我认为,一旦AI产生自我感和丧失感,它就是一种生命)。AI无论如何创作,也无法替代我们的恐惧、焦虑、希望、患得患失,而我们在文学中真正希望看到的正是这些——它们属于生命和死亡。就如阿加莎和艾柯所认识到的那样,幽默感来自于人类对死亡和伤害的认知,AI可以伪造出幽默,但你一定会觉得有点别扭。阿加莎的确创作了一些套路,所以依照现有的庞大资料库,我知道AI一定会创作出一篇标准的阿婆式谋杀案小说,但相信我,我会分辨出真伪——只要我仍有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