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县城里所有生命,都是主角
藏在县城里的大千世界
记者:和万樱一样,您在县城有四十年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历了一个迅猛发展的阶段。小说这样写道:罗小军觉得云落越来越陌生,“云落犹如正在褪壳的螃蟹,旧壳尚未完全剥离,新壳正随着风声慢慢地氧化,没有人知道这只螃蟹是否还是原来那只螃蟹,唯一能确定的是,它的心脏依然是从前的心脏。”
哲学上有个“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对于县城,这是一种思考,还是一种担忧?
张楚:当一艘船的全部零件换完后,它还是不是原来那艘船?这还真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人也一样啊,人体的细胞大约7到10年全部更换一次。那时,我们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70年代中国的县城基本没什么楼房,街道、人们的衣服,甚至天空都是灰扑扑的。我曾在小说中无数次写过我生活的县城(滦南)。或许有些读者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非常传统、陈旧的北方县城。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的拆迁、改造,以前只存在于都市的高楼大厦在县城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时,我带外地朋友回老家做客,他们都感到非常震惊,觉得这不像一座县城,而是一座三、四线城市。
与人们缓慢的、渐近式的精神变化相比,城市的改造速度实在太快了,短短几年可能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中国县城的迅猛发展,我整体还是比较乐观的。未来,县城的个性也许逐渐消弭,南北方城市不再会有太大差异,但只要人们能在其中获得幸福感,外在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与都市的疏离感不同,县城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浓稠,既是县城的迷人之处,也是其窒息之处——县城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我们既能在小说中感受到小说中各个角色倾力互助的温情。但也不能忽略,万樱怀孕后抗拒堕胎,甚至以死亡逃避;蒋明芳情人猝死后不敢报警,都是因为畏惧县城中的流言。您觉得,在人际关系逐渐疏离的当下,这会成为当下年轻人回到县城的阻力吗?
张楚:传统的县城其实和乡村一样,都是典型的熟人社会。
当人们在一个狭小空间内生活,不由自主地会寻求相互帮助。比方说,你在县城里生了病,首先可能会想到哪个同学在县医院里工作?他在哪个科室上班?这种无处不在的熟人关系网可能会让人有某种安全感,但它可能也是对当地法律、规则、隐私的一种破坏。
现在县城里的年轻人确实在减少。但我反倒认为主要原因是一些新兴的大都市对孩子们更具吸引力,他们渴望寻求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而并非事关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记者:在并不大的云落县城,看似处于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都能同台登场。细读小说,罗小军正是穿针引线的一枚重要的“扣子”。
全书41章中,以罗小军命名的章节就多达7章(“罗先生的食与色”“罗先生的烦心事”“罗先生去了娘娘庙”“罗先生的黄金夜”……)将县城各色人物串联起来,这是一开始设计好的吗?为何让罗小军来承担这样的功能?
张楚:这确实是一开始就设置好的。小说动笔之前,我做了一个详细的大纲。具体每个章节由谁来主导,都有分工。万樱、天青、罗小军、常云泽是推动小说剧情的四个主要人物。
罗小军当然是小说里极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曾是万樱的一个噩梦,也是她渐渐喜爱的一个少年。对万樱来说,罗小军是她精神世界的一个白马王子也好,或是一个佛陀也好,但始终能影响她的行为。
你提到以罗小军命名的章节有7章,但实际以他视角讲述的章节还有更多,出场的次数仅次于女主角万樱。罗小军和万樱就像珍珠项链里的两根线,他俩拧在一起,把所有人物串了起来。对小说的起承转合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罗小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体现大时代下,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和未来,以及关于他们的思考。生活中,我经常接触到各行各业的朋友,通过交谈,他们也会和我倾诉在经营上的一些困境和苦恼。因此,我也特别渴望塑造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形象。罗小军就是这个形象的代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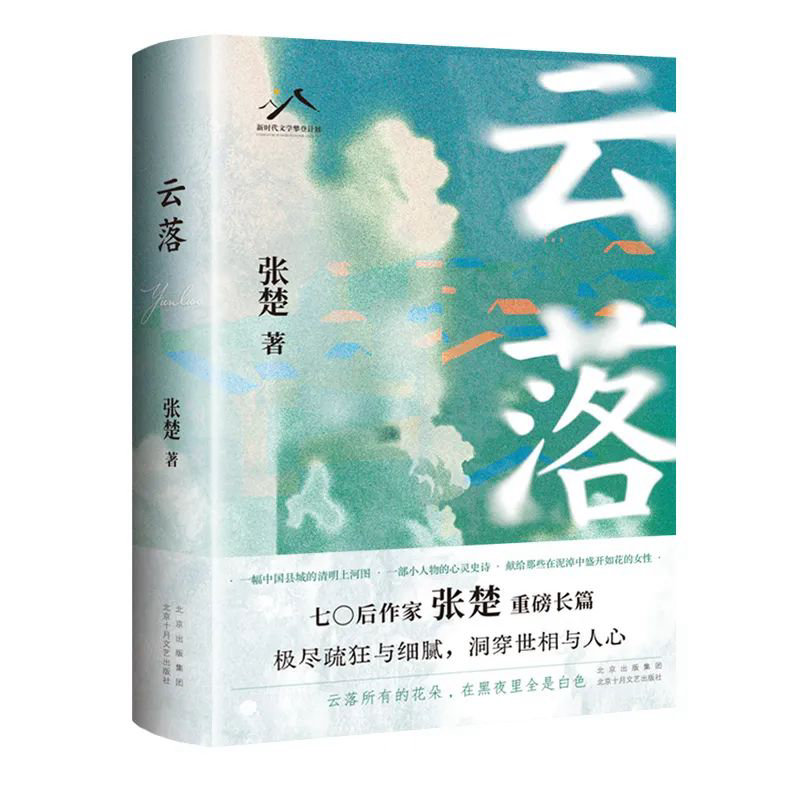
大寒节气知多少
记者:《云落》是您首部长篇小说。从中短篇创作到首部长篇,无论是语言上,还是结构上,您感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楚: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在创作上可以说截然不同。短篇小说可能来源于你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一个片段,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短篇小说的叙事性相对是最弱的,但它的诗意却是最浓的。中篇小说则要讲一个比较结实的故事,包含比较强烈的戏剧冲突。而长篇小说,除了这种诗意和戏剧性,它往往还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命运感。
其实我们很少考虑短篇小说的结构问题,它就像一滴水滴在了纸上,慢慢晕染开去,最后形成了一道水痕。中篇小说可能水花更大一些,形成一个涟漪。而长篇小说可能更像湖泊、大海,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质的区别。所以长篇小说的结构就尤为重要。
在《云落》里,我其实采取了一个复调结构,四个声音交替在叙事。甚至同一件事,也会有A面和B面的不同表达。每个具体的事件,在不同人眼都有不同的意义。这种复杂性和多义性也正是我想通过小说对人性的深度探索。
记者: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小说中许多角色的过往经历,以不同字体出现在章节最后。为何采用这种叙事手法?
张楚:小说部分章节最后的楷体部分,其实就是一则人物小传。这是当然小说中的一种技法,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一个人从童年、少年到成年,直至性格的形成,中间有太多故事了。如果全部按照正常顺序穿插在小说里,必然会影响到小说的叙事速度和阅读体验。
所以我就想用轻便但完整的方式,把人物的成长经历和他(她)的当下性巧妙地联系起来。读者读到这部分,即使略过,也不会影响对小说的整理理解。
记者:是的,这些人物小传读来非常耐人寻味。初读小说,有个不太讨喜的角色叫睁眼瞎,对她印象并不好。等读到小传时才发现,她的性格形成也是有迹可循,甚至值得同情的。
张楚:你注意到这篇人物小传,我还挺开心的。有几个朋友都和我聊过睁眼瞎,在往常的小说里,这样性格的角色并不多见:一方面她敲诈万樱,但当万樱陷入家庭危机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帮忙。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唯利是图,但还是有情有义的人?
这个段落特别短,但对睁眼瞎来说,太重要了。
我上初中时,听大人们讲,县城里有个女工,她丈夫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离婚时对她说:“你把孩子给我,我带他到大城市,他会受到更好的教育。”你想,她多舍不得自己孩子,但还是把孩子给了丈夫,自己一个人生活。几年后,前夫得癌症去世了,继母又将这个孩子送回了我们县城。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不禁想,一个女人经历了生活的反复捶打,她可能逐渐变得自私自利,但善良始终是她的底色。写睁眼瞎时,我的感情还蛮复杂的。
记者:在阅读体验上,《云落》是一部和当代没有距离感的小说,王者荣耀、美团外卖、直播带货等新兴词汇在小说中多次出现。
对于新兴词汇或网络词汇的运用,向来有不同看法:一方面可以体现时代感,但随着汉语词汇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许多词汇也很快被时代淘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会担心五十年后,当人们拿起《云落》时,需要给王者荣耀加个注释吗?
张楚: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在一个中篇里用了许多当时很火的流行词,这确实会带来一些写作的新鲜感。可等过了两年,我再去读那篇小说,就觉得很突兀。当时那些流行语,成了与小说气质不太相符的存在。
所以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对这类词汇的运用是审慎并有所甄别的。
我始终觉得,名词对于长篇小说非常重要。当名词嵌入叙事,它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醒目标识,更可能会成为我们深层记忆的一个“唤醒器”。王者荣耀、美团外卖、直播带货可能已经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记忆人数超过一定范畴,就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它不会像泡沫般轻易消散,而是构成了我们时代记忆的一部分。
其实不光是这些名词,所有有名字的事物,包括植物的名字、鸟儿的名字,我都会在小说里事无巨细地写出来。因为它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和主人公一样重要。
万樱、罗小军固然是传统意义上小说的主人公,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小说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主人公——云落这个县城的所有生命。
小说人物会选择自己的命运
记者:读完《云落》,我脑海里最初浮现的,就是“饮食男女”四个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小说中,无处不在写人的各种欲望。
但《云落》中呈现的欲望却非常干净。您曾说过,万樱是给这个世界缝缝补补的女性。在泥泞的生活中,她所展现的始终是善良、美好的一面,如同“大地之母”般托起了许多不堪。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角色?
张楚:许多读者,包括责任编辑也问过我,为什么要塑造万樱这样一个角色?她长得并不很漂亮,对异性的吸引力就会弱一些。小说里,至少有三个女性对她有好感,有些类似友情,有些类似亲情。大家可能会说,万樱如果更漂亮一些,这个设定是不是更有说服力?但我要说,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女性。她长相普通,但极具亲和力,你愿意跟她接近,吐露心声,把自己一些不堪的过往或故事告诉她。
而且在我的理解里,万樱就是美的。她那种宽容敦厚,对人不设防备,即使身处悬崖还不忘对别人施以援手的性格是最吸引我的,可能我骨子里也是这样一个人,愿意把美好的事物和别人分享。
借用一句流行的话:“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万樱在笨拙地缝缝补补。”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需要这样一种人,让周围的人感到光、暖和爱。否则,人世间就真的太残酷了。
万樱的主要原型是我弟弟的一个小学同学,一个长得矮矮胖胖的姑娘,她是单亲家庭,经常被别的孩子欺辱,但她内在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你能感觉到这个矮矮胖胖的小女孩在拼命往前奔跑,跑着跑着,她就长大了。我和她不太熟,打过照面,甚至没说过话。她未来的生活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处于困境?还是会光明坦荡?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期盼——我特别希望她过得好,过上幸福、明朗的日子。
小说里每个人物都会选择自己的命运。万樱跑着跑着就成了小说里最后的样子。我始终对她充满了无限的热爱。
记者:对于万樱/樱桃这个人物,您不仅是热爱,几乎是偏爱了。从《刹那记》《樱桃记》到《云落》,樱桃可以说是与您一起成长起来的。
《云落》的最后一章,停留在万樱写给罗小军的一封信里,信里充满新的希望。我们不禁好奇,樱桃的故事,讲完了吗?
张楚:这封信我修改了一二十遍。因为长篇小说不能过多留白,每个人物的归宿需要有一个交代。这封信就是注脚。
而当我幻想着万樱用小车推着孩子去公园散步,就觉得特别开心。万樱一度认为自己流产了,但她最后还是生下了和云泽的孩子。我真心觉得,这是整个世界对她最好的安慰。罗小军进了拘留所后还没有判刑,他们之间维持着书信往来,其实也蕴含着她对罗小军的某种期待。
对罗小军而言,万樱的吸引力更多源自一种安全感、信任感,更像一个特殊的异性朋友,而非男女之情。当然,罗小军出来后,两人会不会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这封信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我以后还会不会写万樱的故事?或许可能不会了。我在心里已经和她道别了无数次了。她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安慰,我也不想再参与她的命运走向了。
但或许某天,我会觉得和她还有个约会。这大概就是文学的魅力,一切皆有可能。
记者:尽管《云落》被誉为一部女性的心灵史。但小说中男性角色的塑造也非常丰满。比如常云泽这个人物,他既有仗义和温情,也有狠辣的一面,很符合我心中对燕赵游侠的印象。这个人物最后的猝然离去,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张楚:当一个小说家变成一个“杀人犯”,而这个“被害者”是他亲手塑造又特别喜欢的角色,他一定是痛苦的。
说实话,写到云泽弥留之际,他感到万樱在给自己擦拭眼泪的时候,我特别难过。我喜欢这个人物,他死的时候我非常舍不得。
其实一开始我是准备让天青走向死亡的。身世之谜对他而言已经无关紧要了,死亡反而更像是一种解脱。随着小说的推进,死亡的天平才发生了偏移。
云泽进入商场时才刚刚结婚,我本来不想让他多管闲事,可他骨子里那种义气性情又让他自己做了那样的选择。当他以这样一种特别憋屈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我替他感到不值,我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但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小说人物会选择自己的命运。这是云泽自己的选择,我也没有办法改变。
记者:《云落》的故事告一段落。对于那些陪伴了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物们还有什么想说的?能给读者透露一下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吗?
张楚:小说刚发表后,几乎一年的时间我都有些伤感。那时候单行本还没出来,我经常会看看电脑里的文稿,好像依然和他们在对话一样。
《云落》从构思到完成大概花了6、7年时间。漫长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和小说里的人物打交道:白天我用文字记录他们的生活,深夜,他们闯入我的梦境,我和他们的关系就和亲人一样。人都是情感动物,当你与朝夕相处的多年的人们挥手告别,内心的伤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知道,我和他们的缘分也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我可能会写一部以天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它也会涉及北京、河北等地的多重叙事,目前正有这样的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