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我希望成为契诃夫那样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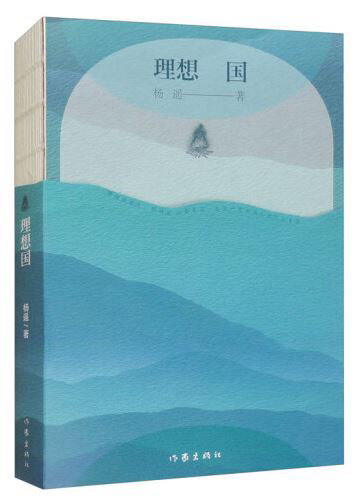
《理想国》,杨遥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读杨遥的小说,总想起贾樟柯的电影,叙述平实缓慢,不甚明亮的色调,略带忧伤的故事……我也出生在山西,同为70后,对杨遥的故事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
和杨遥一起参加采风活动,也一起喝过汾酒,闲时却聊得很少,倒是听鲁院的同学聊起他的故事,表面憨厚的杨遥其实率性幽默,在作家中颇有人缘。真正熟悉起来还是通过他的作品。杨遥的作品像陈年的老酒,醇厚而芳香清冽,需要细品才能咂摸出其中味道。他的叙述很有耐心,像埋头耕地的农民,一锄又一锄,深深地凿开干枯的土地,把文学的种子随着梦想和汗水一起埋入。几十年过去,如今这种子已生根发芽,并且繁花似锦。杨遥的作品频繁地见诸报刊,获得各种大奖。最近他的小说集《理想国》出版,仍是他惯有的风格,叙事平静甚至不加渲染,却扎实有力,有时候分不清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笔下那些小人物也写得平实真切,卑微却不乏坚韧。读杨遥的小说,会感受到他对于笔下痛苦迷惘、挣扎着艰难生存的各色人物,满怀深切的体贴和关爱。
杨遥是一位真诚的作家,“我创作时力求把真实生活和虚构生活都描绘下来,尽量让他们做到浑然一体。”在回答我关于小说实与虚的问题,他坦率地说,这恰恰是他努力的结果。
记者:你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吧?不知道为什么,读你的作品,总想起他的电影,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
杨遥:贾樟柯的电影我都看过,我喜欢他的表述方式。《理想国》出版前,我请贾樟柯给我写了推荐语。也有朋友说我的小说和贾樟柯的电影很像,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觉得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都像镜头,只要把它们准确地写出来,排列组合,自然会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就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想我和贾樟柯都是小地方出来的人,都很敏感。我们脚下的土地孕育了我们,不管她好与坏,我们都是吮吸着她的乳汁长大的,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她的基因,她的喜怒和爱憎。
记者: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和文学结缘?有没有文学的引路人?
杨遥:1999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滹沱河边的一个小村落当老师,我不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便开始写作。早期的写作完全是自发的,我的文学引路人应该是我的妈妈。她是位农村妇女,但非常喜欢读书,从小就给我讲故事,讲她听来的故事和书本上的故事。2001年,我第一次发表小说,得到鼓励之后便一直坚持。
记者:是不是有一些作品直接来自阅读的启发?比如《隐疾》,你曾谈到是读完《尤利西斯》之后,创作上有了新的变化?
杨遥:有些作品来自阅读的启发,多数创作来自灵感。我读完特别喜欢的小说后,总想写一篇类似的,但不是模仿,写出来之后读者根本看不出来两篇作品之间的渊源。读完《尤利西斯》曾经很绝望,觉得连里面的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乔伊斯写得太准确、深刻了。我便学习他怎样观察生活,怎样选择有意义的事件,后来发现要遵从人物的内心世界,要真诚。有了这些认识,慢慢练习,写作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记者:谈谈最新的小说集《理想国》吧,编选有何标准?集中第一篇《黑色伞》是哪年发表的?这篇小说里提到的黑色伞很有年代感了,其中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比如把蛇皮袋子折一个角进去,当成雨衣。
杨遥:《理想国》收录的是近几年我比较喜欢的短篇小说,只有《父亲和我的时代》一部中篇。《黑色伞》发表于2015年,用蛇皮袋子当雨披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事情,那时农村家庭基本都没有伞,一下雨大家就把蛇皮袋子折起一个角来当雨披。我的小说中有很多关于童年、少年的故事,因为时间隔得久远,我对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意义看得更清晰。
记者:《炽热的血》的叙事耐心令人感慨。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包括《黄河远上》等作品,总有一些没有反抗能力(或即便反抗也终以失败告终)的人物?
杨遥:在我早期的小说中,激烈的细节比较多,近年来作了调整,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时候在忍,因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这样做。快意还击比较刺激,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一般人付不起这个代价,这样书写是理解生活之后的选择。
记者:中篇《银针》用套构的叙事方法,讲了两个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先是通过医生陈永生的回忆,讲父亲在一次医疗事故中的故事;又通过一个男人的回忆,让我们看到父亲医术的高明。可以治好他人的病症,却无法医治愚昧和偏见。你在写作的时候,会特别注重叙述技巧吗?
杨遥:怎么写和写什么一样重要,主题和内容确定之后,应该思考怎样表述,就像运动员跑步时,怎样跑会影响比赛成绩,文学作品也一样,好的作品叙述和主题是非常协调的。
记者:《大鱼》里开店的夫妻、《头顶一片云》里的下岗职工……你的小说始终关注平凡的事物,这些人物也许活得卑微,但是始终有一种生命的韧性,对逆境、对命运有一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很想了解你的创作状态,是否这也是你面对生活的一种状态?
杨遥:因为我就是“小人物”,我的父亲和众多亲人、朋友,基本都是小人物。他们在生活中生活,很少遇到波澜壮阔的大事件,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丰富的情感,代表着中国的大多数。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同情他们。他们面对各种生活困境,努力活得更好,我喜欢他们,力求把他们写好,这也是写好我自己。
记者:《父亲和我的时代》是一篇主旋律作品,写山乡巨变写得非常巧妙。能谈谈你是怎么构思、创作这篇作品的吗?
杨遥:写《父亲和我的时代》时,我在北京读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办的研究生班,听了很多老师的课,常常引发许多思考,我意识到很多人把“主旋律”矮化了,《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和契诃夫等人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主旋律作品,他们讴歌真善美,歌颂人民,倡导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我便想写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写出《父亲和我的时代》之后,我更加确信,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谁能真正写出赋予人力量,弘扬人类优秀品质的作品,就占到了文学的最高点。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努力。
记者:你喜欢户外运动吗?《理想国》里写的行为艺术,让我想起纪录片《荒野独居》,你的小说集里经常涉及到户外运动,包括装备等描写得很细致,这是不是你的个人喜好?
杨遥:我喜欢户外活动,买过很多装备,帐篷、背包、登山鞋、登山杖、冲锋衣、软壳裤、抓绒衣、瑞士军刀等。我曾徒步五台山大朝台,骑自行车去过太原周边所有地方,在汾河里裸泳,最大的愿望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和穿越罗布泊沙漠。我认为和自然交流比和人简单得多。但我没看过《荒野独居》,《理想国》设计出父亲住在笼子里,是联想到现代人的处境。
记者:你在记录和表达时代的各种密集细微的表情和情绪,也会给笔下的人物透出一些光亮。这种“光”是你小说中很重要的精神力量,你在写的时候是有意让这“光”照进来吗?
杨遥:我写小说,会有意让“光”照进来,因为在生活中,常常因为一点小小的暖意,就会让人鼓起生活的勇气。在《头顶一片云》中,在《大鱼》中,我都写了“光”,我写了花儿渐次开放,绿篱焕发了生机,人们开始重新生活。
记者:写作多年,目前是否还会遇到创作的瓶颈?
杨遥:创作瓶颈一直有,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把想到的内容很好地表达出来,面对这个瓶颈,我的经验是不停地写,一边不断地实验,一边向优秀的作品学习。写《隐疾》的时候,我觉得写出了《尤利西斯》里面的句子,最近在写长篇,感觉有些地方有了《战争与和平》的微妙。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记者:你平时如何开始一篇小说的写作?故事的走向是预先构思好,还是靠灵感激发?
杨遥:开始写一篇小说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是一本书的激发,比如读鲁迅、汪曾祺、卡佛,常常会产生创作冲动。有时候是一个念想,比如那年去圆明园,在福海边忽然想起个小说题目《在圆明园做渔夫》,后来写了这个小说,发表在《长江文艺》上。有时候是一个概念,想写某个主题,比如《黄河远上》,但大多是靠灵感激发。
记者:有没有文学的偶像?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
杨遥:文学偶像选一个的话,我选契诃夫。他用谦卑的文字写出了俄罗斯的众生相。他写的《萨哈林旅行记》改变了俄罗斯流放犯的命运。他还身体力行,帮助了很多人,做了许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作家。
记者:你对自己的创作有规划吗?
杨遥:有时候有规划,创作早期写过“鸟镇系列”,后来写过“大院系列”。今年计划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离弦》,另外这些年想完成两个系列,一个是“理想国”系列,写人在各种处境下的理想;另一个是写一部人在不同年龄段面对的不同主题,最后出本集子,像《都柏林人》那样,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够用。
记者:你如何看待文学对于自己的影响?
杨遥:文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婚姻、我对世界的看法。没有文学,我现在可能仍然是乡村教师,可能会凑合着找一个没有共同爱好的人过一辈子,可能对生活的理解比现在狭隘许多。文学让我的世界扩大了无数倍,让我在各种艰难面前有了力量,让我的生活总充满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