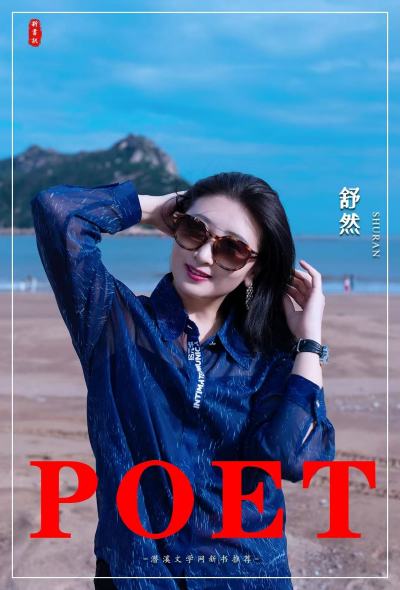张陵:小说是野生的
多年以前,曾经编过作家谭歌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令我不忘。他说:“小说是野生的。”现在读甘肃作家弋舟的小说,又想起这句话。他的小说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从“野地”里长出来的。这并非说,弋舟小说不管不顾,一味疯长,而是说他的小说更多地吸取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这片“野地”里的营养,长出了自己独特的小说花朵。现当代小说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和技巧,也培育了相当稳固的阅读模式。不过,如果过度信任这些技巧与模式,也会进入误区。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小说成熟的技巧正在掩盖作家们远离百姓生活、沉迷个人“小圈子”的空虚与苍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需要质朴的“野生”小说的冲击。
据我所知,弋舟虽然第一次出版小说集,但他的写作年头并不短,也写了许多好作品。他的小说作品不断在省内外获奖,说明他很有读者人气,也很有思想艺术水平。我在编审中发现,他其实很懂得小说的技巧和表现方法,也就是写实功底很扎实。不过,他并不过分受制和迷信于技巧,坚持从人民生活这片“野地”里汲取创作资源,坚持把普通民众当作小说表现的主体,真情实感地写他们的命运,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小说集中的《我们的底牌》《天上的眼睛》等就很能说明他的思想坚持。坦率地说,我个人是比较偏爱“野生”小说的。现在生活层面很多样,文学也就很多样,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对“野地”有兴趣,会写出“野生”作品。一个作家,要有这样的坚持可是不容易做到——需要道德良知,需要使命责任,更需要思想。
现在的文学偏重于流行时尚消费,如果形成潮流,就得检讨反思一下我们当代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因此,特别需要那些与时尚流行格格不入的“野生”文学。我们除了在这种文学里感受清新的生活气息、新的人物风貌以外,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新鲜活跃的思想冲动与热情,从而更真实深刻准确到位地认识我们的现实社会,认识我们的生活进步,认识具有先进价值的文化。这些活生生的东西,只有“野地”能提供,只有“野生”的文学能表现。如果我们的文学失却了这些鲜活的东西,那么文学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如果任其流行时尚的文学成为文化的主体,那么民族国家的文学离终结也就不远了。这话说得让人不怎么爱听,不过,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并不特别深奥,听听并无害处。
从这样的思想层面上,我读弋舟的小说,对他小说中真实生活形态的描写会有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在我编审的这部集子里,他似乎很关注凶杀与犯罪。他笔下的平民生活描写总是会和案子联系在一起,但却不是刻意展现案件本身。他不是在写流行的犯罪或警匪小说,而是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好像我们周边危机四伏,缺少基本的安全感。这样的关注点,很容易出现片面。不过,我宁可相信他的这点“片面”。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时代,不安全感是一个普遍的民众心理。他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样的生态,是以他的思想为支撑的,而不是任意编造。当然,他的小说中平民的暖意和力量也是在这样不安全的关系中表现的——“片面”又多了一层人文诗意。
此时,正值文艺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8周年。《讲话》在中国文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群众确立为文艺的表现主体,希望广大文艺家投身到人民群众伟大的生活之中去,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思想创新,也是新中国文艺立足之根本。这一创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实践,积淀了深刻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伟大传统将延伸下去,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作家在继承它,因为无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变化,这片“野地”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