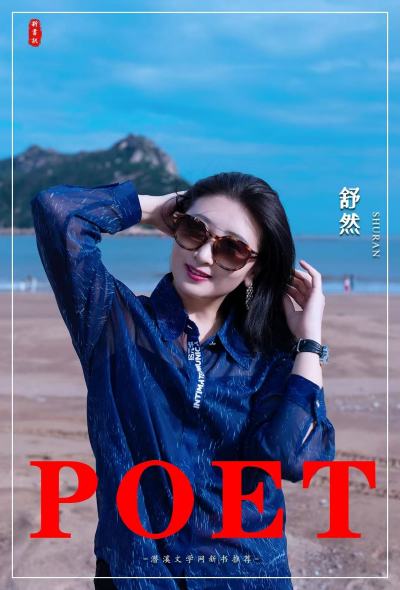江艺平 吴承学:《冰壶秋月》序跋
《冰壶秋月》序
◎ 江艺平
1987年,我和吴承学结婚第五年,他去了上海读博士,我在广州当记者,我们住报社宿舍,家中别无长物,惟书多。那时日子清贫,聚少离多,心中却充满希望。
一转眼,我们结婚已经38年,承学也已经是大学教授,读书依旧是最大癖好,终日手不释卷,却偏偏惜墨如金,一辈子做学问,出版专著屈指可数。我笑他无望“著作等身”,他告诉我,他的导师王运熙先生,年轻时写论文篇幅并不长,提出的观点至今无人超越。有先生榜样在,承学写论文轻易不敢动笔,思虑至极辄如老僧入定,待初稿既成,修改更费工夫,他希望多听不同意见,学生常常参与其中,有弟子指出可改处,为师的必喜不自胜,时时说与我听。
虽然和承学是大学同学,对他的研究领域我却不甚了然。他读博士就选定尚属冷门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直至把冷门做成热门,自己也成为学科带头人,个中甘苦却很少说起。我们夫妻之间,更多的分享还是来自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亦缘于此,他的随笔写作更得我心。
承学写随笔往往缘事而发,性情文字,少见清词丽句,却显朴茂深挚。1989年,他的导师黄海章先生去世,他在复旦读博,无法送别恩师,写下《冰壶秋月》发表在羊城晚报。当年读这些文字,远隔千里,也能触摸他痛彻心底的悲伤,从此一袭黑衫一身清气的海老形神毕肖镌刻在我的心底。而海老耳提面命的古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也镌刻在承学心中,成为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漫漫求学路上,上苍对承学何其眷顾,一路走来,总能遇见最好的老师——黄海章先生超迈脱俗的淡泊,邱世友先生古风犹存的正直,王运熙先生温润如玉的良善,傅璇琮先生宅心仁厚的宽容……透过承学的笔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们为师为人的纯粹,一直影响着承学。所谓润物无声,莫过于此吧。
承学从1992年开始招研究生。弟子们脾性禀赋各异,家境学识不一,在承学眼里,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意味着“因材施教”需要投入更多时间,花费更多心血。承学并不吝惜于此,每有弟子学成,专著出版,请导师写序,他都务求写出每本专著、每个作者的独特之处。写序之难,难在知人论世,我读承学为弟子作的序,犹见弟子性情模样,想起师生之间的趣事往事,不禁莞尔。平心而论,承学要求学生其实颇严,甚至近乎严苛,尤其见不得对学问轻慢敷衍。我理解他良苦用心,惟求学生学有所成,不虚度人生,不泯然众人。
人生在世,要做到不泯然众人委实很难。承学用一辈子的努力做学问,也用一辈子的努力做自己,一辈子的努力悟透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他把这句话用作一本学术专著序文的标题,也融化在平日的所思所行之中,包括各种场合的言辞里。
“宁作我”就是做自我独立的人。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总免不了要作这样那样的发言,张口就说冠冕堂皇的话,说“政治正确”的话,是不少人的“明智”选择。然而言者滔滔,能让听者入耳入心,又有几何?想独抒己见,说点逆耳忠言,且做到一针见血,就需要一点勇气,一点襟怀,一点见识。承学出生于50年代,家世坎坷,际遇沉浮;受益于80年代,得遇良师,终成学业,独特的人生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培养了独立的价值判断,凡事经过自己大脑思考,而非人云亦云。所谓“我口写我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在北京“长江学者论坛”的发言《长江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对“长江学者”这一光环日渐变味乃至名利叠加的社会现象坦率直言,有反思反讽,更有自责自省。按世俗眼光,在此场合,作此发言,显然不合时宜,承学却心怀坦荡,丝毫不以为忤。
有独立思考的真诚之言,自有其价值。承学随笔之深得我心,亦基于此——对现实勤于思考,勇于批判,写作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夫妻相伴走过大半辈子,回想起来,我这辈子做传媒,也得到过承学不少帮助,虽然他从未对此写过片言只语,我们之间却拥有弥足珍贵的共同记忆。这记忆关乎我们的理念,关乎彼此的师友,即使从不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知道,承学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在儿子年幼时没能陪伴更多。生而为80后独生子女,儿子的童年是孤独的,承学在上海读博士,每次送他离家,在开往广州火车站的公交站前分别,年幼儿子都免不了嚎啕大哭:“我要爸爸!”5岁那年,寄宿幼儿园的儿子思家心切,约了一个小朋友,白天侦察地形,半夜爬树翻墙,穿越大街小巷逃回家。幸亏那天我没出差,听到儿子拍门叫嚷还以为做梦。天亮后,急忙用自行车把两个“小逃犯”送回幼儿园,那边已乱作一团。现在回想起来,后怕之余,也着实感激80年代的良好治安。
承学的遗憾其来有自——他有六个兄弟姐妹,虽然家境贫寒,且因“家庭出身”饱受白眼,幸有国学功底深厚的父亲,还有父亲收藏的许多古籍,承学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发端于此,亦由此奠定了他日后的学业根基和事业根基。三十多年前,我随承学回潮州省亲,曾记下一个小片断:“丈夫的兄弟姐妹多,一屋人围炉拥坐,盈耳都是年轻人的说笑。公公总是眯起一千多度的近视眼,把笑意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守住陶壶茶盅,终日一语不发。公公的头发稀短斑白,一副木讷守拙的模样。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丈夫,探身过去,躬低了宽的肩,垂下一头浓密的黑发,向老人讨教,常常寥寥数语就点破迷津。”
这样的家学渊源和父子学缘,在承学和儿子之间已经难以延续。上小学就熟读《三国》、《水浒》、《西游记》,参加全国小学生作文竞赛拿过奖的儿子,不知从何时起,对枯燥刻板的语文教育生出厌恶,最终高考选择了生命科学专业。今年春节我们到波士顿探亲,除夕之夜,儿子郑重告诉小孙子:“小时候,爷爷让爸爸长大了当医生,爸爸现在就做了和医生有关系的工作,能够帮助到生病的人。”80年代出生的孩子,常常被父母告知长大了要当医生,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情怀和情形。儿子并没有辜负父亲期望。至于小孙子,在他心目中,认得许多汉字,会打“中国功夫”(太极拳),会写毛笔字的爷爷,更让他着迷。
人生就是这样,岂能事事如意。当你生出一种遗憾,没准会收获另一种满足。就像儿子,虽然未能延续家学,却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就像我,虽然看不懂承学的专著,却能够分享他的随笔。
感谢上苍赐给承学著书立说之余另一副笔墨。现在,他将其中部分文字收集成书,我一再阅读,感触纷纭,书生本色,依然如故。
2020年春节于波士顿
《冰壶秋月》跋
◎ 吴承学
这些文字,是数十年间因人、因事、因书而作的,虽无意为文,皆有感而发。鸿爪雪泥,往事如水,纵时过境迁,而中心存之。
全书分为三类,文章编排大致如下:“忆语”类是对家庭与家乡、老师和前辈的回忆,以及治学上的感想与寄语。“札记”类为读书心得,综论置于前,个案则以时代为次。“序跋”类以前辈、同行、后辈、本人之著作为先后。
我的妻子江艺平并非学术中人,只因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对文字养成特别的感觉。她不但了解本书作者和所写的事与人,更是书中许多文章的第一读者。我一贯对文字颇为较真,但写出文章,经其过目,仍能发现可改之处。往往删一字即显简练,增一字顿见韵味。我们共同生活数十年,相濡以沫却甚少言谢。本书特意请她写序,只想借此机会,说出“谢谢”二字。
庚子之秋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