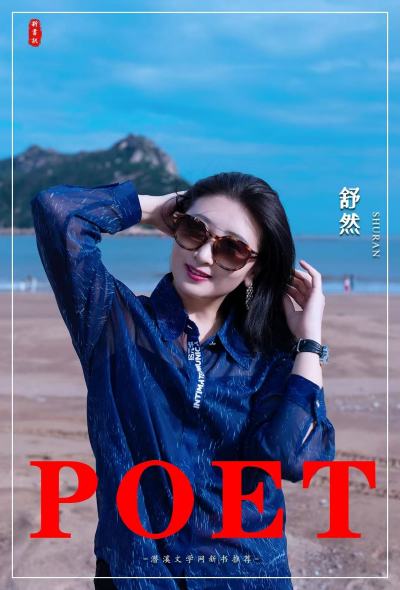《石燕》序
生活看似一场不伦闹剧,但小说却让其倍加严肃,这种严肃性增加了我们经历的分量,防止遭遇被遗忘,被消解,被社会人轻描淡写,其残酷、辛酸、喜剧性,允许了它抵达故事题材允许的深度。
强雯是我在鲁院的同学,2008年。在同学期间她曾不断地与我讨论文学议题而我也必须承认自己多是一知半解,却有着那么不自知的傲慢——似乎,我曾反复地对她和我的同学们说不,不能,不对,文学不应是这样子的,文学要想达到高格就必须怎样怎样……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在经历了多年的教学尝试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所谓“必须”是多么的可笑,才意识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应是随口说说的套话,它是确然的真理而我其实当时并不真正地理解它。我当然也记得强雯和我的争执,她不肯轻易地妥协——大约是直到今天,在一遍遍翻阅强雯的这部《石燕》的时候,我才理解到她不妥协的可贵以及这份不妥协的意义所在。当时,我貌似尊重文学的多样表达但其实有一个固定的、固执的偏见在,我貌似认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本质上却暗自规定:只有一条道路是能够真正到达罗马的,其余的道路都是幻象。
从2008年至今,我的文学观念有依然的固执也有部分地调整,偶然反思,我会为我当年的那些并无道理的傲慢和坚持羞愧,为我的盲目自大羞愧。是的,之所以提及这些是因为强雯的小说集《石燕》,它让我想起当年的争论,也让我对自己的不自知的傲慢有了更多的警醒,我甚至觉得,《石燕》也是检视我此时认知的一面镜子。在阅读这部小说集的过程中,我读出了感动吁嘘,读出了丰富,读出了精心和内在的涡流,而之前,在那个2008年,我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如此的感受。
强雯的小说源自于生活,她善于捕捉来自于日常的那些凡人故事,乐道于属于他们的酸甜苦辣,内心的波澜和面对日常事物时的计较、算计、挣扎和取舍,乐道于属于他们的“沉默”和沉默的回声,乐道于那种平静之下(至少是貌似的平静之下)个人的面对和杯水里的微澜,尽管这微澜就个人而言已经接近于风暴……在2008年,在我和强雯同学的期间,我对这样的写作颇有轻视,我会觉得它所有的不过是“手把件的美”,它缺少我以为的文学的宏大和宽阔,缺少“深刻感”和“力量感”,我希望文学能以虚构的方式言说我们的存在和形而上面对,我希望它一直面对宏大和宽阔,对我们的习见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并能说服我们——现在,我在阅读强雯的这部小说集的时候,却发现我以为的某些“匮乏”其实属于偏见,她的文字里有这些,并不像我原以为的那么匮乏。
譬如《石燕》,一个文物修复师的故事:故事沉在日常性之中,强雯书写的当然是日常层面,一个“有故事的人”的事业观、人生观和情爱观,以及这些观点和性格的成因等等,而重庆的地域文化则作为特征性补充拓展出另一层面的丰富……然而它并不止于此,它在内部是有不断散出的折光的,这个折光其实更有意味。透过折光,我们看到考古行业在时风影响下的挣扎、流变,以及古迹修复专家、社会团体在争夺古玩市场上的种种角逐;我们也看到那个人(或那类人)既被这个社会需要,但又不能接受转变的“可贵固执”——这里面,有生活和生活之思,甚至有隐约的价值判断和对于“后果”的反复掂量,有那种“生活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没有更好可能?”的隐含追问。再譬如《暴饮暴食》,再譬如《单行道》和《旗袍》……在她的这些小说中,日常生活是她乐于的取材,她属于那种“小事儿的精灵”,敏感于日常的艰辛与欢愉,敏感于“个人生活”和对自我欲望的处理,敏感于神经末梢所发出的些微震颤。但这些小说是有褶皱藏匿的,如果我们具有耐心,会发现它们其实暗有天地,暗有内在的精神指向、时代指向。这在我充满偏见的2008年以及之前,是意识不到的,读不出来的。事实上,强雯笔下的小事儿往往并不小,她言说的一沙背后也有一个隐约的一世界,更为让我看重的是,她的每一篇小说的言说都是不同的,都指向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不同的精神疑难——也就是说,阅读《石燕》这部小说集,你会窥见很不相同的、具有意味的风景。
对于生活的熟捻也是强雯写作的强点之一,她的故事往往能让你“身临其境”,进而是“感同身受”,将这个故事看成是你的故事,是你要面对的生活和生活可能。她的小说大约看不到在文字处的特别着力,然而——
……艾云丽听见沉重的拖鞋声在客厅的地板上摩擦,停顿,再没有了声音,也没有灯光。……怎么回事?她又仔细听了一会,没声响,便悄悄地把自己的房门打开,借着路灯的微光,她看见父亲沉沉的背影挂在窗户边,像一件用旧的黑雨衣。
“还不睡呢?”
“明天不是要去景园公园吗?”
父亲依旧背对着她,不回答。
艾云丽披上外衣,好奇地走上前去,只见父亲直直地望着窗下,冷清清的凤尾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超市、饭馆全都拉上了卷帘门。
——《百万风景》
在这里,叙述客观,冷静,貌似只是一个日常生活场景的记录,我们似乎也读不出波澜:不,波澜在着,在艾云丽的心里也在那个父亲的心里,只是强雯有意识地掩藏了它,只放出了些许的回声,譬如对父亲背景的比喻,譬如父亲的那句话和话里的言外,譬如——“清清的凤尾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超市、饭馆全都拉上了卷帘门。”它的里面有着况味,有着百感交集,有着空旷和它所有容纳下的巨大回声。它让我想起海明威在他改写了39遍的《永别了武器》中的那个结尾:
我往房门走去。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我觉得二者之间有那种大致相同的妙:经济而冷静的语言,它几乎不渗带情感,但内在却是大波澜;悠长而耐人寻味的回响,它们有着近乎太过辽远的广阔;百感交集,一种可意会到但无法用另外的方式解释清楚的百感交集。
“语言是小说的刀刃”。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拟或就是强雯说出的?在我看来这句话用给强雯大抵是有效的、恰应的,因为她的小说语言时常会呈现一种刀刃感,我能注意到她在书写时对于日常的那些“划开”。
“我们希望你协助调查。”警察说。
张丹眉头一挑,立即恢复了神色,“噢,我只是他的前妻。”说完,丢下事故现场,不闻不问地敲着足音轻快地走了。
……
张丹自问自答着向前走。身后的喧闹已经与她无关了,她有些歇斯底里地想尽快脱离这个现场。后面一个警察在叫她站住,她装做没听见,抑扬顿挫地继续高跟鞋的清脆。
站住!站住!警察继续喊叫。
他到死都没告诉我真相。是的,没告诉。张丹不回头地往前走,她和后面的警察一样生气,脚步也越来越快,一滴冰凉的恨意顺势滑落地上,和着地上的雨水,被细长的鞋跟溅起,瞬间没了踪迹。
——《暴饮暴食》
话语简洁,但它在姿体、行为、对话呼应和心理描写之间几经转寰,它们参与着人物的塑造和呈现。她几次写到张丹高跟鞋发出的脚步声,“不闻不问地敲着足音轻快地走了”、“抑扬顿挫地继续高跟鞋的清脆”,“脚步也越来越快,一滴冰凉的恨意顺势滑落地上,和着地上的雨水,被细长的鞋跟溅起,瞬间没了踪迹。”……这些描述也是刀刃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它有伸向人的沉默的幽暗区域的通道,它有人心和人性的解剖。
《百万风景》中的一家农村的拆迁户,搬到城里居住,卤菜摊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家简陋的社区旁边建起了一座豪华小区,最初让他们拥有了休闲活动的场所,享受到了城市的优雅环境。但是随着小区的落成封闭,反而给他们增添了从未有过的烦恼。他们曾经拥有的乡村田园已不复存在,在城市里却又难觅一处栖居之所,贫富悬殊,心理落差,通过一件平常的小事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些散落的碎片和隐秘的心理也被巧妙地剖露了出来;《清洁》里,主人公小海有着强烈的做清洁的爱好,在这个人们纷纷膨胀着欲望,疯狂追逐名利的时代,他却丝毫不为所动,喜欢着属于他内心的,在别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事情。他在一座寺庙里做一份整理拓片的工作,安心于微薄的收入,连他好不容易交到的女朋友也不能理解他……寺庙里缓慢而澄静的生活,遥远的风铃和木塔的故乡,被强雯描述得令人心驰神往。《水彩课》是父亲一场青春期幻灭,是特殊时代青春期的幻灭。那个悲情年代,似乎让人无力指责,小说结尾,无比虚弱的父亲在女儿面前沉沉睡去,人生苍凉的况味通过作者具象化的笔触被充分地传达给了读者,对于时代和个人命运,我们说什么好呢。而《黑水仙》充满了黑色幽默,风光无限的一代文坛高人在人生落幕时,由她的情人掀底,聚沙成塔的不止爱恨。《单行道》里的单亲妈妈,她的人生残酷又温情,原生家庭里被掠夺的父爱,并不是原罪。其中的心理描写我以为是最出色的。《旗袍》中,旗袍是道具,也是悲剧人生的序幕。中年女人以旗袍为标识重塑生活,却又最终被冷酷的现实嘲讽打败,人物描写很吸引人。《功德碗》则重现了文字意蕴的古典美学,故事返场与民国时期,在兵荒马乱的军阀乱世之中,一个大户人家三十多年坚持做功德,帮助和感化前来投靠的乡民,然而看似保护伞的功德碗却自承双重含义……《暴饮暴食》是本书中极少数背离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品,应该说具有将意识流和表现主义融入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它描写了一个电视台的气象播报员,幻想成名到疯狂,像酗酒一样,他暴饮暴食成瘾,现代化大都市人心的渴望急速膨胀,无法落实,气象播报员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疯狂的案例。
《石燕》中的小说们,看似独立,却又彼此关联,那些美好宁静的往昔、当下甚至未来,像一个气泡,它们和脆弱的现实肥皂水互为纠缠,偶然的幸福时刻,不过是脆弱现实的缓刑,这些小说,以及小说外的事情,让作者和读者都理性含恨:“闭嘴,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