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花灯调》我必须写,不写就跟自己过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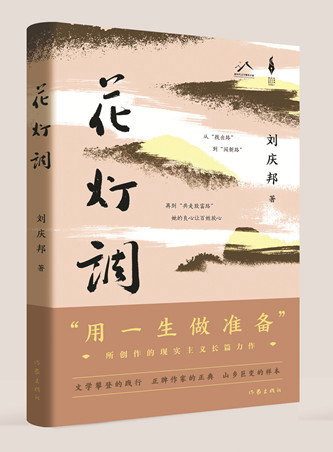
新时代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反映山村历史性变化的新作品,读者也在呼唤这样的作品
记者:庆邦老师,您新的长篇小说《花灯调》列入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今年初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作品中,您聚焦脱贫攻坚,描述了下乡干部向家明带领高远村村民“找出路”“创新路”“共走致富路”的故事,在书的封底上您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请您谈一谈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和写作过程,也请您谈谈对新时代文学的理解。
刘庆邦:由作家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我的第13部长篇小说《花灯调》,是我必须写的一部书,不写就过不去。不是别人跟我过不去,是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进入新时代以来,对于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全面脱贫、步入小康和乡村振兴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功绩,我愿意用一座丰碑和三个千年来概括。所谓丰碑,它不是石碑,是口碑;它不是建在土地上,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我没使用里程碑,而是说丰碑,因为丰碑更伟大,更长久。所谓三个千年,是千年梦想、千年德政和一步千年。这里所说的千年,不止一个千年,也是三千年,五千年。如果把三个千年展开来谈,容易谈得比较长,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新时代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反映山村历史性变化的新作品,读者也在呼唤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不写出来,就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责任。
从写这部小说一开始,我就考虑如何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来,我每年都回河南农村老家,跟老家还保持着血肉般的紧密联系。对老家不断发生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眉梢,动在心上,很想写一部表现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可是,不是我想写就能写,有了写作的愿望和冲动,不一定就能付诸写小说的行动。这里有一个写作机缘的问题。小说主要是写人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是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好比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又好比主要人物是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如果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客观,没有主观,只见变化,不倾注感情,并不讲究细节、语言和艺术,新闻报道和纪实作品就可以承担,何必要写成小说呢!我知道,全国有五十多万个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我设想,我最好能找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来,统帅起来。因为我的心是有准备的心,当我有幸遇到遵义山区这位女性驻村第一书记时,心里一明,好,众里寻他千百度,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不正是我要找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优秀代表人物嘛!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人物对这部小说的启动和完成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这部小说。
恕我直言,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对何为新时代新人并不是很明确,正是在塑造新时代新人的探索中,正是在向家明这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我才逐渐认识到新时代新人的特质。那就是,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承担,新的作为,新的奉献。拿向家明来说,她身患重病,却瞒着领导、亲人、村民等,坚持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她曾三次差点把生命丢在山村,可谓九死一生,这又需要多么忘我的牺牲精神。新时代新人形象不是一个概念,是通过具体行动在向家明身上完美地体现出来。
当然,向家明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她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她也想得到职务上的升迁,也想多挣工资。遇到不高兴的事儿,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这些局限不但不会削弱向家明的新时代新人形象,反而使她的形象更真实,更立体,也更加光彩照人。
《花灯调》是新鲜出炉,对这部书我还要再说几句。回顾总结起来,我觉得自己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我吃过苦;二是我不怕吃苦;三是经过五十多年的创作训练,我知道小说应该怎样写。吃过苦,是指我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常年处在饥饿状态。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懂得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之不易,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心怀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日乡村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体会,写起来更加贴心贴肺。不怕吃苦,指的是我到偏远山村定点深入生活。比起小时候所受的贫困之苦,我到山村吃的那点苦,不算什么。但比起我在北京的生活,山村吃住行各方面的条件还是差一些。我放低姿态,不讲任何条件,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跟着村干部翻山越岭,走遍了全村所有的村民小组,走访了不少农户。我的写作对生活非常依赖,好比庄稼对土地的依赖。没有好土地,就长不出好庄稼。正是我脚踏实地地在那个山村生活了十多天,才有了这部长篇小说。第三个优势似乎有些自我吹嘘,但也不完全是吹嘘。学无止境,写作这个事儿更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训练。学习和训练的时间长了,总会积累起一些基本的写作经验。还拿这部《花灯调》来说,尽管在中国作家协会提出“新时代山村巨变创作计划”之前,我已经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与“计划”不谋而合,但不可否认的是,我的这部小说也有着主题创作的性质。主题创作是比较难的,弄不好会主题先行,图解政策,记录过程,写得太硬,太实,缺乏文学性。文学性是主题创作的生命,只有保证主题创作有较高的文学性,才能真正实现主题创作的价值。意识到这些,我就调动情感,极力使主题柔软化,具有感染力。我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处理好实与虚的关系,在实的基础上全面升华,升华到文学艺术的层面。
短篇小说是我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种,把诸多短篇小说加起来,形成合集,也可以构成长篇小说的容量,从中也可以看到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世界
记者:您在文学界以创作短篇小说著称,被誉为“短篇王”,您的短篇小说《鞋》《响器》《麦子》《种在坟上的倭瓜》等,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请您谈谈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并请您谈谈在具体的写作中,您如何选择短篇、中篇、长篇等不同文体?
刘庆邦:我写短篇小说是多一些,大约有330多篇。出版过12卷本的短篇小说编年。写完长篇小说《花灯调》之后,我又连续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写长篇小说需要大块的材料,而短篇小说不需要太多材料,有时通过一个细节就可以生发一篇。我喜欢写长篇小说,也喜欢写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多次说过,从几何的角度讲,短篇小说是点,中篇小说是线,长篇小说是面。用水作比,长篇小说好比是大海,中篇小说好比是长河,短篇小说好比是瀑布。拿日月星辰来形容,长篇小说像太阳,中篇小说像月亮,短篇小说像满天星斗。各种体裁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光亮,都不可或缺,谁都不能代替谁。
短篇小说是我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种,它也像一把把小小的钥匙,帮我打开一个个心灵世界,并再造一个个心灵世界。其实,把诸多短篇小说加起来,形成合集,也可以构成长篇小说的容量,从中也可以看到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世界。
记者:数年前,我在《十月》杂志上读到您的《陪护母亲日记》,至今不能忘怀,您以日记体散文的形式记录了在医院陪护生病的母亲的过程,其中对母亲的深情与孝敬之心,是您个人的真情流露,也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影响。请问您如何看待民族文化,如何看待散文与小说在处理题材时的差异。
刘庆邦:谢谢您读了我的长篇日记体散文《陪护母亲日记》。这篇散文的前半部发在《十月》杂志上,后半部发在《北京文学》上。前半部得了当年的《十月》文学奖,后半部得了《北京文学》奖。后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我就是我母亲》,获得了第二届孙犁文学奖。我在写小说之余,每年也都会写一些散文。我已出版了十多部散文集,北京联合出版社最近在筹备出版“中国散文60强”,其中也有我一本。中国的小说家大都写散文,如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等,他们的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很好。散文写作是作家整体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作家不写散文,创作就称不上完整。小说和散文所担负使命的差异是明显的。小说是虚构,散文是纪实,小说是隐藏,散文是坦白。有人说散文也可以虚构,我坚决不同意。散文可以想象,但不是虚构,虚构就失去了散文的本真。
记者:跟您接触总是感觉如沐春风,感觉到您的善念、善意和善心,您的小说中也充满着对他人生活的理解与温柔敦厚之风,比如您乡村题材的小说中体现出的对小人物的同情与理解,对他们身上爱与美的发现,但另一方面,现代小说往往趋于极端,对人性之恶进行极端的刻画与描写,而且被认为是深刻,请问您如何看待现代小说的这种倾向,如何在小说中处理善与恶的关系?
刘庆邦: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暴露人性恶的极端的小说,如《走窑汉》《血劲》《神木》等。这些小说被评论界称为酷烈小说。现在随着年事渐高,我不敢再写比较激烈的小说,写起来容易导致心跳加快,对身体不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内心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柔软,感情越来越脆弱。我认识到,相对物质慈善事业而言,文学作品不当吃,不当喝,不当穿,不当戴,偏重于心灵慰藉和心灵滋养,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心灵慈善事业。不是吗?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既有身体,也有心灵,既需要物质的供给,也需要精神的支撑。
做慈善事业的人,必定有一颗慈善之心。从事写作的人,也必须是天性善良的人。这个条件是最起码的条件,也是最高的条件。只有写作者的天性善良,才能保持对善的敏感,才能发觉善,表现善,弘扬善。
记者:作为一个来自河南的作家,同样书写乡村,您小说的艺术风格与留在河南的李佩甫等人不同,与同样来到北京的周大新、刘震云等人也不同,请问您如何看他们的作品,如何看待与他们的差异?
刘庆邦:您提到的这N位作家,都是我的老乡。巧合和有意思的是,也曾有读者把我们放在一起说。同是河南人,我的老家在豫东,周大新在豫南,刘震云在豫北,李佩甫在豫中。我们哥们儿虽然都是生于斯,长于斯,写出的小说却各不相同,因天性、思想、情感、主观的不同而不同。说得好听一点,是各有千秋吧。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是“50后”,随着身体渐老,创作的势头肯定也会减弱。好在年轻一代作家顶了上来,如李洱、乔叶等,他们所取得的创作成果让人欣喜。
记者:在乡村题材之外,您集中处理的是煤矿题材,这应该与您对煤矿生活的熟悉有关。长篇小说《红煤》讲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临时工宋长玉如何向上爬的故事,令人想到《红与黑》中的于连。相对于农村农业,煤矿开采属于工业,您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与西方的现代化有哪些相同与差异之处,有哪些独特的经验值得书写?
刘庆邦:我在煤矿的基层工作生活了九年,后来调到北京,还是长期在煤炭行业工作,对煤矿的生活比较熟悉。我写了大量煤矿题材的作品,中短篇小说不说,仅长篇小说就写了四部。有《断层》《红煤》《黑白男女》《女工绘》。我们的写作离不开现实,每个作者都有自己对现实的切入点,我对现实的切入点之一就是煤矿生活。煤矿的现实既是我个人心目中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层次的现实。文学来自人民,我们的作品必定要书写人民。全国600多万矿工,1000多万矿工家属,无疑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他们称为矿民,也可以把他们说成是头戴矿灯的人民。这部分人民从事的是人世间最繁重、最艰苦的劳动,支撑着共和国的能源大厦。这部分人民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却胸怀高远,一心在为祖国的光明和强盛贡献着青春和力量。每每想起我的那些仍在地底日夜挥汗的矿工兄弟,我的双眼就禁不住盈满了泪水,让我们怎能不深情为他们歌唱?
只有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像看见亲人一样,无条件地走到他们中间,将心比心地和他们交心,才会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
记者:我注意到您时常回到故乡或到其他地方采访采风,对您来说,“深入生活”是不是您进行创作的前提或必需?换句话说,您已经有了丰厚的生活积累,为了新的创作,您是否需要重新深入生活?
刘庆邦:深入生活对作家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夏天,我专门写了一篇谈深入生活的长篇文章,题目叫《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分上下两期发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我在文章里写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限,活动范围有限,经验也有限,写作素材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做到持续写作,必须不断深入生活。作家好比是一只蜜蜂,蜜蜂只有飞到野外,飞到百花丛中,在很多花朵中进进出出,才能酿出蜂蜜和王浆。作家还好比是一棵树,只有把根须深深扎进土地里,一年四季不断从土地里汲取营养,才能保证每年都能开花,结果。我们的办法,只能是向勤劳的蜜蜂和有耐力的果树学习,飞出去,扎下根,不断向生活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活水淙淙,生生不息。
深入生活,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不那么容易,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还有一个能力问题。态度问题是深入生活的首要问题,态度决定一切。正确的态度,是有着深入生活的真诚要求和迫切愿望,是我要深入生活,不是别人要我深入生活。是心甘情愿的,主动的,而不是磨磨叽叽的被动行为。还有一定要放下当作家的架子,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再放低。我们只有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像看见亲人一样,眼里常含泪水,无条件地走到他们中间,将心比心地和他们交心,才会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能力问题,是要求我们要有社交经验,要有求知欲,好奇心,并始终处在思索和想象状态。我除了上面提到的去偏远山区定点深入生活,还曾三次到煤矿定点深入生活,之后都收获满满,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篇中短篇小说。
记者:您写过一篇文章《小说的种子》,在一个访谈中也谈到“小说要会拐弯”,这其中蕴含着小说艺术的真谛,以及小说与生活更深层次的关系,请您结合您的创作经验,谈一谈一篇小说从“种子”到写成作品的过程。
刘庆邦:关于小说的种子,我主要是针对短篇小说而言。我多次应邀去鲁迅文学院讲课,所讲的题目之一,就是《短篇小说的种子》。至于种子说,有许多类似说法,支撑点、闪光点、爆发点、眼睛、纲等等,都是种子的意思。我觉得种子说更形象,更圆润,更饱满,也更美,就说成种子。所谓短篇小说的种子,是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有了种子,小说才会有出发点、落脚点和生长点。那么,种子是从哪里生发呢?不是从土壤里,不是从水里,更不是从石头上和云彩里,而是生长于心,是从作者的心里生长出来的。种子在心灵的土壤里孕育过,被心灵的雨露滋润过,被心灵的汗水浇灌过,被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一点一点打上心灵的烙印,生长成一篇篇心灵化的短篇小说。
记者: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以来,一直持续写作到今天,请问您持续创作的资源和动力来自哪里?对您来说,文学意味着什么,持续写作意味着什么?
刘庆邦:持续写作是需要资源和动力的支持。关于写作资源,我在前面说过了。关于动力,我认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有思想的,情感的,逻辑的,责任的,也有名誉的,效益的。回忆起来,我1972年写第一篇短篇小说的动力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正在谈恋爱,写小说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写作才能,是为了讨得女朋友的欢心,说得好听一点,是为了爱。是呀,那时写了东西没地方发表,没有稿费,更没有评奖和改编影视剧,写作的动力只能是为了表达爱。作者是我,读者也只有女朋友一人,女朋友读了小说,说写得不错,就完了。到了现在,我想来想去,还是愿意把写作的根本动力说成爱。冰心先生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当然,我所说的爱,是扩大的爱,延伸的爱,除了爱自己的爱人,我们还爱祖国,爱人民,爱时代,爱生活,爱自然,爱一切可爱的东西。
记者:您和作家们的交往非常广泛,老一代作家如汪曾祺、林斤澜,同代作家如王安忆、史铁生、王祥夫等,都与您有深厚的友谊,后辈作家与您的交往就更多了,您在作家中有这么好的人缘,主要是您的作品还是人品打动了他们?
刘庆邦:这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让我回忆起和作家们交往的诸多往事。从河南调到北京之后,和作家们的认识和交往,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指点和帮助,我也许成不了一个作家。如果把我和诸多作家的交往一一细细写来,写一本书都够了。比如刘恒,我和刘恒认识比较早,他当时在《北京文学》当编辑,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认识了。刘恒看到我在河南的《奔流》发小说,就给我写信,向我约稿,让我“把大旗从河南移向北京,用重炮向《北京文学》猛轰”。我写完了短篇小说《走窑汉》,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去编辑部送稿。刚好编辑部只有刘恒一个人在那里值班,他接过我的稿子,当场就看,看了表示认可,立即在稿子上用曲别针别了推荐稿签。比如王安忆,王安忆看到我在《北京文学》发的《走窑汉》后,认为“好得不得了”。她推荐给评论家程德培,建议程德培给《文汇读书周报》写评论文章。此后,只要看到我的小说她都要看,好的说好,不太好的就给我写信指出不足。她给我的短篇小说集写了比较长的序,说我的天性里有与短篇小说投合的东西。王安忆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莫言与刘庆邦及其他》,把莫言的一些小说和我的一些小说做对比,说莫言是道家,我是儒家。再比如林斤澜老师,他写文章,说我是写短篇小说的“珍稀动物”。还说我“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他不仅喜欢我的小说,还喜欢我这个人,我们是忘年交的酒友。他一当上《北京文学》主编,就约我去编辑部谈稿子。谈完稿子,他要我接二连三给他写稿子,他要接二连三给我发。我把林老的厚爱当真,此后果然每年都给《北京文学》写稿子。四十多年来,我仅在《北京文学》发的中短篇小说、散文、创作谈就有将近五十篇。
我已先后写了王安忆、刘恒、林斤澜、史铁生、莫言、陈建功、何向阳、徐小斌、曹文轩、徐坤、付秀莹、荆永鸣等作家的印象记,以后还会写从维熙和雷达等作家老师们的印象记。
记者:在不知不觉中,您已经跨过70岁,成为了一个“70后”作家,请问对您来说,年龄与写作有什么样的关系,您对未来的写作有什么规划与展望?
刘庆邦:我是1951年腊月出生,今年73岁了。73岁好像是人生的一道坎,有人避讳承认自己73岁了。我不避讳,73就是73,怎么了!我没有那么自觉,阎王不叫,我自己是不会去他老人家那里报到的。我现在写小说,还想写,还能写,写出来还不失水准,干吗不继续操练呢。属于我的小说都在我心里,我不写的话,没人能代替我写出来,还是走着说着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