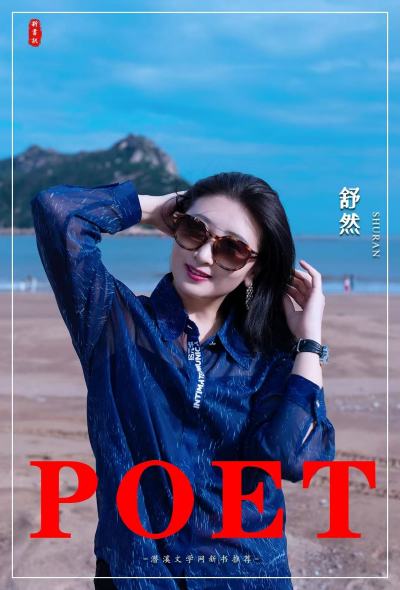何志云:“京漂者”及其故乡
如果把徐则臣的作品加以题材上的分类,那么,人们看到的大抵有如下两个方向:其一,以一个外地来京者的视角,观察和描摹活跃在北京不同角落的外地人的境遇和心态,收在这里的有《啊,北京》《三人行》《西夏》;其二,是对故乡印象的俯拾与整理。这里说的“印象”,相信既有徐则臣的亲历也有儿时的听闻乃至想象,一概以他的感受和体验为底子,比如《花街》《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多数篇什。此外,在末尾留了《我们的老海》《养蜂场旅馆》,用李敬泽在“推荐辞”中的话说:“体现了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对形而上的兴趣,这类作品致力于小说意蕴的模糊性的开掘,也体现了徐则臣对小说艺术性的追求。”对这类作品的评价很可能会见仁见智,留作读者欣赏则不失为有意义的事。
对“京漂者”生存境遇的关注,而今算不得是独特的艺术发现了。不过能像徐则臣那样锐利地切入“京漂者”的生活,同时一样锐利地提炼出激烈的思想和心理冲突的,却并不多见。《啊,北京》里的边红旗,拿起笔是个诗人,放下笔是个办假证的贩子,“哪位要想办假文凭可以找我,诗人打八折”,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边红旗朗诵完自己的诗作这么自我介绍道。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京漂者”,边红旗从“踏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看见了火热的北京”那一天起,他所挚爱的首都北京就给了他从未想象过的磨砺,那是生存的艰辛奔波,是永无尽头的无望挣扎,直到最后不得不流着眼泪离开北京。《三人行》里在北大读博的康博斯,北大食堂的厨师班小号,偶然和在北京谋生的姑娘佳丽租住在同一个四合院,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属于“京漂者”,各有各的人生遭际。然而,面对在京八年,“时时刻刻都在精神和身体上感受到生活的不容易”的佳丽康博斯和班小号遭遇的种种波折,最终都不再属于一己的悲欢,而折射出来“居京民生之多艰”的慨叹。有意思的是,和《啊,北京》一样,《三人行》也结束于佳丽的离开北京。佳丽流着泪登上火车之际,康博斯想到了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写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艰难曲折中,寄寓了他们对北京爱恨交加的情愫。
这几乎是所有“京漂者”面对着的尖锐冲突。一方面,“北京是我们伟大的首都,我们爱北京”,从懂事时就被教育被熏陶的这份认识和感情,早已融化进每一个“京漂者”的血液。在他们的心目中,北京不仅意味着无尽的发展机会,更像母亲的怀抱温暖而亲切地等待着他们;但在另一方面,一旦他们踏上北京的土地,融进北京的茫茫人流,立即尝受到生存的艰辛,同时,失去依靠的恐惧也很快就包围了他们,用边红旗的话说,“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问题的实质就这样被锐利地揭开并推向前台:计划体制下接受的意识形态信念以及情感归宿,与市场体制状态下严酷的生存现实,这一巨大的反差,把“京漂者”推入的,既是迷惘的深谷,更是炼狱般的心理煎熬,这就是“京漂者”生存境遇的实质。那么干脆离开北京呢?很少有人如此决绝。“京漂者”们无论是在北京求学,还是漂泊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少有人能断然选择离开,一方面固然由于北京的巨大魅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离开不仅意味着人生的重大失败,还意味着他们信念与情感的就此割断。这一点,在深圳、上海以及全国各地漂泊着的各色人等是很难感受到的,那么,有心人从小说中读出的,恐怕还能有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
在我看来,徐则臣就是因了这种“京漂者”的体验,来频频回顾故乡的,这时,故乡旧日的风物人情依然狭窄猥琐,竟显现出来别样的亲切与缠绵。《花街》里的修鞋老默与开豆腐店的蓝麻子一家,庸常无为的几十年后面,是如此让人肝肠寸断的那一份情意;《失声》中的姚丹,为了守候入狱的丈夫,拖着女儿度着艰窘的岁月,留给我们的是传统所谓“恩爱夫妻”的全部广阔与博大;《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中有个后爸的小艾,和失去了父亲的“我”,相濡以沫中的童真毕竟敌不过成人世界的规则,那规则又由于“鸭子上天”的谎言透出浓浓的虚伪和荒诞,读来令人扼腕;《弃婴》里被时光抚平了的人生惨痛,《奔马》中孩子那深知无望却不折不挠的向往,《逃跑的鞋子》里疯婆子六豁老太坚韧的一生……“对人性的处理宽容而节制,对苦难的审视放达而隐忍,对现实的质疑深入而开阔”,仍然是李敬泽“推荐辞”中的评价,照抄下来不仅因为深以为然,也在于它的准确中肯无从置换。中国底层就是以这样坚韧阔大的人性之美,几千年支撑起一个民间世界,从而赓续着民族的血脉。这么看来,它们今天一定也会支撑起“京漂者”的一番天地,从而把希望铺展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