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芹|金龙贺岁·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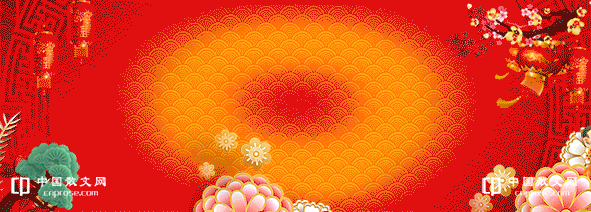
刘荣芹|金龙贺岁
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作家简历
★
刘荣芹 退休教师,济南市作协会员。有多篇散文发表在省市报刊杂志上。《齐鲁晚报》曾开辟专栏:『收藏•济南』,刊登她写的家族收藏故事。其丈夫韩庆祥编辑出版的《韩庆祥家庭成员作品集》「妻子篇」中,收录了她发表过的文章三十余篇。
“金打簧”怀表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
一天,一位同事找到我问:“听说你父亲会修表,能给我帮个忙吧?”“没问题,”我说:“不过父亲是业余时间义务修表,找他的人挺多,你得多等几天。”他听后,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鹿皮小袋子,笑着说:“我这块表不用修,只要把机芯和表壳分开就行。”见我不解,他解释说:“我这是块金壳怀表,有个收废品的要买这个壳,给600块钱呢!”“值这么多钱啊?”我羡慕地说:“回去先让父亲给你拆了。”
周日回家,见父亲坐在里屋的写字台前,眼上夹着放大镜,手拿小镊子,正忙着修表。我轻轻地把这个小鹿皮袋子放到写字台上。父亲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了看我。当他拿出这块怀表时,不由地啊了一声。我忙问怎么了,父亲惊喜地说,这是块金打簧怀表啊,得有九成新呢!“这表很稀罕吗?”我问。父亲说:“我收藏了几十年钟表,咱家这上千件藏品中,没有一块这么高档的。”“很值钱吗?”我又问,父亲点点头说:“这种表解放前见过,是瑞士进口的,一块值200现大洋啊!”当听我说了同事要拆下金壳卖掉时,父亲的脸沉了下来:“这忙可不能帮。这么好的表可不能把它毁了!”他见白瓷表盘边上崩了点瓷,心疼地说:“看来有人想启开,把它弄伤了,太可惜了!”
“我怎么跟同事说呢?”我问。父亲想了想,说:“告诉你同事,现在的金价是每克70块钱,这表壳是14K金,按半价算,每克也值30来块,这表壳大约重40克,算下来,至少也值1200块。如果拆了卖600块钱,表芯可就报废了?要是完整地卖,得值2000啊。”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不到90元,不吃不喝也得攒两年,我不由地啊了一声。
同事知道了他的表值这么多钱,很是惊讶。可他说:“谁能拿出这么一笔巨款买块表呢?要是不卖,母亲住院借的钱,指着工资是还不上的。”我把这话告诉了父亲。他担心地说:“你同事还是有卖的意思啊。”
就像说书唱戏那么巧。事后不久,父亲去逛大金庄旧货市场,看到一个地摊上有个打开的牛皮纸包,上面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表芯。他赶紧蹲下身细看,心里不由地一震:是块金打簧表芯啊!忙问这表芯从哪里收的。摊主说是人民商场一个修表的卖给他的。父亲问摊主卖多少钱,那人张口要100块。父亲顾不上还价,收到包里就往家赶。路过榜棚街时,他进了服装三厂传达室,借用人家的电话。那时候只有单位才有电话,每个电话机旁边都有本厚厚的号码簿。父亲查到我们学校的号码,打了过来。我正在上课,一位老师叫我说:“你父亲的电话,怕是有急事吧!”我拿起电话,听父亲着急地说:“快去问问你同事,那块金打簧拆了卖了吗?”我赶紧向二楼跑去。当父亲听说那块表还在时,连声说放心啦!放心啦!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不等问,电话就挂了。
父亲买了表芯,就有了心事,一心想为它配个壳。他找出好几块破坏表,没有一个合适的。一次,他从外边回来,拿着一块刚买的银壳表比了比说,这表壳配上这个表芯正合适。可就在要动手拆的时候,父亲犹豫了:不能拆啊,不能让这两块表都毁了。
之后,父亲几次让我嘱咐同事:那表千万可别拆了卖啊!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对我们说:“我还是担心那块金打簧表,要不咱想办法买下来吧!”
80年代后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开始铺水泥地,打家具。二弟挺机灵,学了一手好木工活。他和同学小山,业余时间为别人打大立橱,一家没干完就有另一家在等着。忙了一段时间攒下2000多块钱,准备买个大冰箱。当他知道父亲为买表犯愁时,说:“我晚一点买冰箱,先用这钱买表吧。“同事得知我父亲要买下金打簧,喜出望外立马减掉100元。
我把表带回家的那天,章丘来的小姨正和我母亲包水饺。听说花巨款买了个金打簧,不知是何物?连忙拍了拍手上的面,起身接过小口袋。当她把里面的物件拿出来时,大失所望:“嗨,这不就是块表吗?我还当是啥宝贝呢?这东西不能吃,不能喝,怎么比俺的家还值钱?”父亲笑着接过怀表说:“这表是金的,和普通的怀表不一样,它能报时、报刻、报分。这么小的一块表,有了这些功能,结构特别复杂。这表里藏着人的智慧啊,就是个宝贝。”说完,父亲上了上弦,按了一下表壳上的按钮,凑近耳朵,眯着眼睛听起来。我们都争着要听听,父亲说:“我教给你们怎么听。这表有两根音簧,高频音簧发声“叮”,低频音簧发“咚”。叮报时,叮咚报刻,咚报分。”见我们没听懂,他举例说:“如果是1点36分,就发出叮、叮咚叮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这下我们明白了。父亲拨一拨表针,按一下按钮,挨个让我们听。一时间,满屋子的人都咧着嘴笑。
父亲给表配了条银链子,把表装在上衣口袋里,链子夹在衣襟上。后来听母亲说:有了这块表,可把你爸爸高兴坏了,一晚上好几回让它报时,把我都吵醒了。我说夜里安静声音显大,吵醒了你不烦吗?母亲笑着说:“不烦,叮咚叮咚的像唱歌,可好听了。”
有一天,我和二弟熄前后脚进家,见洗衣服的大铁盆里放了不少东西,有旧照相机、单筒望远镜、手摇计算机,还有瓷枕、小罐等。我忙问,这是哪来的?母亲说:“你爸想找些东西卖了,凑起冰箱钱,可好东西不舍得卖,这些东西都卖了也值不上500块钱,差的远呢?弟媳说不着急,咱这些年没有冰箱不也照样过吗?母亲说:“这话可别让你爸爸听见,他要听见,不光不攒钱了,有了钱,还得往家买破烂。”
那一年,在省军区通讯修理所当所长的姐夫转业,补发了一笔安置费。大姐高兴极了,拿出2000块钱给父亲说,先让二弟把冰箱买了。这钱我用不着。你就不用着急了。后来,父亲把这块金打簧表给了大姐。说我玩了不少日子了,放到你那里吧。我还有那个表芯,等配上表壳,咱就一人一块了。
多年之后,父亲离世。在他的遗物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精美的小木盒,打开来,里面是一个玻璃器皿,透过明亮的玻璃,那块崭新的打簧表芯就躺在里面。我心里一震:父亲倾毕生精力搞钟表收藏,终生与钟表相伴。他用双手救活了不计其数的残钟旧表,却没能为这块金打簧表芯找到它的家。
想到这是父亲终生的遗憾啊,我的眼泪就扑簌扑簌地落了下来。
那件青花笔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机械局任职的丈夫,偶然发现了一个商机,立马动了心。经过好几个月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最终横下一条心,丢掉了三十多年的大国营铁饭碗,在知天命之年,白手起家,冒险下海创业。
下海初期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历经几年的苦苦打拼,在迎接新千年曙光的时候,终于还清了创业时欠的账,余下的钱,还让我们当上了“万元户”。
休息日回娘家,说了这个好消息。父母听后,脸上立刻挂满了笑容。
父亲说:“你这钱要是存着,就会越来越少。”“怎么会呢?”我问,“放在银行里还会生小的呢,月月都有利息。”父亲摇了摇头,说:“这账不能这么算,你想想,你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每月29块5的工资,那时候猪肉6毛5一斤,你算算能买多少斤!”我拿过算盘,噼里啪啦拨了几下说:“45斤多点。”“把钱放到现在,一斤肉5块钱,你再算算能买多少斤!”父亲又说。我又拨了几下算盘,不由地张大了嘴巴:“啊!还不到6斤啊?”
父亲笑道:“明白了吧?往后工资随着涨,物价也随着涨。过上几年,人人都成了万元户,你这钱就贬值了。”听到这里,我不由地为这一万多块血汗钱担心起来。
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别担心,有办法。”他指着屋里摆满的那些藏品说:“买成这些东西,不光不贬值,还能升值呢。”
接着,他举例说明:“你记不记得当年我花10块钱买的那个一拃多长的鼻烟瓶,上面还有条龙?”“记得、记得。”我说。“前几年你小弟弟装修房子的时候,卖了1万6。刚兴电视那会儿,你小弟拿着我修好的两块怀表,去天津外贸公司,卖了300多块钱,回来又添上点儿,买的那台14寸泰山牌电视。买那两块表的时候,一共才花了七八块钱。”接着,他指着条几正中那座大号苏钟说:“你二弟结婚那年,我把攒的,办几桌酒席用的90块钱,买了这座钟。现在9千块钱就有要的。还有……”
见父亲滔滔不绝地讲,我忙说,先别说了,快用我的钱,买个古董吧!父亲笑着说:“古董这东西,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得碰机会,碰运气。我在行里打听着,有合适的咱就买下。”我点了点头。
世上有些事巧到无法解释。就像有人给安排好似的,正要吃午饭,小弟拎着个布包进了门,他左手托住包底,小心翼翼地放在方桌上,把包打开。
父亲一看乐了:啊!这青花瓷笔筒颜色太正了。细看更加惊喜:呀,这么长的诗文啊!丈夫听了,马上凑上前细看,大声读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爱好诗词的他,像见到了老朋友,高兴坏了。
转动笔筒,全文之后还有落款“青云居珍玩”。接着是一副精美的图画:两只小船遥相对,船上各有一老翁,苍茫夜空中,隐约可见北斗七星和一弯新月。这是苏东坡夜游赤壁图啊!
父亲还告诉我们,青云居是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专为上流社会烧制精品。把笔筒翻过来,看底部时,丈夫提出怀疑:怎么写着大明嘉靖年制呢?父亲说,这叫寄托款,康熙鼎盛时期,不少瓷器喜欢落嘉靖或万历年制。
父亲又说,这胎底是两层的,凹底挂釉。我忽然看到,沿着底部边缘,有个一指来长的裂纹。忙问,这是个残品啊?父亲细看后说,这是窑炸,也叫窑裂,是烧制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裂纹比较稳定,人为磕碰的那种,不能收藏,裂纹容易越来越大。
父亲拿来盒尺量了量:高18公分,直径18公分。又掂了掂重量说,这是个大号笔筒,胎体敦厚,青花用料纯正明快,是件好瓷器啊!
他转身问小弟:这笔筒哪里来的?小弟答道:我在千佛山古玩城开店时,和我合租过一间店面的那个老张,下乡串户收的。他要卖1万块钱,我很喜欢它,想留下,先拿回来让您长长眼(行话:过目、鉴定的意思。)
打小我就知道,古玩行有个“行规”,熟人之间,要出手物件,不管价值多高,哪怕20万、30万,可以随便让对方拿走,既不写收据,也不打欠条。过上十天半月,如果要就留下,不要再送回。于是,有门路的人,先把物件拿走,找到买主卖掉,再给原主人送来钱,一次挣个好几万也是有的,谁叫人家有渠道来。
父亲问小弟,你有这么多钱吗?小弟答,正想说呢,钱不够,差好几千呢!
父亲笑道:巧了,你二姐刚说手里有一万多块钱,想买成古玩。我看这件挺合适。他转身对我说,买时觉得贵,但只要是珍品,升值空间就大。
见小弟没吱声,我忙说,不让你白忙活,给你1万1,多的算辛苦费。小弟同意了。
包好笔筒,丈夫右手紧抓布包,左胳膊紧紧抱住,我在旁边保护着。一路上,他沾沾自喜:怎么这么巧呢?想要啥就有啥啊!我喜欢诗文,喜欢什么来什么,这笔筒简直就是冲咱来的呀!
进了家门,他把笔筒放在写字台上,忙不迭地解开布包,又读诗,又赏画。高兴地简直手舞足蹈了。
儿子、女儿回来了,见了笔筒很喜欢。争先背诵《前赤壁赋》。他们原来都学过,忘记了不少,正好用这个笔筒补补课。见此景,我也跟着读起来。
一日饭桌上,女儿得意地说,这个笔筒,让一家人对《前赤壁赋》了如指掌了。儿子考问:“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前两句是什么?一时众人无语,继而,一齐站立,争先要去书房问“老师”,客厅里顿时传来一阵笑声。新千年到来之时,儿子把女朋友带回了家。于是买婚房的事儿提上了日程。
马路对面的那片荒草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几座红色外墙的商品楼。我们便去考察。得知是台商胡老板盖的,他在台湾是建筑设计师,难怪楼盖的这么有特色。室内瓷砖铺地,日式隔断:欧式小窗、吊灯、壁橱一应俱全。
一问房价,吓了一跳:一套三室两厅不到160平米,带一个25平米的地下室,竟要价30万。考虑到离公司近,豁出去了。
我们相中了四楼西头带弧形窗户的那套,和胡老板商定,一月内付款交房。便开始四处筹钱。离交款期越来越近,还差几万块钱,怎么办?丈夫一点儿也不急,他说:这房价太高,他不好卖,等等看,说不定还能落价呢!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套房已经卖了的消息。我们傻了眼,又跑去考察,定下五楼的一套。胡老板却说,按台湾的规矩,上一层再加五千块。无奈,我们只得想方设法筹钱。
付款期又快到了,还差四五万,这次是一家人着急上火。走投无路时,我想到了青花笔筒。买了一年了,能升值吗?我托二弟帮忙卖了。他说:试试看吧,带着去天津古玩市场碰碰运气。我嘱咐说,要价两万,少钱不卖。
隔了一天,二弟带着笔筒回来了。他说:古董这东西,不是想卖就能脱手的,用咱爸的话说,得碰要茬(行话:碰巧要买的人)。
笔筒没卖出去,我喜忧参半。挖空心思,连没过门的儿媳娘家,及她家亲友的钱都借了,终于凑齐了房款。
房子是精装修的,拿到钥匙搬家前,我们贴着墙打了一个很大的博古架,丈夫亲自设计,正中为笔筒留了个方方正正的“家。”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大姐打电话问我,青花笔筒还卖不卖,有人打听它了。
大姐住在英雄山下百旺古玩城附近。当时,二弟任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秘书长,在商城里有个办公室。大姐退休后,闲来无事,经常到那里玩,一来二去,和商家们混得很熟。
一天,她又去那里,二弟不在,商场里空无一人。这很正常,干古董这行,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嘛!于是,大姐约了几个老板,在走廊里打扑克。
忽见一人探头探脑走过来:“老板们,打听个人好吗?”嗬,一口地道的天津腔。大家想到,生意来了。因为那时,不少天津古董商经常来济南“进货”。
“你找谁啊?”有人问。“有没有叫刘荣光的?”“他是我弟弟。”大姐问:“找他有什么事?”“哎呀大姐,我找的就是您哪!”见大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说“前年,刘荣光带着你的青花笔筒去过天津,我是奔着您那笔筒来的。”大姐笑着说,那是我妹妹的。于是给我打来电话。
我说,现在不急着用钱,不卖了。那人一听急了,忙说出五万块钱买下行吗?得知我真的不卖,他失望地走了。
家里的博古架上,摆满了瓶瓶罐罐,过一段时间就落上了灰尘,每次擦拭都很麻烦。那次,我又一件件取下,放在地上,当我抱起笔筒时,无意中发现,它底部的窖裂似乎变长了。是真的吗?难道经常搬动擦试伤到了它?细看时,又不能确定。
之后,经常想起父亲说过的那些话:翠怕蓝、瓷怕残;瓷器有了残,不值几个钱……。我想,如果裂纹真的越来越大,到那时这笔筒就卖不上价了。想到此,忽生一念:不如现在就把它卖了。
二弟听说我要卖笔筒,带来了买主,来人拿起笔筒,反复细看后开口了:要个价吧。我回答:卖10万。,对方说,高了点儿,再落落。我说:前几天电视上拍卖的,同时期的一个笔筒,比这个还小一号,都卖了36万呢。他笑了,那是个完整的,你这笔筒底上有个窖炸,不可同论啊!我只好说:那你出个价吧。他说,我是真心要买,6万5,多一点儿也不添了。想到买了这几年,升值五万多,就点头同意了。他付了钱,包好了笔筒带走了。
买主走后,我想,人家是个内行,都说是窖炸,看来笔筒没有磕碰坏呀!真是这样还不如不卖呢!心里矛盾了好一阵,日子久了也就淡忘了。
十几年后的一天,二弟对我说,前几天跟着一个朋友去串门,竟见到那件笔筒了。我一愣:你确定是咱卖的那个吗?我问。二弟笑了,他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瓷器鉴定,这点儿眼光还是有的,笔筒的色彩诗文画面完全相同。尤其是底部的“窑炸”,和原来一样,不知你当初怎么看的……二弟走后,好几天我心里都很纠结,毕竟是件心爱之物啊,奇怪,我当初怎么会觉得裂纹越来越长了呢?如今,钱花没了,笔筒也成了别人家的……
一天,忽然想到了什么人说的一段话:世间任何东西都不会永远属于你,因为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带走任何东西。现在的拥有,只不过是暂时的保管而已。
我顿悟:今生我与这个青花笔筒有缘,保管了它六年,之后就轮到别人保管了。它虽然离开了我,但留给我一个难忘的故事,一段美好的记忆。
“千里走单骑”,一场古稀之年的友情接力
一位76岁深居简出的长沙退休老人,独自一人坐高铁,乘飞机,往返四千多里来到济南,只为在有生之年能同他的诗友——我的丈夫韩庆祥拍一张合影照片。他说,只有这样,今生才不会有遗憾。
这场“千里走单骑”的壮举,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里。听闻这件事的亲朋好友无不赞叹,同时感到好奇:这段纯粹、质朴的友情佳话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段故事呢?
那是十六年前的春天,我随丈夫应邀到湖南长沙,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一起赴天成公司参观交流。在焊接车间的展台上,一块小黑板引起了丈夫老韩的兴趣,上面用粉笔写着一首欢迎诗,笔迹清秀,语句流畅,可见写诗之人虽身处劳动一线,却有着不俗的精神追求。老韩驻足边读边拿出手机拍照下来,兴致勃勃地随口问道:哪位诗人写的?站在旁边观看的几个工人指着其中一位年长的师傅说:“李师傅写的”。
这位师傅个儿不高,穿一身工作服,戴着口罩和安全帽,并没看清模样。老韩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夸他诗写得不错,眼看要掉队,便转身追上了参观队伍。
随后的招待会上,丈夫特意提到了这位李工,并引用了诗中的句子,赞扬厂里的发展变化和工人的爱岗敬业。之后从厂领导处了解到,这位师傅叫李石均,年近六十岁了,工作非常出色,曾获得过长沙市“劳动模范”称号。
回济南后,在公司晨会上,丈夫回顾了长沙之行,并盛赞这位李师傅,还让员工朗读了他的那首诗。
之后不久,在来自长沙的货物箱中,员工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是写给“韩老板”的一首诗,署名“李石均”。
爱好了一辈子诗歌的老韩喜出望外——遇到知音了。他马上把电话打到湖南天成公司,要来了李石均师傅的手机号,于是就有了此后长达十六年的诗来诗往。开始是互发短信,后来有了微信更是时常互相赠诗,这一发就是十几年。
上月中旬,公司接到湖南长沙的商务邀请,老韩因身体原因不能同行,由女儿陪我前往,临行前他嘱咐我说,这次去长沙,如能抽时间见到李石均夫妇,同他们合影最好。
我们联系这么多年了,还不清楚他的模样呢!我把丈夫的嘱托记在了心里,并为李师傅夫妇二人准备了小礼物。
会议安排得满满当当,竟抽不出一点儿时间,我只得推掉部分日程,用挤出来的两三个小时约见李师傅。电话接通后,他愣了好一会儿,经过反复沟通,他才明白过来,连说太意外了,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特意见他。我约他们夫妇去橘子洲景区的入口处见个面,拍张照片,他想了一下说,我们互相不认识,这样吧,我带上韩总寄给我的《家庭成员作品集》,举着它做我们的“接头暗号”……我们都笑了。
没料到约定时间下起了雨,橘子洲的入口处一片花伞,去哪儿找人呢?接通了电话,也说不清具体位置,我们各自一手举伞,一手拿手机联系,可怎么也找不到对方。难道这次不能如愿?我急得不行。
约半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一位老者举着伞四下张望,身上被雨水淋湿了一片,脖子上挂着的袋子上方隐约露出《家庭成员作品集》的上半部分。“你是李师傅?”我迎上前去——啊,终于见面了!我们都如释重负,激动不已。这时雨越来越大,四周无处落脚,好在女儿为我们买来观光车车票,一路上,我们如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有说有笑。我把带来的手串和挂件送给他们夫妇,他们一个劲道谢,说接到电话太突然,没有什么准备,约我一起吃顿饭,尽尽地主之谊。无奈下午有会议安排,所剩时间不多了,女儿在观光车上为我们拍了合影,分别时又在橘子洲地铁站口合影留念,便匆匆惜别。
女儿把合影第一时间发给爸爸,而这时,老韩已经收到了李师傅在观光车上发来的赠诗。
从长沙回到济南的第五天,突然接到李师傅的电话,他说自己在长沙火车站,还是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我买了明天中午的高铁票,要去济南和韩总拍张合影照片喽。”我立马说,太好了,热烈欢迎,我陪你们二位好好逛逛济南。他却说,这次是自己来,拍了照片就回,“哪里也不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第二天傍晚,我带车去西客站接李师傅,怕人多不好辨认,照例带上那本《家庭成员作品集》。用了餐,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老伴儿正坐在沙发上焦急地等待,两位诗友一见了面,手拉手激动不已,无奈的是两人都听力欠佳,加上李师傅的一口湖南话又不太好懂,我便在中间做起了“翻译”。他们从16年前的相见开始,一直聊到相互写的诗歌、厂子的变迁、退休后的生活……时间太晚了,我们安排李工在家住下,多一份亲近。李工执意第二天返回长沙,又不会在线购票,我便让女儿为他买了第二天的机票,他才放心休息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给他俩拍了合影,带他参观了小区,参观了我们公司,又在公司和老韩拍了合影,还特意在前些年他寄来的匾额下合影留念。李师傅给老韩带来了珍贵的人参和一幅精美的十字绣壁挂,我们则送上山东特产和老韩近期出版的诗集。
中午时分,公司派车送李师傅去机场,分别的时刻到了,两位老诗友拥抱、告别,他一个劲儿地道谢,说晚年圆了相见梦,今生无憾了。十六年的光阴,斑白了头发,沧桑了面容,只有这份情义,历久弥新。
下午5点多钟,手机收到短信:我已平安到家了。照例还有一首赠诗——
来去两天赴山东,远隔千里会韩公;
只为了却情和义,目的已达乐心中。
此后年老更难忘,保持网络互传情。
祝愿韩总早康复,全家幸福永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