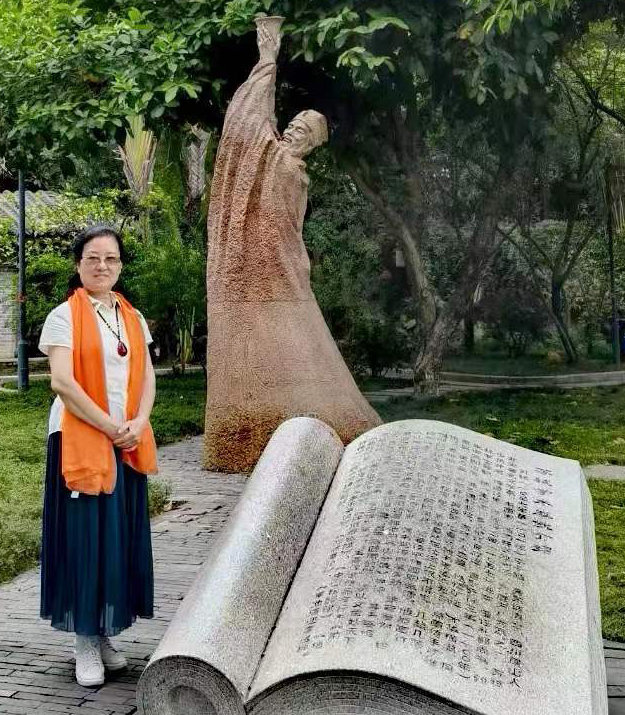【2023新春特刊丨中国作家 廖庆平 作品展】
2023新春特刊
中国作家 廖庆平 作品展
■ 作家简历 ■
廖庆平,1954年出生于重庆市。退休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疾控中心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副高职称,先后在《中国公共卫生》《中国地方病学》《预防医学情报杂志》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喜欢阅读,爱好文学,散文《重庆燕归来》在《重庆晚报》副刊发表,被选为“有生命力的阅读”刊发。《科学饮水知多少》《自发生态绿豆芽》在《重庆政协报》发表。《饮水与健康》《你知道空气维生素吗》《大狼狗窜上公交车乘客惊魂》等数篇,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攀枝花日报》上发表。在《新浪博客》写过游记、医学科普文与人生五味随笔百余篇。在《黑子草》微信公众号发表散文《母亲永远在我心中》等数篇。散文《一声老师傅的幽默》获2022年第二届“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银奖。
★★★ 作 品 展 示 ★★★
话说碗足
上周末,在老母亲家聚餐。这次由我掌勺做几个菜,其中“硬菜”是家常麻婆豆腐和炖鸡汤。
想到家常麻婆豆腐是一半固体一半流体,如用盘子装则铺得太散,拈菜没那么方便。我就特地选了一个中等大小、高矮合适的瓷碗备用,没留意碗独独儿有名堂。
碗独独儿是重庆土话,学名碗足,指碗底下支持碗的部分,多为圆圈状。
豆腐烧好了,我左手端碗,右手持锅铲,将热腾腾的豆腐铲进碗里。嗬哟!还没来得及将锅里的豆腐铲完,端着碗的左手手指就被碗底烫得受不了啦!赶紧把碗放在灶台上,只得用锅铲一铲又一铲去屈就灶台上的碗才能完成盛菜过程。缺失了碗与锅铲的互动,盛菜变得笨拙低效,好别扭!
接着,我用一个大瓷碗盛沸腾的鸡汤。
这次是把大瓷碗放在灶台上,用大汤勺连肉带汤舀进大瓷碗中,直到将满为止。接着双手端着大瓷碗从厨房走向餐桌。灶台到餐桌也就四五米远吧?!扣在碗独独儿上的几个手指头就招架不住了,把我烫得龇牙咧嘴的。要不是革命意志坚定不移,强忍痛苦我也牢牢把持。天哪!只差那么一丁点就碗落地一一汤打翻一一人烫伤,好危险!
本人既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支使分子”,也不是做学问远庖厨的“象牙塔知识分子”。我是一个亲力亲为的“制食分子”。历史的经验和实践的证明,炒菜做饭于我,虽谈不上游刃有余,但绝不至于兵荒马乱。
何故如此?
我感到问题出在碗上。
于是,我找出盛豆腐装鸡汤相同的碗,再找到家里幸存的一些老式碗,把它们翻过来倒扣在桌上。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下子一目了然!
老式碗的碗足,有深度有厚度,实实在在,有个把门儿的。现在的碗,其碗足被大大的虚化了!碗独独儿既缺乏深度又少了厚度!故而我们端碗时,失去了碗足的保护。遇上滚烫的汤和菜,就须采取措施才行,比如用托盘或毛巾等隔热。否则端起时手指将被迫与碗底零距离接触,被烫毫无悬念!
想起当年学“人体解剖学”时,老师经常说“形态决定功能”这句话,可谓言之凿凿,放之四海而皆准。
碗足变浅薄了,它的功能必然大大降低!
深度合适的碗足,让你端起碗来得心应手,特别适合我们使用筷子端碗吃饭的民族习惯;厚度合适的碗足,既防烫手又防烫坏桌面,而且洗碗时抓得牢,既有利于清洗干净又不容易滑脱摔坏。
其实除了实用功能,碗足还有美学意义兼卫生学意义。
看吧!没碗独独儿的碗,矮趴趴的耷拉着,形态欠优美,气质不高雅。有贴心碗足的碗,坐如钟貌似鼎,沉稳端庄,器宇轩昂。
碗足还便于沥水和干燥,从而有益卫生。
碗足好处多多,窃以为不该虚化,返璞归真可好。
母亲的悲喜人生
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三,是我敬爱的母亲一百周年诞辰的日子。母亲于2019年2月26日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永远地离开了她深深地爱着的子孙及这片多情的土地。
母亲的离去,留给子女们无限的思念和回忆。百年诞辰之日,儿女缅怀母亲的一生一世,百感交集……
母亲一生,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内容很多。女儿才疏学浅,难以展现全貌,只能将母亲一生素描推出,作为母亲百年诞辰的纪念。
母亲陈景芳,原名徐焱容,1922年农历十月初三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母亲的原生家庭四口人,我外公是教私塾的先生,外婆只生养母亲姐弟二人且勤俭持家,家境尚可。
母亲家乡是黄麻革命老区,幼年就遇上“大革命时期”,战火频发,社会动荡。
1931年在一次“跑反”(方言,指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中母亲与家人失散。失散的孩子们被汇合在一个祠堂内,命运由天。
母亲在失散孩子中看起来干净利索一些,被国军营长陈仲龙夫妇领养,改名陈景芳。虽说叫领养,实则是童工。年仅八九岁,母亲就开始了繁杂辛苦的劳作生涯。小小年龄已然明白“领养”与“亲生”云泥不同,故而苦和累都能隐忍。唯一忍不住的是一个孩子对亲生父母的思念。
母亲身上有一张写着家乡“黄安七里坪”的纸条,一直随身珍藏着。不料偶然被陈夫人发现,她认为母亲要逃跑,暴怒之下将开水泼向母亲,母亲昏死过去。母亲被放在一块木板上奄奄一息,幸遇一位宅心仁厚的良医救治,才大难不死活了下来。脖子周围一大片烫伤痕迹遗留终生。
抗战爆发,陈姓军官奉命赴前线抗日,不久即在宜昌保卫战中阵亡。陈夫人失去丈夫,三个幼女没了父亲,天塌地陷,境况悲哀。母亲善良,尽释前嫌,以德报怨。一家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母亲去客栈洗衣服洗被子挣点钱贴补撑持着。
被现实所迫,武汉待不下去了。大大小小五个女性背井离乡,跟随内迁逃难人群辗转来到重庆石桥铺。因为国民政府抗战人员抚恤机构在此,希望领到抚恤金。在陪都重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后因抗战遗属孤儿寡母着实堪怜,才得以在石桥铺曾家花园寄居。
陈仲龙阵亡在抗战初期,当时国民政府的抚恤机构只是属于铨叙厅的一个科,对抚恤不够重视。抚恤费很少,遗属可悲,对付不了多久又捉襟见肘。
眼看着一家人揭不开锅了,母亲去做苦力活求生存。
一个十四五岁的瘦弱女孩子,每天半夜起来,爬坡上坎,经黄沙溪、虎头岩、佛图关到米亭子,走这么远的路去买两斗平价米背回家。第二天再背到石桥铺市场上去卖掉,赚点力钱一家人勉强糊口。
1942年母亲与石桥铺曾家花园佣工廖炳楠结婚。
1945年父母到小陪都山洞,做手工切面谋生。
1957年公私合营父母转入粮食公司制面合作社。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身强力壮的父亲被抽调到长江边长寿县的重庆川江电冶厂(后名重庆铁合金厂)。受限于经济、时间与交通不便的多重困窘,父亲一年只回家几次。从此,父亲在长江长寿那头,母亲在重庆主城山洞这头。抚养子女撑起一个家的重担,就这样主要落在母亲肩头。有句歌词“父亲是那拉车的牛”,没错!可我家的实情却是“母亲是那拉车的牛”。
父亲工资41元,每月寄20元回家,母亲工资30元,共51元。父母生育了9个子女,一大家人的吃喝拉撒,孩子们陆陆续续要上学要交学杂费……
就这51元,怎么活下去?
李白雄文惊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把蜀道的艰难险阻写到了极致。母亲的前半生之路何尝不是“蜀道”!
母亲一生经历的艰难困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妈妈的工作单位是制面社,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概念,长年累月都是无偿加班制。天蒙蒙亮,妈妈已上早班,去做餐馆和人们需要的早餐鲜面条。夕阳西下倦鸟已归时,妈妈还未归。那时工艺落后,干面条的晾晒、切断、称量、包装全是手工操作,制面机器和工作场地必须每天清理清洁,事情繁多琐碎,耗时费力。
妈妈整个白天既要忙工作又要忙一日三餐,命运让她养成了走路快、做事快、吃饭快的特点。饭熟了她总让孩子们先吃,她忙着这做着那。到头来,剩下什么算什么,剩下多少是多少,她三口两口囫囵吞下了事。很多时候,母亲吃饱没有,可能只有天知道!
母亲起五更睡半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连生病生孩子都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全是母亲无师自通地裁剪,一针针一线线手工缝制出来的。
曾记得,寒冬腊月里,孩子们睡梦中醒来解手,总能看见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不是在纳鞋底就是在缝衣服。
忘不了!冷得哆嗦的严冬季节,我家小学生早上起来居然有棉鞋放在床前。
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妈妈凭借勤劳能干的一双手和伟大惊人的母爱支撑着,坚韧不拔地和命运抗争决不言败,终于让我们九个儿女得以长大成人。我们兄弟姐妹无一人因家贫而辍学,没有谁因穷困而蓬头垢面衣不蔽体。
知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兄弟姊妹读书没让妈妈操过心,家里的破墙上贴了大半壁奖状。这是妈妈最高级的精神安慰和任劳任怨的动力。
63年我三姐考上重庆市一中,因穷孩子考名校的新闻效应,一条街都在传说。可三姐本人不敢说,因为违背了妈妈叫她考中专的决定。家里读书的孩子太多,父母工资多年不涨一分,经济压力太大了!
为了读书及生活,哥哥姐姐们节假日常去孃孃家干活,挑煤洗被洗衣服,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嬢嬢就是妈妈那三个陈姓妹妹,虽无血缘关系,但曾经相依为命的经历就注定了缘分。嬢嬢家子女少、工作好、姨父都是干部,经济条件好得多。哥哥姐姐踏实干活,能得点赞助交学费及补贴生活。三姐就是多亏这种勤工俭学方能高中毕业。
六十年代是最困难的时代,尤其是每学期开学时,母亲心忧学费愁得要命。平心而论,那时我们家还是得到过嬢嬢家一些资助。我们全家从没忘记,我们懂得感恩。
母亲有一颗菩萨心肠,自己再苦再难都乐善好施。
那是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母亲下班回家,见我家街边上有个人在地上摸索着什么。走近一看,地上有碎玻璃渣,母亲心里咯噔一下,柔声相问。
“你怎么了?”
“摔倒了!主要是眼镜落了!我是高度近视眼啊!”
“哦!不要再摸了,地上有玻璃渣喔!”
“没得眼镜我看不倒,我啷个回璧山嘛?”
呜呜……
他一边哭一边还在地上不停地摸着……
妈妈看不下去了,说“你等一下哈,我马上就来”。
转身直奔我大哥珍藏眼镜的地方,抓起眼镜就给了那个可怜人,还给他两元钱,让他赶紧坐班车回璧山。
那可是六十年代啊!我们家何其贫困!大哥这副屈光度四五百度的近视眼镜,是他做苦力挣钱配的。平常他舍不得戴,就把那副断了腿的旧眼镜缠上胶布对付着用,妈妈心知肚明。大哥找不到眼镜心急火燎地问,妈妈道出原委。末了说一句“人家看不见啊,撞到电线杆啷个得了?”
我们那时好傻,只知道玻璃渣会划伤手脚,完全不懂高度近视眼没了眼镜危机四伏。
我们安静地听着,默默地接受着母亲质朴的教育。
母亲可能没多少文化,但这并不妨碍她说出有预见有哲理的话。那哲理虽然十分朴素,但直抵人心且实用。
母亲未能上过学读过书,这是她终其一生都深深遗憾的事情。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掀起了一场扫盲运动。久旱逢甘霖,母亲一头扑进扫盲运动,在谋生养育子女和兼顾扫盲的夹缝中艰难穿行,拼了命地学识字。
通过扫盲,母亲能认识常用汉字几百个了。母亲学识字孜孜不倦且悟性好,想来与其父亲是私塾先生多少有点相关。扫盲后妈妈没有浅尝辄止,而是坚持下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问家里的学生孩子。我们都乐于给妈妈当一字之师。
母亲既有天赋又勤奋,日积月累,逐渐能写常用字,后来能写简单的书信。看报纸几无障碍,看连环画看戏曲津津有味。
母亲童年和原生家庭失散的悲伤,一直在心里隐隐作痛。实在心有不甘,她就把当年走失的遭遇告诉住地山洞派出所,求助公安部门帮忙寻找。在山洞派出所好民警贺纯文的大力帮助下,通过重庆与湖北两地公安部门的合作努力,终于在1964年找到了母亲的亲弟弟。同年,母亲与湖北麻城来的弟弟在重庆见面了。失散三十多年的姐弟俩喜相逢传为佳话,《重庆日报》曾有提及。遗憾的是姐弟二人的父母双亲均已过世。
母亲1976年退休,退休后开始礼佛。
妈妈依然忙碌,因为子女这一代人中已有子女,老人家辅助第二代照顾第三代,爱心满满,睦邻友好。
母亲的品行赢得四邻八方敬重,她的好口碑令我们自豪。
随着子女们的成长和时代的发展,八十年代开始,妈妈终于有过一段相对幸福的时光。
这阶段时而有子女陪伴旅游,老人家时而到子女家走走和带孙辈。母亲慈祥宽厚,生活经验丰富,卫生习惯良好,做饭可口,做事放心。老人家走到哪里就像春风吹到哪里,温暖滋润,倍受欢迎。每当她要离开哪家时,大大小小包括各家的邻居都依依不舍。
爱,应该是双向的。
子女们陪母亲坐索道登上过峨眉山青城山泰山玉龙雪山;牵着母亲的手去看过长江黄河太湖西湖洞庭湖东湖;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杭州苏州香港澳门观光过。成都武汉自不待言,那是去过多次的地方。国外游过新马泰缅甸、欧洲八国和日本。80高龄那年,老人家去北京孙女家看心心念念的曾孙,还尝试了一把飞机头等舱。
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
2016年春天,母亲已近94岁。想到光阴不饶人,我们鼓动母亲参加了“海洋量子号”豪华邮轮十日游。“海洋量子号”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十艘邮轮之一,载客四千多,餐厅就有18个,娱乐场所运动场所也很多很大。邮轮的壮观出乎母亲意料,老人家感到新奇震撼。十日游回到重庆,有外孙问“外婆,邮轮大不大?”一向低调的老人家高调地回答“大得无比哦”!
好开心!双向的开心!
可是,衰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可抗拒。但见母亲饭量越来越小,人也越来越瘦,生命力日渐式微。
在母亲生命最后的70多个日子里,病痛让老人家受苦了!我陪护在病床前,看着原本清秀的母亲变得形销骨立,心如刀割。我们子女包括母亲的侄女轮番24小时陪护,擦屎倒尿,无怨无悔。
母亲是一个平凡人,但又是不平凡的。在我们心目中,她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人!是母亲使子女有亲情,有根基,有力量。母亲的恩德无量无边,无与伦比。
在母亲的高尚品格濡染和言传身教下,儿女们总算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子女中有救死扶伤德艺双馨的好医生,有勤奋务实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有教书育人甘为蜡烛的人民教师……
母亲百岁诞辰,我用这篇倾注心血的散文凝聚子女的一腔真情,献给我们的妈妈,表达子女的寸草心,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亲爱的妈妈,感谢您给我们的爱!今生今世不忘怀!
穿越人生至暗时刻
六月十六日,好吉祥的数字!可对于我来说,这是个记忆深刻的沉重日子。
三年前的这一天,我不经意间跌倒,使我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那是2019年6月16日,夏季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
午休后,四岁的小孙女提出去附近的一个中学玩。那儿有足球场、篮球场,铺设着塑胶草坪和跑道,宽敞又干净。
提议不错,婆孙俩手牵手乘兴而去。
该中学管理比较严格,一般不能随便进入。我嫂子是该校退休教师,住房在校内。那时还没有新冠疫情,说清楚找谁,门卫就准入。
球场上人不多,北半场两个小孩在玩足球。小男孩的爷爷只看不动,长得壮实的小女孩玩得兴致勃勃,她的妈妈在指导。小孙女想参与踢球,我一说他们都表示欢迎。
三个小朋友开心地玩起来,越玩越嗨。有时球踢得远,大人就帮忙弄回去。我看南边缺人,就去南边守着。
忽然,那个壮壮的小女孩飞起一脚,足球从北向南快速地直线滚动,瞬间越过我向南而去。我跑步去追,眼看追上了,一边向北转身一边抬起腿想踢球回去……
“咚”!
只见60公斤65岁的我,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倒在球场上,迅雷不及掩耳!
小女孩的妈妈跑过来,连连问我要不要紧?叫不叫救护车?同时好心好意想扶我起来。我摔懵了,幸而意识尚存,能准确感知是手腕最痛。当时人晕乎乎的,不想说话,我示意先不动。
静静地躺了两三分钟,脑中复盘惊魂一幕……
我确认摔倒时是一双手先触地的,脑袋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一双手,舍车保帅的那一双手啊,正疼痛不已,想必在劫难逃!
不能躺平了,要尽快就医才是王道。在小女孩妈妈的帮助下,我咬着牙站起来,走向求医之路。
家兄是重庆市沙坪坝区第五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从事骨科专业几十年,深耕厚植,医术医德有口皆碑,至今仍被单位返聘发挥余热。
经过我哥检查和拍X光片,我被诊断“双手尺桡骨远端骨折”。我哥说有点严重,详细情况是右手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尺骨撕脱性骨折;左手桡骨远端2cm处横型骨折、尺骨颈突骨折。天哪!我摊上了双手前臂共4根骨头全部中枪的重彩!
这是怎么了?
不久前我刚经历了慈母逝世的悲伤,精神痛苦犹存,身体也受影响。才多长时间啊!又要遭遇双手骨折的摧残!
这是什么节奏?
人生无常!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这下可好!这下可怎么好?
不能吃饭、不能洗漱、不能穿衣、不能用手机……
一双手什么也做不了!却留给我肿胀、疼痛与沉重……
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瞬间变失能人。落差太大,情何以堪?!自己受痛就不用说了,接下来生活不能自理,要给家人增添多少麻烦啊!
一想到诸多麻烦将接踵而至,我被郁闷缠绕住了。当晚,双手前臂因夹板固定着与敷药未干有一定重量,难以适应。感觉一双手无比沉重,放哪儿都不对。整个人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疼痛加忧虑,一夜无眠。
尽管理智告诫自己应该休息,不要想了!但停不下来。
还好,想着想着,让我想起了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的故事。那个伤痕累累饥饿困乏的淘金者,在荒原上与一只病狼对峙决不放弃的情节,曾经极大地震撼过我的心灵。由此联想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那位老渔夫在风雨飘摇的小船上与巨大的马林鱼博击不屈不挠……
突然间,我茅塞顿开,不再沮丧了。
天亮了,我的世界也晴了。
我平静地接受家人的照顾,同时振作起来,动脑筋想办法,尽量减少亲们的负担。比如:端不动杯子就改用吸管喝水;用肘关节下压门把手开门;利用曲肘凸起的鹰嘴摁抽水马桶的开关;手机平放操作不了就让它斜放到最佳角度;穿闺蜜为我特制的极简连衣裙,利用写字台的直角去蹭或挂住裤腰的松紧带可解决内急……
如此等等,行之有效。
与此同时,我谨遵医嘱,按时去医院换药、牵引、调整夹板等。一边虚心向家兄请教,一边自学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手外科的图文科普,坚持循序渐进的带痛功能训练。多管齐下,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早日脱困。
如此这般,骨折愈合虽说还得按“科学发展观”的进程演变,但是努力拼搏兼收并蓄的成绩斐然。大约20余天,我就从中度失能老人转化为轻度了。
“失能老人”是指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指标,一到两项做不到的定义为“轻度失能”,三到四项做不到的定义为“中度失能”,五到六项做不到的定义为“重度失能”。
由于受“洗澡”这一指标限制,我被定义为轻度失能有两个多月。直到骨折12周时狠下心尝试独立洗澡成功,终于作别失能老人这个椎心的称谓。
骨折八周后我去医院拍X光片对比,影像报告“骨折线模糊,有连续性骨痂通过骨折断端”。这表明骨折修复正常,临床愈合达标。但骨折的临床愈合并不代表功能全部恢复,这之间还有不短的距离。
骨折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损伤,修复过程受年龄、身体素质、骨折部位、骨折类型、软组织损伤程度、有无感染、治疗方法以及营养与康复训练等许多因素影响。
由于我已是65岁老人,骨折又比较严重,在及时正确的治疗后出现了预期的疗效,应该知足而乐了!
三年过去了,一步一步走过来,一天一天静下心,一次一次活动手,我的双手主要功能失而复得。我从人生的至暗时刻穿越出来,我坚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