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春特刊|中国作家 王护君 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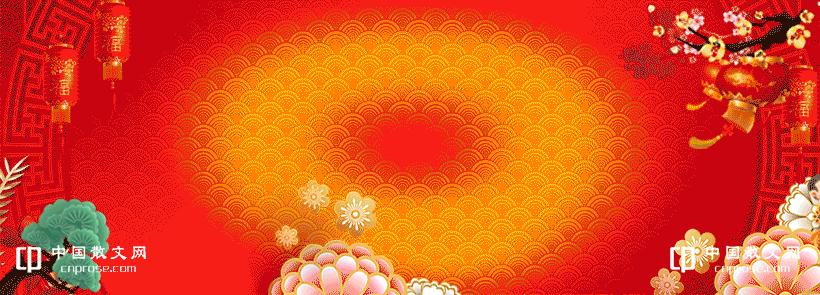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
—— 王护君 作品展 ——
作家简历
★
王护君 笔名山乡村夫。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人 ,大学专科文化,教育工作者,乡土文学作家,一个行走在墨香里的性情男子,喜欢在温暖的文字中寻找一种倾心的诗意生活,常有感性文字散见于网络平台和地方报刊。
桑葚情深
桑葚,是官名,又名桑杏,小名叫桑儿,不知还有什么叫法,反正我们这里一直都这么叫。开春时节,桑树枝条冒出嫩嫩的、黄绿色的小芽,新鲜的芽儿给人以清爽干净之美。到了春夏之交,桑树开始结果。桑儿的果子,小小巧巧的,仿佛缀在绿叶间的粒粒纽扣,又好似藏在枝叶间的小星星,香甜美好,煞是喜人。刚长出来的桑儿,颜色涩清,果实紧固,像穿着一件紧身的外衣。没几天,有的逐渐变成微红,有的变成了鲜红,有的就直接变成深红色,熟透后的桑儿就变成黑亮黑亮的紫红,一个个就像小精灵似的,一颗颗、一串串挂满枝头,向下低垂着,光鲜耀眼,馋得人口水直流,也惹得鸟雀们捷足先登,在枝头活蹦乱跳,一边硺食着成熟的桑儿,一边卖弄着清脆的歌喉,奏出婉转好听的大自然神曲……
记忆当中,那小小巧巧的桑儿,味道特别甜美,那些不拘形状的小精灵们,似乎是对孩子们一种特殊的眷顾,而对我们这些穷山僻壤的孩子们来说,那简直就是人间仙果。放学回家,狗成子、牛儿子、拴狗子一伙儿,书包一扔,就迫不及待的往桑树底下跑,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脱,就像猴子一样“噌”的窜上树去,盘坐在桑儿最多的,果粒较大的树枝上,看着颗颗桑儿胖乎乎的在微风里摇曳,兴奋地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伸手就去摘着往嘴里塞。摘得一颗放进嘴里,轻轻咬一口,发出微微“吱吱”的声响,一股清甜登时从舌尖漫溢开来,直到嘴巴被桑果的汁染成紫褐色,脸也染成了大花猫,这才溜下树,抹把脸,心满意足的回家去。
“走,摘六唤子家桑儿走。”这是夏季开始庄里最响亮的声音,也是每年必不可少的声音,一群土匪般的野孩子们笑着,嚷着奔向了六唤子家的桑树低下,那个树股上桑果繁,那个树股上便接满了孩子,够得着的地方早就被捋光了,够不着的,就找来一根粗细适中、长度足够的竹竿,再把铁丝做成钩子绑在竹竿上,伸向桑树枝条,轻轻一勾,缀满了果实的枝条慢慢垂了下来,树下的人仰起头,伸出双手飞快接住,小心地摘下紫黑色的桑葚,摘着,吃着,吵着,“哎吆,六唤子他答拿的棒来了!”“噗通”,“噗通”,一下子跳下树都跑光了,直到这会儿,树下才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五月中旬的单家湾已是绿意葱葱,花香四溢,从西头的后梁到东头的绿化峁,绿草覆盖着往日的黄土沙洼,桑树早已挂满了硕果,在晨雾里分泌出淡紫色。于是,麻雀,微风,大地都等待在宁静中,阳光,水分中分享它的甘甜,这时桑树已经不见一朵花瓣了。展露出淡红的、红褐色的桑儿来,蜜蜂、小鸟们争先恐后的飞来飞去,不知是偷吃还是闻着香味……
彭阳这里冻土时间长,不生蚕蛹,更没有人去养蚕蛹这名贵难养的东西,所以桑叶是无用的。但是,今年的气温忽高和低,极不稳定,早上艳阳高照,一转眼就是大雪纷飞,冷的发颤。整的那些爱美的靓男倩女们都换不极衣服,冻的清鼻眼泪,申唤连天。过了四月八,天气转暖,气温逐渐回升,棉衣要换成单衣,这,就意味着摘桑儿的时节快到了。
摘桑儿,旧床单是采集果实的绝佳工具,四个人在树干底下扯着,一个人上树抖动,桑粒收集在床单里。虽然床单近乎废了,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蜡染“艺术品。”可收获的快乐却让你惬意无比,甚至还能吃到香甜可口的桑儿,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老家单家湾属于宁夏西海固,是生态移民区,村民们响应政府号召,都居家搬迁到千里之外的兴庆区月牙湖了,所以,无论是打蕨菜的,还是摘桑儿的,都无所顾忌,没人拦挡。每到这个充满诱惑的季节,总有人张罗进山采桑儿,打蕨菜,拾地软等等,闲情逸致,可想而知。山坳平缓,也不知什么缘故,溶在太阳光里的树林梢头,草地,红的,黄的,白的和嶙峋的砂石,泛着光辉,放着异彩,冒着幻想,我想,田园之美,不过如此罢了。
这桑粒采多了,也是愁人,吃不了很快烂掉。学着老家人做果酿,泡药酒。一坛桑葚二两酒,酒的度数越高越好,散白干烈性,封坛半个多月,滤出紫红汁,一碟咸黄瓜条,一杯酒,或者一碟花生米下酒,这酒劲喝少了甘甜,喝多了亢奋上头,天灵盖都感觉有雾。
我们这里有谚语“屋前不栽桑,屋后不插柳”的说法,山里的桑柳是大自然的杰作,鬼斧神工,福兮祸兮自有深趣,也早有安排。《诗经》曰:蚕月条桑,取彼斧斨。攘之剔之,其檿其柘,诠释了对桑枝的描述和赞美。
也曾有文人抱怨,这山无百果,树不参天,砂石遍布,毫无观赏价值,植被多以小灌木乔木为众,以穷山恶水之不屑。就显得浅薄了,既然欣赏,至少要有底蕴,分明的远山近水,在大写意似与不似之间,想像平庸者观其平庸,瘦石,病柳,枯杏,一叶扁舟,历来是墨客的追捧者。而这独特山峦在迷雾叠嶂时,将天地全然隔绝,浑然不留一丝罅隙,正是实派画家的一手好素材,美不在于背景,而在于慧眼独具的角度。
岁月更迭间,已经不再是搭伙成群摘桑儿的年代,采野果,拔狗娃花,拿柳梢拧咪咪,绊脚、打架、攀爬沟壑山崖的趣事更是望而兴叹。儿啼那令人神往的时光已悄悄地从腋下溜走了,好在绿意五月,网上南方转运的人工种植桑葚也开始上市,馋嘴时买来尝尝也不失一种补益,颗粒饱满,颜色尚佳,即不媚俗,也不欺世,何乐而不为呢。
“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桑儿味浓,故乡情深!
心中的黄土地
家乡在生态移民中搬迁了,那块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也将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我这个在那里出生的山乡村夫,像一片落叶在天空中慢无边际的飘旋,像离开母亲的孩子怅染无着,家乡的黄土地将要永远地留在记忆里,久别的思念和久违的忏悔萦绕心头,如烟似雾,挥之不去。住在设施齐备、窗明几净的楼房里,思绪就像放飞的风筝,飘荡在记忆的河流上空,却总被那块土地牢牢地牵着,永远飘不出心中的那块厚厚的黄土地……光屁股的时候,母亲常说:“人是从土里来土里去的。”我忽闪着好奇的眼睛迷惑不解,常常陷入稚嫩的遐想:人是不是就像土豆一样从土里刨出来又埋下去?等到上学前疯玩的年龄,我对黄土痴迷成癖,成天与小伙伴在黄土上厮混。每当谁家修房打院,那一堆堆松软的黄土便成了我们的乐土,或是爬上高高的土坡大声叫着:“燕面馍,蘸辣子,谁不吃,成瓜子,得儿驾,一截子。”然后就像鱼儿跃入大海纵身跃下,只见尘土飞扬,笑声一片;或是选个平坦的土滩,抖擞精神,摩拳擦掌,来个“搂花腰”式的古典摔跤,只见兔起鹘落呐喊雷动;或是拣一堆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绵绵土,然后脱光衣服把身躯埋在金黄的土中,嘴里吹着土雾死劲喊着:“双扇门,大亮开,里面住这个女秀才。养个儿,会种地。养个女,会扎花。大女扎个牡丹花;二女扎个水仙花;剩个三女不会扎,一把打到案底下。妈,妈!你别打,我给你烧锅抱娃娃。”只见阳光和煦,土头攒动……直到母亲焦急地呼喊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堆黄土。这时,定有谁把鞋子陷进土里找不见而不敢回家,或是谁把裤裆扯了哭鼻子,但第二天照样疯玩。天天疯玩。突然有一天,外婆把我喊到身边,庄重地说:“去,找个干净的地方搬点干净的土疙瘩来!”我不辱使命的完成了任务,只见外婆异常虔诚地把土疙瘩打碎,向锣面一样锣出了绵绵土,然后摊在热炕上焙得暖烘烘的。两三天后我的小妹出生了。看到她红润的身躯沾满了黄土,我似乎顿悟了,我来带人世间的一瞬间,首先也接触到的是母体般的黄土。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儿时的记忆里依然充斥着饥饿和寒冷,是黄土驱散了我心中的饥寒。为了有个着风挡雨的家,父母用自家的自留地和别人兑换了一块据说是风水较好的地,选了个坐北向南的地方,每当下午生产队散了工,粗粗地吃点东西,便领着哥哥和我挖起窑洞来,只挖到夕阳西沉,月上柳梢,暮色沉沉。就这样,一镢头一镢头的挖,一铁锹—铁锹的铲,一担一担地担,硬是打出了两孔窑洞。当安好门盘好炕时,住在‘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窑洞里,睡在煨得烫烫的土炕上,心中被焙得荡漾起层层暖意和温馨。为了能种点庄稼填饱肚子,母亲领着我在自留地里吃力的挖着长长的苜蓿根。忽然有一天,一镢头挖下去,挖出了老鼠攒的一大窝糜子,足足有半斗。母亲和我欣喜若狂的拿回了家,用清水反复的淘了又淘,等晒干后用石窝捣碎,做成了糜面发馍。我第一次放开肚子吃饱了饭,那种腐霉而微甜的味道深深地留在了我的灵魂深处。对温饱的企盼是我对土地更加膜拜和依恋。土地承包后,我家共分了山川共三十几亩地。有了土地,人心中就有了底,父母领着我们耕种、收割、打碾。丰收的喜悦像醇香的美酒,每到初秋时节,玉米成熟、瓜果飘香时,老家的那口大锅里装满了我的口福,锅底是迸开了皮像白牡丹似的土豆,土豆上头是喷香的毛豆,毛豆的上头是绵甜的南瓜,南瓜的上头是香甜的玉米,玉米的上头是雪白的馒头。一顿饭下来,吃得你大汗淋漓,肚儿圆胀,口齿留香。憨厚的土地用丰厚回报着耕耘,耕耘的感觉在我的生命中是唯美而诗意的。天还在睡意朦胧中准备睁开惺忪睡眼时,我已干着自家的两头黄牛,扛着犁,哼着小曲,优哉游哉地上山了。到了地里,套好牛,握紧犁,一声吆喝,一串鞭响,黄澄澄的土便被哗哗地犁开,空旷的山谷中便只有我和牛犁土的声音,这,活脱脱的一幅田园交响曲。在长长的犁沟里播种着我幼小的希望。牛困人乏时,母亲就会准时提来咸菜白馍地椒茶。此时此刻,咸菜就白馍,胜过了山珍海味;仰头一壶地椒茶,胜过孙悟空在瑶池喝过的玉液琼浆。那个美啊,只有在人困马乏时才能找出的那种感觉。然而,终于有一天,父亲也要和先人一样魂归黄土了。我在他耕种了一生的土地里选了块坟地。等挖好了墓穴,,我跳下去检查偏堂的宽敞程度,睡在黄土地下,与土地肌肤相亲,嗅着新鲜的泥土气息似乎有一种母亲才曾有过的奶香,忽然有种躺在母亲怀中的感觉,酸涩的泪水滚落在偏堂的黄土里,冥冥之中似乎又听到了母亲的摇篮曲:“哄娃娃,睡觉觉,睡着醒来要馍馍,馍馍啦,老猫叼……”在阴阳肃穆的超度声中,父亲躺在了他辛苦一生的土地里,我在黯然之中思忖着“入土为安”的内涵。是啊!人吃黄土一辈子,黄土吃人刚一口。人从土里来在土里长而终要到土里去。离开家乡的那块土地竟那么多年,可我灵魂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都在那里。无论走到哪里,总忘不了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我深深的眷恋着那块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我的那片黄土地。
老家的月亮
离开了家乡在外流浪
漂泊的我只有一身风霜
疲惫的时候向夜空望一望
看见的就是那老家的月亮……“梦中,没有梦见闰土,没有梦见貒,却梦见邻居胜利家的黑狗在追我……
梦中有家,心之所向。但每当一觉醒来的时候,还是睡在山城和平小区的卧室里,毫不犹豫的说,舒服极了,可心却一直都在向往着老家。家,是我们开始的地方,也是我们一生兜兜转转离不开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年龄越大,越想回老家居住,也许,他乡只是打拼,故乡才是归宿。人的一生,永远都在回家的路上。
魂牵梦绕的老家,是一幅童年和乡愁完成的年画;亲切温馨的老家,是一条心灵依托的温馨小巷;充满母性的老家,是一个永远吸引着游子回归的磁场;诗意悠长的老家,是一曲悠扬而清新的歌谣永远在心灵回荡。
和任何一个天涯游子一样,我非常喜欢老家,也愿意在老家生活下去,一直到满头霜发,其实,谁不喜欢老家呢?那陈旧、低矮的瓦房、草棚,大杏树,一群小鸡,和那条卷着尾巴的大黄狗……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标志性的老家,就成了每个人难以割舍的牵挂。
和那些常年在外打拼的那些人们一样,只要时间一长,也就会有着一种强烈的乡愁;也就会想看看那轮弯弯的月亮,唱出那撕心裂肺的《老家的月亮》也就会想走走那幽静的羊肠小道;也就想着爬爬那雄浑的大山,也就想看看那清澈的溪水流淌。这时候,游子的泪会不参杂任何成分的留下来……
岁月沧桑,年龄增长。思乡的感情也就会更加强烈。如果再将那房顶上飘逸的缕缕炊烟集攒起来,而把思乡的情节再绵长一些。那么就会感到“月是故乡明,悠悠天宇旷”,的境界更加清晰。
说实话,我的老家很贫穷,虽然抹掉了穷困的帽子,但实际上只是解决了温饱。我的老家很简单,没有名胜古迹,自然也就没有名人大官。但我和众多的农家子弟一样,深深地,深深地爱着老家。爱老家的后梁:爱老家的菜沟洼,爱老家充满神奇的马莲滩河……
老家,越住越亲切,越住滋味越浓。我只想永远住在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进出一扇门,住一间房子,睡在一张床上,年年守着一个人,只闻花香,不谈悲喜,这种幸福,是那些出远门的人无法享受的。人们都说听风懂雨,一个地方如果你住的时间长了,肯定能听懂风声、雨声、水声;知道草木的语言,山野的冥思;懂得大地的意义,原野的梦想。
老家的白杨树湾,马鹿湾、剡家洼、还有那神奇的打炮窑梁、高不可攀的峁儿尖山……老家,风景很美,美得让人热泪盈眶;老家的味道很香,香得沉醉了人们的心房;老家的山野很高,高得让人们总想爬上去仰望;老家的溪水很多,多得到处分成了小河,多得到处都是山泉水。这几年,抓住商机的人竟然把老家的山泉水拉到城里卖,一桶十二元。
网上最近流行很火的一句话:他乡容不下灵魂,故乡容不下肉身。这话好像顺应了这个时代一样,这么恰如其分,一个人呱呱落地、哭嚎着来到小村庄,妈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严父慈母呵护下长成美女帅哥,再由各种原因背离故乡、背上行囊、踏上征程,有的功成名就远离了故乡,有的跟随儿女远离了故乡;有的成了贪官污吏永远回不了故乡。
老家的月亮那么慈祥
像母亲温柔而坚毅的目光
无论我离家的路有多么长
抬起头你始终在我的心上
啊老家的月亮
啊母亲的目光……”
在山村里长久生活下去,守望着老家。守望着土地,守望着已故先人的坟茔,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愿望,也许有许多人,都在企盼着,都在向往着,永远也不离开故乡。
老家的地虽不肥沃,却能安放灵魂;老家的地虽贫瘠,但能长出茁壮放心的庄稼;在风调雨顺时,庄稼饱满丰收在望。
老家住久了,也就是老家的一部分。就连岁月,也无法将彼此分开。老家并非那么完美,但却是一个好的地方;老家并非那么富裕,但却有着一种古老的风韵;老家并不那么美丽,但却像母亲一样在哺育了我们的成长;老家并不那么出名,但却让人感到它奇香四溢,清秀淡雅、十分清爽。
老家,是一种岁月。是年龄越大,越想奔赴的地方。老家,当是我们疲于奔命时最温馨的退路,是我们孤独彷徨时最温柔的依靠,是我一生幸福的向往,也是我们年老时最温暖的归宿,美丽的老家,愿有一座院子,安放我心,与爱的人相守,花开花落,幸福绵长!
啊老家的月亮
啊母亲的目光
孩儿默默祈祷你幸福安康
愿你慈祥的目光永远明亮
愿你慈祥的目光永远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