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春特刊|中国作家 李爱萍 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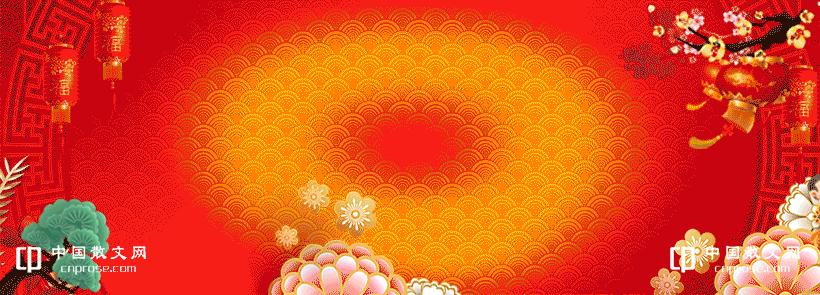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
—— 李爱萍 作品展 ——
作家简历
★
李爱萍 生于1958年10月,女,汉族,内蒙古包头市人,下乡五年,七十年代返城,参加工作。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包头诗词协会会员,包头市作家协会会员,包头市青山区作协副秘书长,包头市民间艺术协会会员等职。已出版《情丝集》《春之歌》《幸福童话》诗歌、散文集。多篇散文诗歌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并被收录专辑。在读书写作之余,还喜欢苏绣、剪纸等。其中布艺画《孔雀春英》、《朝阳》、《玉鸟》、《花房的早晨》,苏绣《奥运福娃》、《牡丹富贵图》,剪纸《延安精神》等多幅作品在各级艺术展中荣获最佳作品优秀奖等。
故乡剪影
虽然头已染霜,但那远去故乡的乡村生活和故事总是与我快乐的童年相逢,只要闭上眼睛一想,都会来到面前。
1、山雨趣纪
那天晌午饭后,我正沉浸在午睡梦中,突然被雷声惊醒了,听见窗棂上响声很大很乱,我睁大眼睛,看见雷雨像瓢泼一样夹杂着冰雹,哗啦啦下起,好大好大,麻纸糊得窗户,哪经得住这么大的冰雹。冰雹透过小窗户,一粒粒落在炕上,白白亮亮。爷爷奶奶都站起来,一把把炕上的白羊毛毡子卷起来,堵在窗户上。雨下了小一会儿,麻纸糊的窗户被打开好多小洞。我从小洞眼儿向外眊外面雨后的禾草和山谷。突然,山上的雨水流下来了,轰隆隆,声音很大。有人喊:“山洪来了,山洪来了!”
我急急忙忙跑出家门,和小伙伴儿们一起忙着朝河边儿河边奔去,小伙伴儿们纷纷挽起裤腿跳进冰凉的洪水,开心地玩玩儿起打水仗。大人们则站在河水两边儿看红火。洪水声和孩子们的笑声交融在一起,像赶庙会一样热闹。
转眼雨过天晴了,后晌的时间和每天一样,有人过来坐坐。上了年纪的东院儿大妈手里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进院子,我看见忙跑出去迎接,奶奶的小石屋只有半间大,来人进门就上炕。农村的夏天也烧炕,只是每隔一天烧一次。大妈进屋,奶奶总是让她坐在锅头最热的地方,记得大妈总爱说一句话:不用坐在老锅头,你们家的炕坐在哪个地方,都是满炕热满炕热。听到这赞扬的话,我就更感到奶奶的炕头热了。于是大妈这句话许多年都记在我的心底。
太阳快落山了,大妈说:“羊群快回来了,我也该回家了。”话未落,羊群就随着呼隆隆声响着,合着一股羊羴气进村儿了。各门各家的羊,不用主人出去领,都认识自己家。我和奶奶把切好的萝卜端给羊儿。我抱起可爱的小羊羔,看它们开心的吃、开心的叫。我也开心地看着它们笑起来。
2、有趣的小路
有趣的小路是我的童年,是我的记忆,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盛夏的黄昏,我独自一人去大姨家。从爷爷家到大姨家,两个村庄间只有二三里路可走,大路就有些远了,不是为抄近路,而是那条小路真得很有趣。出发了,我快步走出村庄,一路追着蝴蝶飞舞,一路和小草野兔赛跑,一会儿就走上了那条光光溜溜,曲折蜿蜒,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小路。我蹦蹦跳跳下来一个小斜坡,马上又上来一个小陡坡。我的身体直直下去,又直直上来,因为我的速度极快,这样反复了几个小坡,才走上了平地。平地上有好多野草野花,扎个花环挂在胸前。蹲下来抓了几个蝗虫,有灰色的,有绿色的,很好玩儿。有大肚子的,一点儿也不可爱,我就把它放回了草丛。走着玩儿着,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大姨家,我悠闲地进了门,大姨忙拿着毛巾,笑着擦去我脸上的汗珠。几十年了,那条有趣的小路还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3、山路蜿蜒
这条蜿蜒小路就像一条彩色的带子,一头连着大姨的村子,一头连着我家的村子。大姨家的村子比我们的村子大。那村子里有一所用黄土围成的破烂的小学。我一个乡下孩子,为了上学,每天需要跑十来里山路。为了少花钱,我每天往返四趟。中午不用在学校吃饭。妈妈在油灯下为我缝制的鞋子,也不知磨坏了多少双……
这条乡间的小路,随着山地的起伏,忽高忽低。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也时隐时现,就像在茫茫的大海里撑着舢板似的。这里四季分明。我纳闷,为什么老天爷把四季安排的这么有序?春天,小路的两侧长满绿色,向阳的坡坡上,繁花似锦,到处是打碗碗花、苦菜花、黄连花……蝴蝶在上面翻飞,被山风一吹,就像一片片彩色的树叶儿。小路的背阳处,绿草一片。小鸟儿在上面跳来跳去,吮吸着草尖上顶着的露水珠儿。冬天来到了,小路两边的庄禾和野草、小花都枯萎了。一场大雪把整个世界变得那么洁净、那么单纯,路边的庄禾、野草、小花都覆盖在厚厚的积雪下面,胖乎乎的臃肿得可爱。小路被皑皑白雪覆盖了,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只好拿起长长的木棍儿,就像盲人探路。每天往返几趟,我们便丢掉木棍儿。小路又被我们踏出来了,变得又光又亮,走着还奏起一种美妙的沙沙声响,走起来大家都感到很惬意……
转眼又一个学期开始了。小路两侧的积雪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地消失了,变成了一缕缕蒸汽,向空中散去。这一天,老师把我留下,要我参加节目《春之歌》的排练。排练结束以后,天全黑下来了。老师要送我回家,我不让。我勇敢。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有一条小路,通向大自然,它光亮、无私、蜿蜒、昂扬,真诚地指引我向前……
4、屋檐下的小草
那夜,屋檐下的小草萌动了。他醒了,被生生移在了四周什么也没有的高墙上。他站在墙上远望,自己显得那么渺小。转眼间,风雨烈日袭来,他倒下,起来,又倒下。小草落泪了,此时却没有谁能看见他的眼泪。
天上的星星看着他,他又一次坚强地站起。风雨袭来,他真的,真希望有什么可取暖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他累了,真想靠一靠,看看四周,没有树木,没有可依靠的东西,只得硬撑着。
又是一年,小草在高墙上目送着去去来来的日子,不管怎样,日子还要过下去。我真该庆幸小草的生命力,他应该得到的并没有得到,当得到的一瞬间还要失去。不管弱和强,按理说都不能抵挡,但我似乎又看见风雨中高墙上的小草,却依然还活着。如果思索和绝望,站在你左右,中间会不会出现一条路让你走出荒芜?
又是一个快速升温,快速降温的天气,让你措手不及?你空白的目光,留不住飞来的私语,除了修剪自己,雕塑自己,也只有修剪自己,雕塑自己。
我相信终会有一天,这小草也能展露一个笑脸。希望终会到来。小草的种子会经过风雨春秋,又被带回到山村的屋檐儿下,回到那个久别的家。小鸟为他带路,久别的朋友与他相拥。和暖的风吹来,又随风舞动,彩蝶飞来与他亲吻。它快乐地开出一朵小花,花朵闪着金色的光。我又看见小草与我那段幸福的童年相逢,目光脉脉含情。
春天在哪里
这是我的大姨。
大姨偏爱小孩子,尤其是女孩,我们都曾是她的心头肉,都得到过她的呵护。今年,大姨认为自己老了,说自己干不了活还麻烦别人,脑子坏了不够用,什么也记不住……总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政府不断派人来看她,又送粮又送油,有困难还给解决。
乡亲们劝她不要多想,想多了伤脑子。
大姨说:“吃不成问题。去年的粮食现在还有,没全部吃完。村里的乡亲隔三岔五来人嘘寒问暖,小辈、平辈还给做点好吃的,顺顺口……”
我说:“那你为什么总不高兴?”
大姨说:“是身体这盘机器各部位都有问题了,修不好了,看医生不管用。”我在苦想,这可怎么好?病痛别人替不了。
让大姨高兴起来真不容易。这阵子住在大姨家,想尽办法让她忘却烦恼,减少一点痛苦。有时讲笑话叫她开心,有时回忆与大姨在一起度过的快乐童年。她带我们去草地采摘野花,扎花环戴在头上;偶尔也带我们去逛交流会,口里含着她买的糖块、去召庙转经筒;领我们一起去邻村看电影,三步并两步,大姨总是和我们一起走得很快很快。我们快乐死了!每当这时她才偶尔笑一笑。
几天来为她老人家,不停洗着衣、被、床单,自然水用了不少,那废水便顺着门口的坡地流。今天向外倒水的时候,散见门口台阶下点点绿色,台阶石缝中也挤出了绿芽。我又惊又喜,这些绿芽还分不清是树苗还是小草,嫩嫩的,就像初生婴儿的小手一样,娇柔鲜活。春天就在眼前了,我兴冲冲拿好洗衣盆,推门进屋,对大姨讲:“您看,现在进四月了,转眼五月,这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眼看房前屋后万物都泛黄了,门前的杏花桃花也要开了,你的病一定会随着春天的到来好起来,您不用发愁!”
这之后,我每天要看一看门口台阶下的绿色。告诉大姨小草多高了,杏花绽蕾了。才几天功夫,这小嫩芽一天一个样。又几天我告诉大姨,杏花开了,接着告诉她桃花也开了,小树的枝芽也舒展了……由于我把这些生物的变化不断相告,大姨的气色逐渐好起来,眼前似乎看到阳光,一亮一亮的,大姨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心情好,日子就过得快。春天小草疯长,给大地换上新衣。这时,大姨想晒太阳,坐在草丛绿地,黄刺梅开满村头院落,我站在一边,仿佛又沉浸在这里童年的日日夜夜;家乡的春天草长莺飞,鸟语花香,小伙伴们尽情吮吸着大自然带给他们的精气神,在田野插下丰收的种子,插下又一年的希望。此时大姨的脸上,分明地漾满喜色,漾满憧憬。
花开草绿的季节,给生活添了激情。大姨说:“我有精神了,把火炕修一修,再把窗户重新糊一糊,窗花换一换,把墙壁刷刷新,把……”她的心情格外喜悦,身体也有了架势,终于能站立走路了。
五月中旬,大姨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土坡上采了些野花,用柳条编起一个花环戴在了头上。我看到了,从内心笑出了声。看到她老人家能自理了,病已无大碍,我也该乘车回城了。透过车窗与大姨告别,心里仍有些莫名惆账,但吮吸着这馨郁的春天气息,感受着这满目生机绿意,立刻兴奋地和大姨挥手告别。大姨显得格外精神。我默默点头,感谢春天的到来,愿春天永驻人的心田。
“知青”那些日子
今天的人们,总是拍好多的照片,看着照片讲这是在哪里?那是在干什么?对着照片讲出好多有趣故事。
以前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无数画面都在脑海凝成身体的一部分,变作记忆的影像。
1975年,我报名下乡了。6月18日,一个院的青年们,都坐上一辆敲锣打鼓的大卡车。送别的人们有的掉眼泪,有的祝福。这些好像与我毫不相干,我只管把大红花正正地挂在胸前,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
这一批热血青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被安排到包头市郊区河东乡壕赖沟村,卡车到了村口,村党支部书记和老乡们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一栋给知青安排好的平房。书记说先喝点水,上炕歇一歇,等一等大食堂的饭就熟了。这算是走进社会大学的第一堂课。吃了食堂的大锅饭,队里就让我们自己做饭了。去地里劳动要走很远,收工回来再担水做饭,刚吃完饭又该走了。同屋的知青从一开始都各顾各的,到后来一起劳动、学习,才慢慢熟悉起来,变得相互关心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犹如上天给了我们5年吃苦的机会,在乡间得到一生都无法得到的锻炼。从十几岁到二十来岁,乡亲们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都显得那么亲切。在农村,因为我劳动好,还被村里评上了劳动模范,得到了大红奖状,我像小学生一样高兴得拿回家给家人看。母亲没有表示多么高兴,因为她看到我被蚊子咬得满身大包,就像一颗颗玉米粒那样大。
我下乡的地方以种蔬菜为主,大田不多。我们平地、担秧、栽秧、施肥、撒粪、间苗、锄草、拔麦、装车、跟车送菜。有一次队长分配我们翻粪,很大的一堆,我们一锹一锹地翻,两脚穿行在翻起来的粪堆中间。
队长说:“只有一锹一锹的翻过后,沤好才能用,娃娃们不要嫌脏,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两年后我们知青和回乡青年被公社调到“引黄工程”挑大渠。渠开口十几米,深十几米,挖得深了就溢出水来了,穿上水靴继续挖。我们挖渠用的是条子锹,一锹下去连水带泥,满满当当,往地面上扔,需要使出全身力气,甩开膀子大干。一天下来,累得五脏六腑全痛,但吃饭很香,一顿能吃好几碗。
在工地我们知青抬过大青石、和水泥、搬砖、抬檩子,组长指到哪干到哪。半年后,领导通知要把我调到工地钢筋组。
工地广播站很是热闹,还放一些革命歌曲给我们听。公社下来记者采访,无意间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时发现我的手早已被锹把拧烂了,满手是泡。她还想问什么,但见她泪水在眼睛里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几天后,包头电台播出——《“引黄工程”第一线知青不怕苦不怕累的感人事迹》。巧得是爷爷奶奶正好听广播,听到了我的名字,高兴地到处说。当我去奶奶家的时候,爷爷奶奶笑得真开心,还一个劲地夸奖我。爷爷奶奶要留我多住些日子休息休息,因怕误了劳动,尽管一百个舍不得爷爷奶奶,还是很快赶到热火朝天的工地上。
钢筋组的工作是为准备打预制板弯钢筋,师傅教我怎么弯,我立即就学会了,一鼓作气地干。师傅出去办事,回来一看,我已经把下好料的钢筋全部弯好,像小山一样堆了起来。师傅惊讶极了,拿去放钢板平台上检查,没想到全部合格,赢来师傅们不绝口的夸奖,我却躲在一边不好意思地笑了。
“引黄工程”结束后,我们又回村里。一年一次的全村大会在大礼堂召开,知青必须全到,家家户户能来的都要来,凳子坐满就站着,人好多,气氛比我们在学校的大会还活跃。老乡真爱发言,都敢说话,就像过大年。
老队长站在台上,有趣地说:“知青同志们好好听着,夏天各种蔬菜都熟了,菜上市,你们摘什么就吃什么,摘茄子就吃茄子,不要每块地乱串。”
有位掏大粪的老大爷说:“我咋办呀!就也能吃个柿子解解渴了?”
会议礼堂笑声一片。
每年的春种秋收,虽然很辛苦,但是,当我们享用到自己的双手创造的劳动成果时,心中总是抑制不住地激动。尤其是年底分红的时候,更觉得自己对社会对家庭是个有贡献的人,感到非常骄傲!
我们的日记再也不是像在学校写得日记了,今天帮老大娘拿东西,明天帮老大爷推车,到最后什么也写不出来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们推着知青自己设计的铁皮小推车平整土地,捧着自己种出来的各色蔬菜,似乎眼睛里有一道天然的彩虹。我们的皮肤在农村晒黑了,身体结实了,我们的生活变为了一本本厚厚的日记。
我们的知青同伴们没有丢脸,个个舍力气,不掉队,村里人说知青比回乡青年都能干。一个个年轻生动的身影,活跃在那个年代。大家一起劳动、吃苦、欢笑。每一滴汗水浇灌着我们年青的花朵,我们真地长大了。
知青的那些日子,成了我一生的精神财富,感受到脚踏实地的泥土芬芳、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提起知青的那些日子,就像是昨天,一张张知青兄妹们的面孔历历在目。我们的青春就定格在那个年代。知青的日子虽然已过去39年,却留给我们心中一幅幅彩色的图画,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