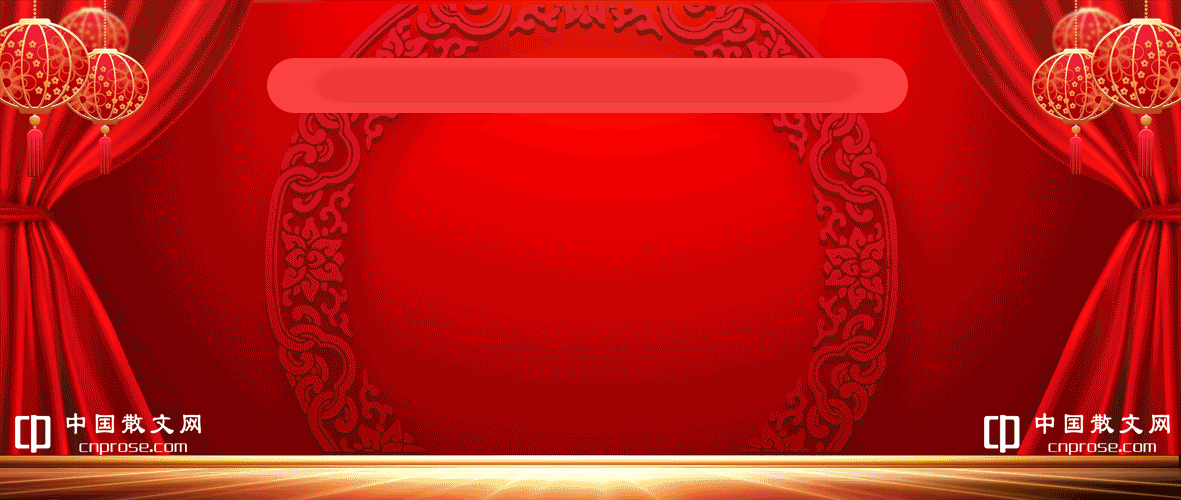【2023国庆特刊丨当代作家 薛毓文 作品展】

艺 术 简 历
薛毓文,现居太原,作家、记者、特约撰稿人(评论员),作品多次荣获国内、省内奖项。近年来主要从事有关乡土民俗、生态文旅、经济社会领域主题的创作,数十万字的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山西日报》《山西晚报》等报刊及诸多知名网络平台。
作 品 展 示
老屋如歌
每次回到故乡,总要在老屋前驻足许久。看着看着,倒仿佛在读一本厚实的书。那一格格的窗户,分明就是一个个会说话的字符,在诉说着老屋的前世今生;那砖与砖之间用白石灰勾勒过的层层缝隙,显然又是一行行跳动着的音符,演绎着老屋如歌的岁月。
老屋也就八十多年的历史,是黄土高原上典型的土窑洞,外加砖接口子。虽比不了纯粹由砖石砌成的窑洞结实,但较之于传统的土窑洞美观耐用了许多,冬暖夏凉。不仅不用担心因雨水冲蚀而导致门面上黄土的过快流失,而且窗户面积也扩大了两三倍,一年四季亮亮堂堂的,住着舒服。
最初的老屋只有两孔土窑洞,是“一炷香”门窗的那种,所谓“一炷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指的是门窗长宽都很短,形状像一炷立起来的香,由于考虑承重承压问题,黄土高原上的土窑洞开口都不敢太大,大致都是如此。后来扩建成四孔大窑洞、三孔小窑洞,耗费了二十一石谷米。小时候没有“石”的概念,母亲说,三斤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这样算下来,整整六千三百斤粮食啊!如果放到现在,当然值不了多少钱,但在纯农耕时代,算是不小的支出,即使村里大户人家也是多少年才能积攒下的财富。而我家自祖上就显然不是大户,十几亩薄田只够勉强维持生计,上学时家庭成分一栏填着的都是贫农。这几千斤的谷米是用一匹骡子换来的。父亲年轻时忙于生计,赶着两头毛驴常年跑太原,半个月一来回,驮走的是老家的红枣核桃小杂粮,运回来的是洋布洋碱等工业品。一次被日本人扣在今天太原的大南门一带四十多天,每天灌辣椒水,非说他是给八路军干活。经营救脱险后为了驮得多,跑得快,换成了骡子,家乡解放后投身农村工作,就将骡子换成谷米修建了这组老屋。
老屋修好后,村里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要在老家结婚,父亲便将最东头的一大一小两孔窑洞以象征性的价格让给他,几年后爱人随迁,便归了他的兄弟,从此两家结了几十年的好邻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继续东扩,将原本两孔烂土窑砌了一大一小两孔砖窑。而最西头的一孔半窑洞说命运多舛一点都不为过,在那个特殊年代被收走,先是用来札棉花,后是弹棉花,那白天黑夜哒哒哒、嗡嗡嗡的声音实在搅得人心烦,打了堵土墙后闹心的杂音问题也没有解决。七十年代末开始落实政策时,两位兄长写下厚厚的申诉材料,但与母亲商量后还是没有交上去,主要担心胳膊拗不过大腿。因为其时父亲已经不在了,而同时期的人有的也早已身亡,许多的事实没法对证,而村里主事的依然是当年那些人。果然没多久,他们便商量将窑洞卖掉,偶然间得到消息后,母亲反复找大队不成,找到公社领导,公社答应应该优先卖给原房主,并且写了字条。谁知早已串通找好了买主。一向和善的兄长动了怒,又有公社的意见,事情出现了转机。虽说自家修的窑洞自己又费尽周折掏钱买回来,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因为买回来的不仅是屋,而且是理,对于母亲,买回来的则既是她的心血,也是她的命。
我刚调往地区不久的一个春天,回家看望母亲时,大门外有几个晒太阳的乡邻。照例给他们发烟抽的时,绳顺不经意地说,老屋东边邻居家的窑洞要卖。事实上,他们的孩子都在省城安了家,老两口多年前也住进了新修的砖窑。我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好像听说过。我便将绳顺叫回家里,让他去问问。不一会,消息得到了应证,五千元出售。我当时身上正拿着钱,便找中人在我家里写下了房契,没有印泥,中人手印处用“X”,这也是古时候农村房契、地契中常常能够见到的表达方式,大抵与画押的作用相类似。
看着齐齐整整的一排窑洞,最高兴自然是母亲。曾经有好多次,她拄着拐杖在三十多米宽的老屋前走来走去,还不时地摇头叹息。其实当时我们兄弟都出门在外,很少回家居住,她曾问我买下窑洞要干啥,我告她“买下为你高兴,买下将来做事宴宽敞!”是啊,完整而残缺的老屋陪伴她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历经沧桑世事而终于完璧归赵般地呈现在她的面前,她能不高兴吗?再后来,外出许久的兄长回来后,喜欢吃苦劳累的他张罗着新修了大门,原先的土院墙也换成了砖墙,屋顶和院子都铺了砖,让母亲在宽敞漂亮的老屋内外安度着幸福的晚年。
不觉之中,硬朗而睿智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但老屋犹在,这可真应了她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物牢人不牢。”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心里,只要老屋在,家就在,母亲也就在。
又是一年中元节
七月十五中元节,留给我许多有趣的民俗记忆。捏面人、上坟祭祖、听喜鹊搭七彩鹊桥的故事、探究葡萄架下牛郎织女互诉衷肠等等,这些渐渐淡忘的稀奇往事曾经点燃过儿时探究未知的梦想,也带来对农耕文明发展演变兴衰的淡淡忧思。
听老辈人讲,捏面人相传起源于元代,原本是为了传递“杀鞑子”的消息。由于事情败露,手拿面人送信的人被官府追杀,后人为了纪念起事的乡民,便有了每年七月十五家家户户捏面人的习俗。这是一件极其神圣和庄重的事。白面要用当年新麦子来磨,而且必须颗粒饱满质量上乘,被雨水淋湿后发过芽的麦子是绝对上不了台面的。准备上石磨的前半天,用清水将麦子洗上两三遍,淘成干湿正好的成色,时间实在紧张时要用干净的白粗布擦掉多余的水分,摊开在簸箩里晾晒均匀。用石磨磨小麦,通常得循环五六个来回,一个来回叫做“一遍”,而且越到后面,由于剩下的大都是麸皮,面的颜色开始发黄,质地也就不如前两遍好。捏面人使用的面,只能取前两遍磨下的,洁白细腻光滑如丝,喷鼻的麦香味。即使在特别困难的时期,清明节捏燕子都可用高粱面替代,但捏面人必须就是这样的讲究,足见人们对这一民俗的重视与虔诚。中元节前两三天,女人们便要取来当地盛产的招贤和面瓷盆开始发面。发面要观察天气的变化,如果是大热的天,需放置到太阳底下晒个把时辰,然后用棉衣包裹好置于阴凉处,取石头将盆盖压结实,曾发生过不少次面被猫或老鼠偷吃的事;如遇阴雨或气温较低,就得将面盆置于灶台后面,靠柴火的余热加快发酵进度,但切记温度要掌握适当,温度太高,会把面“烧死”,不仅会影响整盆面的发酵质量,加入食用碱面后怎么也膨胀不起来,蒸出来的是“死面人人”,不仅品相不好看,而且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捏面人是极考验女人们的面艺技术的。面人有“大人人”和“小人人”之分,“大人人”约有十四五公分大小,“小人人”也就七八公分长短。这些大大小小的面人人节后是要送人的,送长辈或者重要的亲戚,需要“大人人”,一般场景或分给自家孩子选用“小人人”。普通的面人捏出五官、四肢,用黑糜子点上眼睛即可,如果捏得是女性,还得用小剪刀在头上剪出几道小辫子,手艺特讲究的面人身上或附有龙凤,或长有衣物,雍容华贵,出锅后再经炭火一烤,金光灿灿,活脱脱一件件艺术精品,后来在一些面塑展上见到过许多工艺繁杂,水平极高的艺术品,但上火烤过的少而又少,总也找不到那种香干脆的感觉。对于新媳妇,七月十五捏面人也是过门后的一大考验,那几天,有人专门去看手艺好巧不巧,如果手拙捏不成或捏得丑,会认为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这时候,婆婆怕家丑外扬,天不亮就起床代劳,待串门的人们赶到后,面人早已蒸好,甚至烤好。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面子上都能过得去,博一个皆大欢喜。
捏完了面人,还得留下些许的面,中元节有祭祀先人的习惯,家家户户都得捏上三个“圪蛋蛋”,形状酷似现在商超出售的圆馒头,只是个头稍微小些。白面金贵的年月,为了让“圪蛋蛋”气派些,还在中间包进去一个或半个红枣。吕梁山上上坟祭祀一年中有三次,但与清明节扫墓、冬至日送寒衣不同,中元节的祭祀以送果子、桃子、西甜瓜等瓜果蔬菜为主,外加这新麦子面蒸成的“圪蛋蛋”,让先人们尝尝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没的乡民们除却向神灵祈祷与倾诉,恐怕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寄托向往的办法,只能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宗教色彩的精神寄托与崇拜。中元时节时北方已经进入连阴雨季,地里的庄稼接近成熟,齐腰高的糜子、谷子和盖过头顶的高粱、玉米等大杆作物倘若在下雨天,会给祭祀者带来诸多不不便,而且也无形中会损坏庄稼,大集体时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至今常常为当年雨天祭祖踩踏折无数的糜子谷子而深深的懊悔。土地承包经营后,聪明朴实的庄稼人想出了妙招,大凡有坟茔的田间,大多种植土豆、红薯、豆类等低秸秆庄稼,实在腾挪不开,就采用间作的办法,用低秸秆庄稼留条道,既不影响后人的生计,也为祭祀先人让开了一条长长的道。
其实作为孩子们,中元节里更多的是期盼是总想着去兑现那些神奇的传说。七夕开始,大山里漫山遍野叽叽喳喳飞动的喜鹊便不见了踪影,母亲说他们是上天给牛郎织女搭鹊桥桥去了,得过完七月十五才能回来。几天里,门前那颗扎有雀巢的老槐树上来下去不知要爬多少次,想看是不是也在卧蛋,可真的就是不见那对花喜鹊的影子,即使到了七月十五夜里,还是没有。也怪,七月十六大清早,天还不大亮,屋外便又传来她们欢天喜地的叫声。更奇怪的是,此时的喜鹊个个身上脏兮兮的,羽毛也乱七八糟,倒彷佛真是去那儿受了一回苦,遭了一回罪。那时,我常常在想,天河看来也不遥远远,要不喜鹊半个晚上怎么可以飞得回来呢?更为神奇的是,听村里有位先生讲,七月十五深夜,当星星月亮布满天空,用驴粪蛋蛋塞进耳朵后爬到葡萄架下,可以听到牛郎织女相互哭诉的声音。那时恰好刚刚看过电影《牛郎织女》,真就上了这么一回当,结果不仅什么也没有听到,反倒搞了一脑袋驴粪的臭味,沾了一身的污泥,遭了母球一顿的骂。后来想起,那时是多么的童真与无知,但那一种懵懵懂懂的经历,即使在许多年后看起来即使真有点傻,那也是傻得可笑。那种不怕吃亏,傻呵呵地探究真谛的童趣何尝不是一种日渐缺失的人生态度呢?
又是一年中元节,我照例要回趟老家。这些年,尽管超市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但我用的两种水果却常常买不到。一种是甜瓜,一种是小果子。前者因为季节性原因,市场上早已下架,但在儿时,这个时节正是山地甜瓜成熟的时期;而后者因为是生长在山里的一种小众水果,果树寿命又不长,虽说正是上市时节,但很多年没有碰得到。好在今天早晨在市场门口一老农处又见到它的身影,虽说离中元节上有些时日,但还是买了几个放在了冰箱,好到时也上远在地下的母亲尝尝她的生气前的最爱。早两年村里的嫂子还保留了母亲的传统,给孩子们捏过人人,也蒸过“圪蛋蛋”,但因孩子们不再喜欢就放弃了,加之麦子因为气候和产量的原因早已退出村里的种植谱系,没有了新麦子,整个村里这些年便很少有人捏人人,“圪蛋蛋”也渐渐的被蛋糕糕点取代,传承多年的中元节风俗渐次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年那架古老葡萄早已不见了往日的踪迹,早早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去干我小时候的傻事,而那些忙碌的喜鹊,为了那个凄美的故事,想必还依旧奔跑的往返天河的路上。
二月二龙抬头
夜幕中散步,忽听得街边理发店发出了争吵声,循着涌动的人流,原来是顾客与老板为加价的事。顾客持会员卡,老板非让再加价五块钱,理由是快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了,理发者太多。其实商家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司空见惯了。对于洗车店或理发店里重大节日不能用卡或卡外加价的情况,久居城市里的人谁没有遇到过几次?最终在商家的坚持下,钱还是照付,毕竟彼时头发已经理到了一半。
在不停的忙忙碌碌中,不觉已过完了正月。在儿时的记忆里,二月二是有不少礼数和讲究的。孩子们还在被窝的时候,母亲便早早的起来,将干透了的“枣山”百一块放到枕头边。按照习俗,未成年的孩子这天睁眼后第一件事就是“咬蝇子”,现在想起来,那个坚硬的程度实在是不好啃,但一来毕竟属于白面馍,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二来据说只要二月二早晨咬过“蝇子”,一年里就不会受苍蝇蚊子的盯咬,究竟起多大作用,想必没有人去深究,事实上生活再山里的孩子,一年中是免不了受几次蝇虫之苦的,但一些风俗习惯就是在这种将信将疑、年复一年的美好愿景中慢慢传承下来的。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蒸“枣山”,将发好的白面捏成三五个如意状的小卷卷,每个小卷卷都夹上红枣,再捏头部和腿部,头部像一个官帽子,中间也夹着红枣,两条腿的胯部也都夹有红枣,然后在案板上将捏好的部分按头腹腿部黏在一起,用菜刀将其送到锅里蒸,十多分钟出锅后立起来,活脱脱一座用白面和红枣堆砌而成的小山。大年初一早上,“枣山”要在灶台后面、屋门上边各放一个,此后白天放、晚上拿,生怕被猫或老鼠叼走,直到过完正月十五,干透了的“枣山”才被收了起来。
早饭须吃饺子,叫“捏龙口”。听老人们讲,龙抬头,把龙口捏住,为的是不让龙的口空着,既有对龙的崇敬,早春二月,见龙在田,让吃饱喝足后的龙腾飞九天,普降甘霖,又有对龙的畏惧,让其吃饱后就不会吞噬其它动物,图的是六畜兴旺,平平安安。馅是胡萝卜榨成碎末状,拌上咸盐花椒红皮葱,如过能再上点白豆腐,那就是非常高的奢望了。在白面奇缺的年代,二月二的饺子多用高粱面,由于粘性差,通常要放点榆皮面,这样面才能和捏到一块。榆皮面就是将榆树的皮或榆树根部的皮趁湿剥下,晒干后用斧头炸成小块,然后用碾子或石墨磨成面,是吃高粱面的必须之物。
为了全家在午后能吃上一顿二月二的煮豆子,女人们在早两天就忙碌着开始准备食材,自家凑不齐的要提前与邻居家调换。那时没有高压锅一类的灶具,这些食材事先浸泡两天才可以用炭火煮透。煮豆子的食材通常有红豆、豇豆、豌豆、扁豆、小麦、玉米等五六种,寓意五谷丰登。最具特色的是上年收获的小蔓菁,指头般大小,秋天里洗干净后用针线穿起来挂在门外的墙壁上,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后略显干瘪,也得与豆子们一样提前泡上。别小看这个小蔓菁,它可是二月二里一碗煮豆子的魂。有了它,煮熟的豆子就没有了生硬气和寡淡味,才能吃出那种淡雅柔和间透出的清香味。
二月二前前后后最忙碌的当选村里的剃头理发师傅。老辈人用的是剃头刀,就像影视剧中演得那种,背部厚厚的,刀刃薄薄的,外长一个短把,可以拉得开合得住。剃头时将头发用碱水洗干净,然后用刀慢慢的刮。如果剃光头倒也省事,从上而下几个来回就差不多了,难得是剃偏分头、小平头一类,没有个把小时是完成不了的,而村里剃头刀就两三把,会使用的也就三两人,从早到晚都完不成,后来干脆从初一开始连剃三天。随着推剪走入乡村,再后来削发器的兴起,比用剃头刀的效率提高了几倍,理出的头发也漂亮了许多,年轻人都不再用剃头刀,但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喜欢它,说刮得舒服。但不管是使用什么工具,村里的剃头理发师傅都是义务的,即使大家的日子是那样的清苦,但剃个头理个发全然没有任何费用,当然也就没有城市里街头边为了涨不涨价的争吵。有时闭眼睛想想儿时人们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在欢声笑语中去剃头理发“龙抬头”的情景,不禁暗暗摇头发笑,那是一副多么温馨和谐却又不可能再回得去的田园美景啊!
2023国庆特刊征稿启事
请添加办公微信13681238889,将您的20首诗词(新诗共200行内)或3篇散文(共6000字内)、简介、照片传来。传前请仔细校对好您的简历和文字,确保准确无误。10月31日截止,依次在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重磅推出。
联系电话:010-68688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