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春特刊|中国作家 罗挺表 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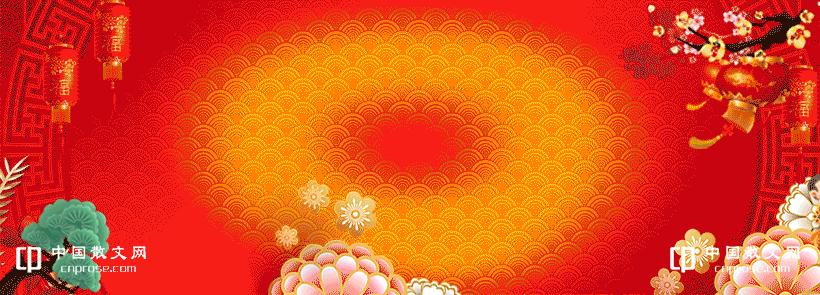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
—— 罗挺表 作品展 ——
作家简历
★
罗挺表 笔名莲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律师办公室律师。已出版作品集《真实与虚构》(广播电视出版社)、长篇小说《冷眼》(作家出版社)、散文集《坚强的玉米》(团结出版社)、长篇小说《平安工地》(天津人民出版社);散文集《痕迹》即将出版。
仰望拱桥
是桥,就要被人踩在脚下。而我,甘心仰望拱桥,以虔诚的姿势仰望,仰望人类文明的星空。因为,那是建设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桥梁技术的一个又一个高度。
我仰望赵州桥。这是中国拱桥的第一个世界高度。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建于公元595-605年,是一座石拱桥,桥体全部用石料建成,桥长50.82米,跨径37.02米,一孔跨过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洨河,以最早之敞肩石拱桥载入世界桥梁史册。此桥颇多民间传说,根据《安济桥铭》所记“赵州蛟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方知并非神仙所为,乃凡人建造,此凡人即李春。赵州桥因李春而诞生,李春因赵州桥而扬名。李春并没有把名字刻入石头,却与赵州桥合二为一,一起走过唐宋元明清和民国,走到今天,历经14个一百年而不磨灭。我不知道赵州桥是怎么设计的,设计图画在什么材质上,也不知道如何建造,但我并不感到羞耻,因为距离李春不过120年的唐朝人张嘉贞早已感叹:“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这就给赵州桥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我无法破解这个谜,但我知道赵州桥不仅已经成为燕赵大地的一部分,也永久地停留在唐诗宋词里,出现在当今的语文课本里,回响在少年儿童天籁一般的朗读声里。我也愿意用沧桑的嗓音反复呼唤它的名字,吟咏描写它的诗句“初月出云,长虹引涧”,想象走过它身上的脚板、草鞋和马蹄,以及与它一起出现在清波倒影里的明眸长发。
我不禁想起现代诗人臧克家的名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李春就是一个“死了但又活着”的人,活在过去,活在现在,活在未来。也许,哪一天赵州桥不存在了,可李春依然活着。肉体不在,精神长存。在我国,有一个李春奖,系国家公路建设最高工程质量奖。这是对李春的纪念,也是对公路建设者的鞭策和鼓励。
我仰望合江长江一桥。这是中国拱桥的另一个世界高度。该桥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境内,全长841m,主跨530米,一步跨过长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径的钢管混凝土拱桥,在世界拱桥建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极力推荐该桥使用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皆连自豪地说:“能拿的奖项,这座桥基本拿完了。”可不是吗?只要在“百度”上搜索,便可查阅合江长江一桥所获得的荣誉: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四川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四川省优质工程金奖。以上是国内奖项,国际奖项是由国际桥梁大会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
据悉,钢管混凝土拱桥由于刚度大、耐久性好、造价低、施工快捷,因而在中国大量采用。但由于施工难度大、风险高,导致其跨径增长困难且缓慢。从2005年的460米到2013年的530米,8年时间仅增长了15%,而斜拉桥由2005年的648米,到2008年的1088米,仅3年就增长了68%,可见钢管拱跨径增大以后带来的问题非常多、解决难度相当大。尤其是由400米突破500米以后,原来的设计方法、施工技术、组合材料、吊杆拉索等都存在各种瓶颈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系统的深入研究。郑皆连院士带领研究团队经过20余年研究,研发出500米级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成套施工技术,包括大跨钢管混凝土拱桥管内混凝土真空辅助灌注工艺和新材料、钢管混凝土桥高精度、低成本施工成套技术及装备。该技术,201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技术主要完成人名单里,我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郑皆连、韩玉、秦大燕。其中,韩玉是合江长江一桥的项目经理,秦大燕是合江长江一桥的项目总工程师。这让我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我不敢说他们就是当代的李春,但至少他们已经把李春精神发扬光大。
我仰望在建的平南三桥。这是中国拱桥的又一个世界高度。该桥位于广西平南县境内,跨越浔江,全长1035米,主桥跨径575米;建成后,将超越合江长江一桥,成为世界最大跨径的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德尔菲神庙有一个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由此可见,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是人类共识,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大桥项目部秉持大型化、标准化、装配化、信息化理念,在施工安装过程中采用就近拼装、方便吊装原则,将塔架分解成大型构件,在平地进行流程化拼装,由塔吊配合完成安装,极大减少高空作业工作面,有效控制施工风险。同时,利用信息化建设,通过监控指挥中心、测量机器人、北斗GNSS自动化监测系统以及在塔吊控制室设置智能风速监控等方式,进行综合智能监测,确保监测数据零误差,确保大桥建设安全和质量。为保证大桥顺利建成,广西路桥集团一个副总经理亲自担任项目经理,一个副总工程师担任项目总工程师。为一个工程配备如此高级别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程师,在广西路桥集团的建设史上尚属首次。同时,在施工现场,人们也经常看到郑皆连院士忙碌的身影。可以说,平南三桥的建设,倾注了无数人的心血,更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让无数人把视线从世界各地移动到中国,移动到广西,移动到平南。更让人骄傲的是,世界桥梁大会将于2019年12月在平南三桥施工现场隆重召开。
平南三桥,是一座高科技的钢管混凝土拱桥,它正在中国南方的浔江流域慢慢崛起,向中原大地上的赵州桥弯腰鞠躬,向拱桥的先祖报告成长的喜讯。再过几个月,它的名字即将传遍全世界。
我仰望未来出现的大跨径拱桥,期待下一个世界高度。但不管技术含量多高,我希望它身上仍然有赵州桥的影子,保留着拱桥的优良传统。已保持1400多年生命力的赵州桥告诉人类一个道理:被践踏的未必是低贱的,反而因被践踏而显得尊贵。
(2019.11.1)
青海印象
黄河水
关于黄河水,被两句话误导了许多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李白醉酒之后吟诵的,虽豪迈,却不是实情。酒话不能当真,当真就上当了。李白这样表达,无非两个原因,一是他喜欢说大话,二是他没有到过青海。
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网》介绍,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
看地图,确实如此。等到了青海,亲眼所见,更加确信无疑。
曾经在山东、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看过黄河,也在电视上看过陕西、山西的黄河,无不河水浑浊。所以,我相信了那句俗语“跳到黄河——洗不清”,黄河水并不能“清清濯我缨”。
可青海贵德县的黄河水给了我截然不同的印象。河水清澈,浪花飞白,不仅可以濯我足,还可以濯我心。
杜甫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陆游也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同是诗人,杜陆两人说得很靠谱。
钱其琛题词:天下黄河贵德清。
这是定论,还了黄河一个清白。
2018年10月2日,我站在黄河边,离河水只有几公分。这天,不知何故,河水上涨,但河道里的水仍清冽,黄河少女雕像的基座被洪水淹没了,仿佛少女站在水中一样,半裸而大方,毫无扭捏之态。
我真想脱掉鞋袜,去感受黄河水的冷暖。
七彩峰丛
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最美的景点是七彩峰丛。
峰已是奇峰,陡峭,光秃,不允许树和草站在它的头顶上流眼泪,也不需要树和草为它遮风挡雨。它就昂首站在天与地之间,像大地伸出的一个瘦骨嶙峋的手指,去触摸天上的星星。
每一个山峰,轮廓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大写的人字。靠近一看,才看出它们的不同。有的山峰,腰上挂着大大小小的葫芦;有的山峰,排列着各种猛兽,或跑动,或站立;有的山峰,雕刻着飞檐翘角的宫殿。
只有站在远处看,它们才是一样的,像一群身披袈裟的僧人,默立祈祷。
一件件袈裟,五颜六色,却显得陈旧,不反光,不耀眼,朴实而厚重。
古代祭祀,用五色土,要从各地进贡,多麻烦呀。不如来此地,捧一抔回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想起云南的红土地,艳则艳矣,略显单调些。
七彩,是它们的本色,不需要其他东西来点缀。
或许这才是泥土的本来面目。
枸杞子
离开水泥路面,往山里走去,还会有不少收获。最让我惊喜的,是看到了一棵枸杞树。
我相信它是一棵老树,虽然只有一米多高,但树皮苍老,灰黑皲裂,如铁铸一般。树枝短小,有少许叶子。叶子绿中偏黄,样子孤傲。看过一部纪录片,说是青藏高原上生长一种植物,一年只长一厘米。我不知道这棵枸杞树是否也生长得这么缓慢,但我知道它生长得不容易。它身上的刺,尖锐而坚硬,保护着它。
南宁的菜市,经常有鲜嫩的枸杞卖,连枝带叶,不贵,5元一把。
吃叶子的枸杞,滥生,廉价。
眼前的这棵枸杞,是无价的。
阳光可以拿走它的水分,风沙可以在它身上留下伤痕,打落它的果实,但无法折断它的树枝,更无法拔出它的根须。
它的根有多深呢,无法知道。
幸存的果实,个子当然不大,只有火柴头那么一点点,但颜色鲜红,像红宝石挂在树枝上。
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颗,直接往嘴里送。轻轻咬破,甜得令人惊讶。
南宁的枸杞不长果。最有名的枸杞在宁夏。我曾在宁夏的枸杞园,摘过枸杞子。论个头,枸杞园里的要大,论味道,则未必了。
况且,想多吃也没有。
我也不敢多吃。留下一些做种吧,愿明年春天长出几棵苗,活下来,给老树做伴。
原子城
这里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神秘得无法在地图上找到。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国家有原子弹,但不知道原子弹是在这里试验成功的,更不知道自己也能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
一切都没有军事禁区的样子了。
这里恢复成牧区已有20多年。白云下,白塔旁,经幡猎猎飘动。羊群悠然地啃着草叶,或躺在地上,无聊地打发时间。游人正相反,忙着选角度拍照、录像,在阳光下露出灿烂的笑容。
草地上,有三块大石头,一块刻着“原子城”,一块刻着“金银滩”,这两块凑在一起,告诉人们原子城就坐落在金银滩上。另一块刻着“在那遥远的地方”。这应该是歌名,曾经很流行的歌曲。
莫朵轻声地哼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我们站在一个山坡上,坡底有河。脚底的草,密而短。不知是不是汪曾祺先生写过的灰背青。
远处是人们聚集生活的地方,高高的烟囱冒着白烟,楼群朴素安静。
两个牧民骑着马,从草原深处慢慢地走出来。看不出男女,他们是夫妻,还是兄弟?
他们是原子城的后裔吗?
青海湖
青海湖太大了,我们只停留在一个旅游点上。
这是大海撤退时留在高原上的儿子。
它有与大海一样的血液和脾气。
一呼一吸,与天地同步。
它永远没有安静的时候,总是吵闹着,总想爬上岸,去抓一把雪。雪害怕了,躲在高高的山顶上,远远地向着湖水喊:“来呀,来抓我呀。”
青海湖里有鲸鱼吗?有鲨鱼吗?
海鸥嗷嗷叫,没人知道它们说什么。但人们乐意听它们叫,喜欢看它们飞翔。那些扔出去的面包屑是人们送给海鸥的礼物。
海鸥是飞往青海湖与太平洋或印度洋之间的信使吗?它们的叫声,也许只有青海湖听得懂。
亿万年来,青海湖瘦了吗?
坐在湖边的椅子上,听着海浪咆哮,我没给青海湖任何回应。什么也不留给它,连剥下的果皮,也装在塑料袋里,带走。
青海湖知道我来过吗?喔,它不知道,或者它根本不在意。多一个人,它并不感到热闹;少一个人,它也并不感到寂寞。我们的脚步都太轻,青海湖不会知觉。
……
想多了,回去吧。带着录像和照片,回去吧。
若干年以后,打开录像和照片,知道自己来过青海湖,这就足够。
茶卡盐湖
茶卡盐湖出名,不在于它生产的盐巴,而在于它的自然景观。
一个盐场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奇怪。盐场的经营者,真是有商业头脑。
盐场是景区的一部分。看工人晒盐,跟看工人酿酒一样有趣。
盐场的景色更漂亮。没有树,没有草,没有花,但有天上的蓝天和白云,夜晚还有星星和月亮。
湖里没有波浪,平静得像镜子。天空有多干净,它就有多干净。
湖里肯定是没有鱼的。鱼长出了脚,走在湖堤上,穿着衣服,戴着帽子。比在湖里的时候,更密集,更喧嚣。
离开大海太久,茶卡盐湖已经失去了本性。
通往湖里的路,就是用盐巴铺就的,路面上撒满盐粒或是盐末,走一步就留下一个脚窝。
或许茶卡盐湖已经死了,是游人给它带来了新的生命。
我突然想,如果哪一天青海湖也变成了盐湖,世界将会怎样呢?
(2018.10.29)
风使劲吹
又是一个多云的清晨,天衣像一件缝满补丁的泛白黑棉袄。那些补丁,大小不同,形状和颜色各异,有的像丝绸,有的像棉布,有的像牛皮纸,随意地拼在一起,叠加在一起,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我站在港区一座废弃大楼的楼顶上,眺望四周,想寻找一丝光线,以印证天气预报所说的晴朗。可是,跌进我眼帘的依然是一团团密不透光的乌云。
乌云从何而来?用不着猜测,一部分答案就挂在眼前。在我的正前方,有一片厂房和一个庞大的烟囱群,那是一家造纸厂;顺着左肩看去,也是一片厂房和一个庞大的烟囱群,那是一家炼油厂;扭头向右边看去,也是一片厂房和一个庞大的烟囱群,那是一家火力发电厂。当然,每个方向不仅仅只有一片厂房和一个烟囱群,而是像崇山峻岭一样,远近高低各不同,我只是挑距离最近的来说。先从炼油厂说起吧。炼油厂的烟囱最休闲,像想戒烟的老烟民抽起的电子烟,冒出的烟呈白雾状,缓缓飘散,不急不慢。发电厂的烟囱最急躁,像烟瘾极大的老烟鬼,大口吸大口吐,吐出的烟颜色最深,射程最远;造纸厂的烟囱介于两者之间,喷出的烟灰白色,刚好把天空的蓝色完全遮住。
浪漫一点的,可以把那些烟囱想像成一支支画笔,正蘸满墨汁捺在天幕上创作。现实一点的,完全看出那是实实在在的环境污染。
我既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现实让我无法逃避,浪漫又让我在沮丧中得到安慰。
好在有风。那一阵又一阵的晨风,随海浪翻滚而来,提醒我一千米之外就是海面。但谁敢相信,此时此刻,我与大海只有一枪之遥。
我不禁张开双臂,摆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样的手势,祈祷迎面而来的晨风吹得更猛烈些,把黑云撕裂,让阳光现身。然而,祈祷没有生效,晨风像柔软的丝巾抽得我脸蛋生疼,却对棉被一般厚重的云层无能为力。
我伸出双手,想拉住海风,但海风像飞奔的野马,挣脱我的手指,疾驰而去。我多想拉住她,告诉她,使劲吹,把那些浓烟吹走,把纯净的空气还给海鸥,还给红树林,还给在此地工作生活的人们。
想起在此地工作生活的人,我无奈地低下头,却又看见了周边整排整排的空房子,看见了空房子紧闭的门窗,看见了空房子阳台边上疯长的野草。目光越过那些水泥建筑物,我看见了一所废弃的校园,看见了一根孤单的旗杆,看见了一个寂静的足球场。
从踏进港区的那天起,我就被告知,我置身于炼油厂的安全隐患区域内。
从那天起,我就生活在这片废墟当中。但我也发现,废墟里零星地生活着其他人。这些人,要么是炼油厂的维修工人,要么是跑长途的大车司机,要么是开小卖部的生意人,要么是像我们这样的路桥建设者。他们或者租了一间房,或者租了一层楼,甚至租了一栋楼,临时地生活着。说是临时,其实也生活了好多年。比如我们,也得在这里临时生活三年以上。龙门大桥建设工期40个月,作为前期筹备者,大桥尚未开工,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废弃的大楼里生活了一个多月。
被烟囱所包围,生活在废墟当中,我虽无意离开,却感到一种无以排遣的伤感。谁曾想到,繁忙的码头边上竟有如此荒凉的景象。
这也许就是发展中的阵痛吧?
眼前的这些乌云,想必也曾停留在伦敦等城市的上空。是什么把乌云吹走了,还他们一片碧空?
也许是风。那好吧,让我再次祈祷:
风,请使劲吹,让那些远在异地的决策者也能呼吸到这里新鲜而又污浊的空气。
风,请使劲吹,吹走这里令人心酸的贫困之霾。
(202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