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心灵双重“东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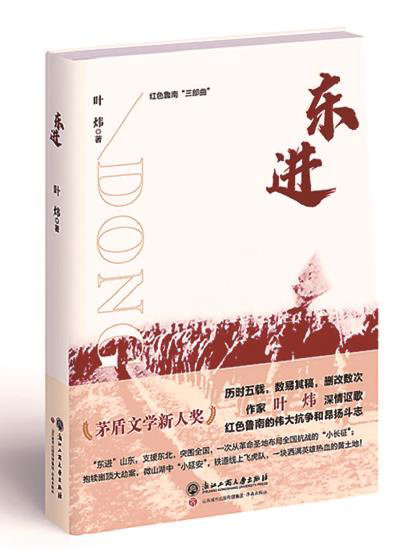
《东进》叶炜/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东进》是叶炜创作的第六个“三部曲”——“红色鲁南三部曲”的首部。小说取材于抗战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真实历史事件,以八路军东进山东展开的重要战斗和关键节点为主要线索,在礼赞英雄的同时还原了鲁南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历史风貌。
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东进》最初也是一部电视剧本。在叶炜的专访中,他谈及此:“作为电视剧本的《东进》最初只有一条叙事主线,根据八路军‘东进’山东的步伐,以所开展的战斗和取得的胜利为主要背景铺陈开来。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小说创作则稀释了电视剧本中过于浓重的历史写实,加入了一条副线——东进山东的八路军对抱犊崮土匪的斗争和团结,最后将其改造为抗日的重要力量。”
从小说文本来看,剧本改编后,剿匪的叙述线索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成为了另一条主线,形成了文本双线叙事的整体结构。作为战争题材小说,《东进》在战场描写上所用笔墨不多,反而将目光转向了战场之后的人。双线叙事为故事提供了两种视角,一种是敢于斗争、甘于奉献、高瞻远瞩、一心为民的革命领导人物的官方视角,一种是亦正亦邪、智勇双全、为家勇担责任。为国甘洒热血的革命人物的民间视角。两种视角交织出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国民党、地方山匪三方互相角力的复杂形势。面对复杂的形势,东进先遣队要面临的是双重东进:不仅是战略上的“东进”,更是思想上的“东进”。
故事从民间视角讲起。小说一开篇就把运西古城里的刘赵两个大户人家的命运牵连在一起。刘玉胜先是与赵当归斗鹌鹑游戏大胜,后媒人将赵家小姐赵灵芝说与他,未料成婚之日却遭山匪刘黑棋抢亲,老刘家三个儿媳悉数被掠往抱犊崮。救人,成为了副线叙事的主要动力,也为刘玉胜投靠八路军做了情理上的铺垫。在这一章的书写中,刘家大院的描写颇值得注意:“三进青砖黛瓦的大四合院”“门框上贴春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浸染。在整个故事中,儒家思想的体现是多层面的,刘家重孝,赵家亲仁,这也是刘赵两家成为可团结力量的重要思想基础。
革命领导人物谷四喜第二章才出场,作为先遣队最高领导者的他一出场却先是丈夫、父亲。这样的叙事安排是颇有意味的。妻子秦林战时的生产牵动他作为丈夫的心,孩子无法带着身边,只能寄放在老乡家里,让作为父亲的他不舍。小说有意将英雄还原为真实的人,给故事增添人情人性之美,也为后文谷四喜面对自己的同志所犯错误迟迟未能做出决断,反而造成一定的损失埋下伏笔。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谷四喜为孩子取名为“东进”,便在一开篇定下了战斗必将胜利、新生必有希望的基调。
作为八路军先遣队的战略制定者,政委谷四喜面临的是双重东进的艰巨任务。在战略的“东进”上,谷四喜与师长陈尔东、团长杨勇以及后来被任命为铁道游击队队长刘玉胜等人的配合下顺利开展,他运筹帷幄,凭借智慧几次化险为夷,打出漂亮的剿匪战、抗日战。
在对内思想改造的“东进”上,难度显然更大。小说开篇的“把鹌鹑”即隐喻了谷四喜的思想改造智慧:“每天把上几个时辰,以增进彼此的感情,鹌鹑会慢慢通了人性,渐渐与主人心意相同,情同手足……把鹌鹑如此,把人亦如是。”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智慧,先遣队完成了对外的感化与团结。
我们不难发现,在思想的“东进”上,作家有意从两方面展开叙述。一方面是对外部的感化团结,一方面是对内部的批评整改。作家比较正面地回应了历史,没有将其减化、弱化,反而有意强化。谷四喜的思考亦是作家对于革命历史曲折性的思考。
小说《东进》的创作,对于作家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历史回溯,也不仅仅是从剧本到小说的文学实践,而是一次心灵的返乡之旅。叶炜是山东枣庄人,以鲁南地区为背景的《东进》充满了地方的风景、风俗、风情。从开篇的喜宴的菜品到刘老爷子的丧礼的仪式,从刘玉胜“把鹌鹑”的细节描摹到赵一味采药挖参的一一铺陈,从抱犊崮之险到鲁南村庄的四季之景,无不透露着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正是有了这份热爱,这个基于历史史实的故事框架才有了血肉与温度。我们亦能从中感受到作家对于那一方土地的敬畏与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