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铭|金龙贺岁·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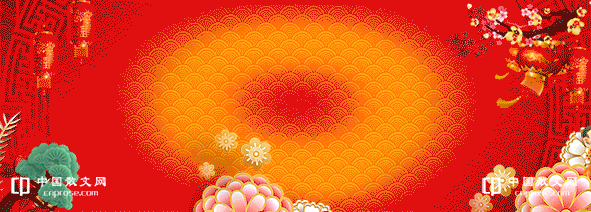
林毓铭|金龙贺岁
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作家简历
★
林毓铭 出生于195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曾务农6年半并当过1年建筑工人,后从事大学教学工作近40年,担任过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导师。退休前发表学术论文27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合著、教材、译著、工具书等42部,主持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退休后退出学术圈跨界走向文坛,2019年至2023年连续出版文学作品4部:《阅尽浮华:灵魂在诗歌里流浪》《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放下后一路潇洒前行》《情系大千世界》等共一百余万字。传记文学《岁月留痕》一书也在2023年底完成。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受聘中国散文网专栏作家与高级作家。
2018年时年62岁,我从熟悉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领域另辟蹊径,冒昧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2019年到2023年,连续出版了4部文学著作,并极其艰难地完成了第5部传记文学作品的创作。5部拙作中的5篇自序,披露了我跨界走上文学之路的心路历程。
《第三只眼睛看世界》自序
世界在变,遍地狼烟,但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松果体是人体的第三只眼睛,如果真有第三只眼睛,我想那是一只独具慧眼的眼睛、有一定的穿透力和杀伤力的眼睛。新纪元思想认为第三只眼睛象征着开悟或心像的深层灵性启发,也代表着意义深远的心理现象。
可惜我的思想还不够睿智,还不具有天高地远的气魄和叱咤风云的决心。至今还算稚嫩的第三只眼睛,无法预知未来,还要增强必需的战略定力,静心凝气、增强人生智慧。在风云变幻的人生世界,让眼光锐利起来,每天去发现新的太阳,让世界在我的眼里每天都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新画卷。
这是2021年我在繁忙的学术研究与教学之外完成的第二部文学类书稿。第一部是诗集,收集了自己在2018年至2019年化了8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斗胆写下的226首自由诗,《阅尽浮华:灵魂在诗情里流浪》作为处女作,2019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部文稿《第3只眼睛看世界》包括诗歌、杂文、散文、随笔、人物传记、纪实文学等文体。在正式退休之后,不用再做什么课题项目,我想我会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以飨读者。
论文是用来进行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文学体裁一般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种。自己对学术论文的驾驭心里有些数,在国家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自诩为一个较成功的学者,而对文学基础的掌握则还处于ABC阶段。第二部文稿是一个大杂烩,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灵魂与血肉,哪怕是晓风残月,也愿意融于每一个跳跃的文字中。“言乎志者也,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非慷慨悲壮之人,不可为之”。
文字的优劣不在形式而在于内容,我不缺乏生活,欠缺的是艺术的处理,有时佶屈聱牙,词不达意,需要以后经常性的修炼,提高诗情的程度,不要炫奇对文字的装饰,而是要以巧妙的笔触将情绪刻画出来,不要削足适履,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艺术道路,做到娓娓道来、从容自然,从文中折射出艺术的素养。
写写诗歌杂文是我未来对退休生活的消遣,从精神上来取悦自己,通过思想来观察自己灵魂的变迁,用一面自鉴的镜子,通过潜意识的释放,不要让自己迷失或沉湮在梦幻之中与老年人的亚文化之中,做到对自己的思想和情形的流露操纵有度、游刃有余。
梵乐希在《达尔西方法导论》中说:诗并不是灵感的产物,却是一种勉力、练习和游戏的结果,诗不但不可以放纵情绪,却反而应该遏制而阻拦它。我认为这就是诗的哲学,我们不可以作空虚的诗人,不要否认灵感一现,思想是没有风格的,需要一颗淳朴的心灵,仔细而小心地推敲出来。一是要用最抒情的诗句表出迷人的诗境、荡气回肠;二是要表现出作者最深邃的思想情感、温暖众生。
除了诗歌之外,其他的文学体裁都不是虚饰的,来自于自然的流露,它源于生活的记录写实,它沉淀了历史的岁月和人生走过的每一道痕迹。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有所感悟,文如其人,在柔弱的文字中,可能将自己暴露得体无完肤,但我仍是高傲的,维护了自己终生的尊严,哪怕成为一个苦涩的尘世蠢物。
对我而言,文学之旅确实有些萧索和突然,但我的思想并不荒芜,我有我的盎然韵致与举重若轻,在尘埃与高尚之间,情动而辞发,我愿做一个性情中人。趁还没有思想糊涂之前,在朴素的日子里尽早在理性与现实的云朵中做出世俗与审美的行走,将人格魅力穿梭徘徊于散文的最高境界,让其徜徉于灵魂的孕育、诗学的浸染和思辨的潜流。
行将遗忘的历史、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家国情怀,用自己的双手与还好用的大脑去挖掘出来,重新解剖拷问自己的灵魂,作一番冰肌雪肠的反省,昭告自己的良心与审美的个性。这里有土地的悲歌与人生的写意、也有乡土文化与人文视野的游走,在体察命运的光彩与沉重之时,我还是乐于钟鼓琴瑟、暖于布帛。
我的骨子里是一个浪漫的人,而岁月的沧桑让我的天性慢慢地蜕变的有些孤傲,在权势面前我一辈子未曾低下头颅,也不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左右逢源。在体制内沉耽于踽踽独行,侥幸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功。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活过了顺耳之年,我潜伏的天性渐渐复苏,收集了近3年在朋友圈公开与非公开的小作品,整理成两部厚厚的文稿公开出版。同事和朋友们有些诧异,说我是被学术耽误了的文学青年,这种褒奖是一种温暖的感动,假如命运可以重来,我愿意验证。
目前我还在返聘的工作状态中,忙着上课、做项目、出学术专著,工作之余我另辟蹊径在诗文的创作道路上孤独地行走,在非文艺圈的氛围内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可能还存有“不务正业”之嫌。可是认定的路我要坚持下去,尽管没有文学成长的平台,我仍然愿做一个在钢丝上行走自律和笃定的独行侠。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我做好了坠入深渊粉身碎骨的准备。
《放下后一路潇洒前行》自序
2018年,当灵魂拷问我,还剩下不到3年的工作时光,就要结束生命的第二周期的时候,你准备干什么?我感到有些吃惊、也有些愕然。岁月无情,我常常看不见他人前行的脚步,对自己也熟视无睹。对体制内剩下的时光,我从来没有像过去那样,突然倍加珍惜起来。
可这3年的时光,顷刻间就烟消云散了。我在体制内残存的时光与时间赛跑,创造了这一辈子的高光时刻,授课约430课时,4部学术专著在人民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完成了主持2项国家社科项目和2项教育部重大项目的结项工作。
2021年9月我退休了,时年65岁,有许多的不舍与惦念,也提前感觉到了一些世态炎凉,我没有选择再就业,也没有打算从此过上安逸的生活。虽然已是白发婆娑,但内心里还有一颗躁动的心灵,不甘于躺平,更不屑于从此将自己包裹起来,背叛自己躁动的灵魂。
出身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过的大多是朴素的日子,我们的思想早就被时代概念化、模式化了,在复杂的态势面前总是那么无意识甚至比后来人还要蒙昧。生活是流淌的,既然不甘于平庸,为何不在流淌的岁月中继续有所作为呢?我是50年代饱经沧桑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当体制内的历史沉寂到只剩下读秒时间的时候,才发现我的人生尚有太丰富的想象力与爆发的潜质。人是有惰性的,往往是在幸福的时刻。人生还是要享受更多的苦难,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柴静说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我认为要加上一个躁动的环境作背景,就像我们做小松鼠的实验一样,思变才是人们生活的本然。从生命的意义来说,当50年代出生的人将一步步走向世界末日的时候,思变并不一定是要改变命运,而是在于索取生命的潜能与价值。很多人在跳广场舞,何尝不是在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呢?他们在太多的历史沉疴中做过无畏的挣扎,现在的时光是他们生命旅程中最后一个驿站,积极老龄化也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我是一个思想比较独立的人,有一个健全和淡泊的人格,但生活的种种磨难让我与社会产生了一个隔离感,我一生都在尽力缩短这个差距,当穷尽我在体制内所有的时间时,才赫然发现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一个佛系老人,不受外界干扰,才真正有近3年的收获,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一路蹒跚而行,其实也是在用文字麻痹自己。
儿时曾经有过许多梦想,可这一切风卷残云般地被吹入了深渊。在命运的若干个时间节点上,历史曾给自己开了几个大大的玩笑。在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做梦人终归会有自己的舞台,不管是砥砺前行还是超弯道跨越式发展。
看来我倾向于后者,砥砺前行是以前的常态,跨越式发展才是在有限的生命形态中应有的选择。历史是需要沉淀的、往事是需要回味的,依靠简单流畅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用辛酸刻薄的文字陈述自己的一些感悟。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无病呻吟,对自己来说,却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对于流逝的光阴,有许多的遗憾、焦虑、悲伤与挫败,重拾自己,悟出了淡然,才懂得释然,用章回体写下自己的序章,告别从前的自己,只要心中还有星辰大海、眼中还有一泓清泉、爱山河的浪漫、珍惜人间烟火的凡俗,一切都可以将自己调整好为刚刚好的模样。
早已进入到低欲望的年龄,放下吧,一切都是浮云。柏拉图说:如果不幸福、如果不快乐,那就放手吧;如果舍不得、放不下,那就痛苦吧。孔子曰: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往后的日子,盼望与幸运不期而遇、期待与美好温暖相拥。用文字结束自己过去的同时,但愿在人生的冬季,不要再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岁月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了条条皱纹,再不要在灵魂上刻上道道伤痕。
少翻历史旧账,有梦就有未来,放下后一路潇洒前行,用莫言的话来说:每个平淡无奇的生命中都蕴藏着一座宝藏,只要肯挖掘,哪怕微乎其微的一丝优点的暗示,也会挖出令自己惊讶不已的宝藏。
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又花了8个月的业余时间撰稿,书中许多生命的故事,有他人的也有我自己的,人生中总会有许多漂泊的、不安的和流浪的灵魂,书中没有特定的重点和主题,可以开启大家对话的窗口。
放下啦,不仅仅只是站在高山上的一个吆喝,而是要从内心里真正产生共鸣,放下后才能一路前行。如普希金所言: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消逝,一切逝去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放下之前的所有,才会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我想下半辈子潇洒的人生莫过于如此。
本书部分内容在朋友圈展示过,得到一些朋友在文字上的指导和帮助,也有的朋友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奉献给了我作为插图,或者是转发一些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我分享,有的朋友还提供了一些写作素材,这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鞭策。《致敬:推动大手拉小手助学项目的清华博士们》一文由原清华大学博士、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祝哲副教授提供素材,我在订阅号助手平台展出后不到24小时,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巴普镇乃拖村9名儿童就得到了爱心人士的长期助学签约资助。事隔一个月,村委会开出了当月收入1200元的收款证明。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了文字与善良的力量。抗美援越老兵周春起团长,高兴地为我提供数十年前中国海军潜艇部队在越战扫雷时的战争素材,成文后转发给他当年的几百个战友广为传阅,让我特别感动。
过了顺耳之年,从学术论文的写作转型到文学创作,难度很大,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一些朋友问我,好好的退休日子不过,为什么还要将自己陷入一个苦逼的文学漩涡之中;同事不理解,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本可以继续努力,为什么要到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试图“沽名钓誉”。我真的大有一番“孤舟蓑笠翁,独钓赛江雪”的莫名之感。我始终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卑微的布衣小人,对权势没有欲望,对生活质量没有需求。有一些文学创作的念想,但远非文学之人,有时也感觉到十分地茫然无助。但愿文学慢慢地陪伴我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俯拾仰取、不虚此行。
《情系大千世界》自序
这是我倾尽全力、并启动了所有脑细胞撰写出来的第二部纯诗集,退休后忙于带娃和疫情所困,很少有机会去接近生活,找不到什么好题材,陷入了只有陋室、没有远方的䇹境中,中途曾多次想打退堂鼓。这时候我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诗人会出现阶段性的人生焦虑,这可能不仅仅是情感的原因,而是所处环境的患得患失。
我退休前为了学术而奋斗,跨越了四个专业,大半辈子都在负责新学科建设,算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学者,业绩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退休前两年自认为精力依旧旺盛,就毫不犹豫地走向了文学之路,这是儿时的一个梦想,也自认为这是自己生命中必须经历的一场游戏,我有无奈的伤感,也同样有创作激情。杨绛先生说:“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待你,都要好好珍视自己,对得起内心的那一抹骄傲。”
我的年龄已经到达山顶,何不来一场如法国作家福楼拜所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中山大学某教授在看了我的作品和作者简介后感慨地说道:当前教育的最大问题,文科生没有科学素养,理科生没有文学功底。新中国成立前培养的大师,大部分是能够最后将科学与艺术在山顶上会合的。听了这段话,我希望我是其中一个成功的登顶者。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都比较坎坷,小学毕业时我失学差不多两年时间,在家里种菜砍柴或是在外做些童工。百无聊赖之际,在家里学写了十几首古体诗,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所谓的平仄韵律。被我父亲发现后劝说我放弃写作,无效劝说后他将我的习作付之一炬,也可能这件事情让我始终有一个疑虑,父亲为什么烧掉我的古体诗,当时他给我说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均曾大兴文字狱的典故,“文字狱”之类的话我当时完全听不懂。父亲仅初中学历,阅书无数,正值文革期间,只知道父亲大概的意思是写诗可能给自己带来厄运。我为何失学,这件事可能让父亲有所顾忌。
父亲后面购买了一整套木工工具,找了一个隔壁的木工师傅教我学木工,我因年幼体弱拿不起斧头只好作罢。那时我能写很漂亮的美术字,当年文革很多大幅标语都是让我这个小学生爬上墙头书写的,引起很多人围观。
文学的情节始终在我心里,到了花甲之年,不知道为何这个小情节又复活了。于是我提笔写下的第一首新诗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从此一种心理暗示让自己“诗兴大发”,坚持了近一年。
好的诗歌,要有感情的纯度和厚度、要有一种浪漫的情怀、更要有一定的艺术手法和语言个性,才能真情大气、典雅精致,体现诗歌的立体感、负重感与使命感。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离不开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妙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风景,我们要用有质地的诗歌赞美大自然一切的一切,去渲染我们的激情,在诗歌里找到自己、发现自己,让我们的情感生命不断地延伸。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写出来的,不单需要真实的情绪流露、需要对生活的理解与包容,更需要巧妙的笔触与匠工的心态。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诗属于朦胧学派、现实主义学派还是其他学派,只觉得自己较多的诗应该属于现实主义学派吧?但是写实是有难度的,要融入情感因素,并要有诗的意境,弄不好就写成白话文啦,若是沉湎于想象之中,又与现实相冲突,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自我分裂,这样的我不是纯粹的自己,而成了一个披着厚厚盔甲的伪诗人。为内心而写诗,才能敞开自己的灵魂。
最近ChatGPT爆火,十大职业人将要失业的信息传遍网络,有人试用ChatGPT这款人工智能软件写诗,软件确实有一个强大的组词功能,但远没有人工的思考和情感,同理心不足、共情力不够,产生不出诗人那种深意识的创造力和灵感。
我曾经是无太多作为的文艺青年,务农7年之余,习字作画达六年之久,还有其中长达三个半年的文艺演出活动,自导自演,扮演了三个剧本的三个主角。1979年进入建筑工程公司当泥工之后,完全卷入了精神崩溃和体力严重透支的折磨之中,直至高考金榜题名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随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断了自己儿时的文艺梦想,在自己的骨子里还残存着一些文化的情愫,退休之后在一种盲目的自信钝感力下复活了。
阅读了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我很喜欢这两位著名诗人的写作风格,也赞赏新月派自主创造的新格律诗的诗风和现代派追求以奇特观念的联络和繁复的意象来创造诗的内涵。但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一样,我只是一个草根诗人,同时也操弄一些其他文体的作品,不专业也缺少一定的文化品位与底蕴,当然在自我陶醉中也是一种人生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