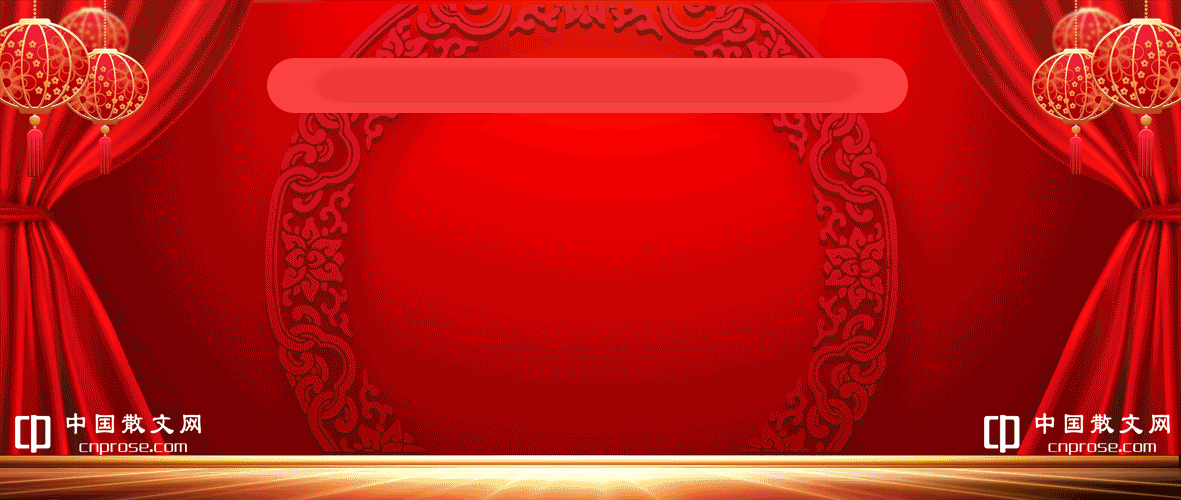【2023国庆特刊丨当代作家 黄光速 作品展】

作 者 简 历
光束(黄光速)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理工科一线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已发表SCI论文150余篇,获准18项中国授权发明专利,1项美国授权发明专利。其中两项授权专利分别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和优秀奖,承担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科技发明二等奖,中国石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等。培养硕、博士生近90名,承担本科生,研究生课程,牵头负责一门本科生专业主干课教学和课程建设工作,多次获校级教学成果奖。文学爱好者,现已退休退居二线。
作 品 展 示
我的两个姑婆
自记事开始,我就和两个姑婆生活在成都西郊城墙缺口外府河边的一个独院里。两个姑婆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三个历史时期,她们的经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姑婆和我
大姑婆生于清末1889年的四川彭山青龙场,距成都虽不足100公里,却非常封建闭塞。封建思想除了君臣父子等桎梏社会发展的弊端之外,对女性的歧视和约束更是其最大的糟粕。女孩子到了7-8岁就要裹脚,三寸金莲是待嫁姑娘的第二容颜。和生于那个年代的多数女子一样,大姑婆顺从地缠了脚。脚是人体运动的重要器官,这导致她终身不能大步疾行。九十多岁时由于行走不稳,摔断了股骨,因保守治疗失败而去世。
大姑婆人生得端庄漂亮,却不让识字;身材高挑窈窕,却裹了小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周姓乡绅的儿子。周家是方圆几十里名人辈出的书香门第,当时论家世和外表两人可能也都十分登对,否则黄家怎么肯将自己的长女嫁给周家。但周家隐瞒了大姑爷患有精神病的病史,后来他发展到神智不清,很年轻就过世了。周家四世同堂,经济拮据,大姑婆年轻居孀,又没有子嗣,无依无靠,精神压力可想而知。由于物质匮乏,她曾忆及大家庭中妯娌和婆媳之间因为口粮不足产生龃龉,特别是周家祖奶奶对于年青的孙媳妇或重孙媳妇的斥责,特别不堪。大姑婆因此决绝地吃素并搬回娘家居住。临近解放时,周家将已经工作的大姑爷的侄儿过继给大姑婆,他一直供养大姑婆到终老。而大姑婆也一刻都没有闲着,帮着带大了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她善良节俭,勤劳朴实,集中了我国旧时代妇女的很多优良品德。
由于历经艰难困苦,大姑婆最讲究的就是气节:“人穷志不穷。”宁愿饿死冻死也不能失却尊严。时值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和弟弟年纪尚小,不可遏制地贪吃美食特别是甜点。对此大姑婆曾多次生气地规劝说“再好吃的东西吞下喉咙三寸就是屎”,让我们自律。其次推崇唯有读书高。要我们闻鸡起舞,发奋学习。那时,我们姐弟俩和大姑婆三人住在西厢房。当我晚上熬夜看小说,早上上学喊不起来时,她会失望地叹息“早死三年,睡多(少)瞌睡”。那时的我懵懂又叛逆,虽不敢直接顶撞,但远不能理解她透彻的人生感悟。她也常说“和尚都是人学的”,要什么家务活都会做,什么苦都能吃,生活才难不倒你。我们家吃的辣椒豆瓣酱,豆腐乳,醪糟(米酒)和泡菜等都是她亲手做的。虽然这些事我一件都不会做,但是她做事专心,追求完美,让我学到了一种踏实的生活态度。大姑婆特别惜物,炒菜时只放很少的油,剩菜少有倒掉,总是巧妙地加入一些新的食材一起烹饪后推陈出新;晾衣服要翻过来晒,避免褪色。节俭归节俭,却绝对要干净体面。她自己也总是洁净光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背脊挺直;而我们的衣服脏了破了,都是由她洗净和缝补。那时洗衣一般用手搓和刷洗,她洗净的衣服大多还要用米汤浆过再晾干;破旧之处,织补的针脚很细。这使我和弟弟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与周围的孩子比起来颇有鹤立鸡群之感。她经常纠正我们身体的姿势: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餐桌上的礼仪更是印象很深:要等吃饭的人都到齐了才能下箸;夹菜要谦让,不能翻过别人的筷子夹菜;吃饭不能砸嘴,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曾经我对这些规矩不以为然,文革时期一度还认为是封建礼教。但是随着年岁渐长,觉得这对于培养个人的基本素质不可或缺,庆幸自己曾受到过中国传统教育。
别看大姑婆心直口快,急了会用一些愤世嫉俗的话呵斥我们。我们却一点也不怕她,以小孩子的直觉,知道她其实很慈爱甚至宠溺我们。邻居家的五姐和六哥是与我们最要好的小伙伴,但是他们总有做不完的事:要到附近玻璃厂捡“二炭”(没有完全燃烧的焦炭)、生火、煮饭、摘菜和洗衣服等等。我也常去帮他们刨炭花。一天我穿着簇新的浅色线呢衣服,蹲着去捡二炭,可能值班的人觉得那一炉炭燃烧不完全,就要没收我们捡到的二炭。我站起来气愤地大声说:“你们为什么今天就不让捡二炭了?不让捡又不早说,凭什么没收我们的炭?”一下子把那几个人怂得哑口无言,谁知其中一个人突然指着我说“抓住她,就是那个最扯的省委的娃娃”(那个地方离省委大院很近)。我吓得拔腿就跑,惊慌失措中又跌了一跤,线呢衣服弄黑一大片,还撕开了一个小口子。中午回去,一家子都非常吃惊。初步查验身体没有受伤后,大姑婆心痛地说:这么漂亮的新衣服都撕破了,还弄得这么脏,洗都洗不掉了。我抽噎着讲了事情的原委,她就没有再数落我。隔天早晨看见被污损的衣裤整齐地叠放在我床头,污渍没有了,撕破的口子织补得完好如初。
一天,五姐姐弟又因为干活不力被妈妈责罚不给吃午饭,我让他们悄悄地藏到我家竹林里,傍晚时分和弟弟各在一个大斗碗里盛满饭菜,端去和他们分食,并让他们继续躲着,等天黑再溜到我家楼上过夜。当我们返回厨房,姑婆们似乎什么都知道了,让他俩到餐桌前坐下,给他们各自盛了一碗饭,劝他们回家与妈妈和解。倔强的姐弟答应了,但却没有回家,在残缺的城墙上躲了一宿。深夜里听到她妈妈大声呼唤“五妹儿,六弟儿,妈不怪你们了,回家吧,回家吧”那声音在静寂的夜空里清晰而苍凉。大姑婆拍着床沿,咽哽着说:“作孽哦作孽,两个娃娃整来做苦工,当妈的一天耍到黑,还不准娃娃们吃饭。我们也想留他们过夜,但是挑唆的罪名担当不起啊。”
再长大一些我上小学了。那时候孩子的功课少,放学早,寒暑假又长。看着同学养蚕新鲜,就要来了蚕卵,大姑婆在空鞋盒上面戳些小洞洞,再把垫纸和蚕卵纸铺到盒里。很快蚕卵便在新家里孵化形成小小的幼蚕,一个多月后它们就长得像青虫般大,身体渐渐地变得透明,吐丝成茧后,茧中的蚕蛹锐变成蛾破茧而出,在垫纸上产下好多蚕卵。第二年大姑婆找来一个大竹筛,才满足了蚕宝宝的住房要求。蚕每天要吃很多桑叶,甚至晚上醒来也能听见它们刷刷刷的吃食声,所以大姑婆半夜都要起来给蚕子添加桑叶。养蚕的过程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多了吹嘘自己的谈资。其实这蚕是大姑婆养的,每天都要摘桑叶,洗净并擦去桑叶上的水,还要更换垫纸,去除蚕砂(排泄物)。我最多就不时地去摘点桑叶、换一下垫纸。后来我又迷上了养小白兔,那小白兔长长的耳朵,红色的眼睛,颜值很高,可是食量更大。如果放学早,有同学陪伴,我就会到附近田坝里去采摘一些农民丢弃的菜叶或其它草料;如果不想去,那小白兔吃什么,就是大姑婆的事了。就这样,我小时候还养过金鱼、小鸟、小鸡等等。我的爱好无疑给大姑婆增加了很多麻烦,但是却极少听见她抱怨什么。这或许是老人家爱屋及乌,我揽的事她一力承担,我的喜怒哀乐,她感同身受。正是姑婆们的爱使我和弟弟能够天真烂漫地快乐成长。当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大姑婆常因惦念我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新出家门,也常在田间地里一边干活,一边含泪默诵普希金的诗:我严峻岁月中的友人,我老迈了的亲人,独自在松林深处长久地等待着我,那满是皱褶的手,因耽心不时停下你的编织......。就是现在,姑婆们去世也都四十多年了,我还时常梦回府河岸边的家,寻找我的姑婆,梦境中她们仍然在已经荒芜的院子里过着艰辛的生活,醒来时我都非常心酸。这也许反映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恩,懊悔和惆怅。
三姑婆和我
三姑婆生于公元1901年。她从小就有主见,拒绝缠脚,并抗争着上了小学。但是每天上学和放学,都不让她从古镇窄窄的街道走过,须穿过族人的院子再到学校,这样坚持到了小学毕业。1921年,三姑婆只身来到成都,考入四川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她结识了亦师亦友的学姐陈竹隐女士。民国初期,当彭山青龙场还不让未婚姑娘在街头抛头露面时,陈女士就剪了短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陈女士思想新潮,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尤其是“女子要读书成才,争取自立”等观点,深深打动了三姑婆年轻的心。对此三姑婆和好闺蜜一道考进了上海的大学。到上海读书她无疑经过艰难的争取:一则这有悖于封建思想,二则家境不算富裕。在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系读书的三姑婆认识了三姑爷,一个跟杨闇公要好的我党早期(1925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留法归国学者,还当过黄埔教官。大概三姑爷觉得同为四川老乡的三姑婆秀丽能干,可风雨与共。三姑婆则欣赏三姑爷学问好,理想崇高。两人情投意合,还在读大学时就结了婚。三姑爷早年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奉命以各种身份长期在上海、杭州、江西、湖北和四川从事军运、情报和抗日宣传等秘密工作。三姑婆大学毕业以后,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夫妻俩辗转多地,身份也随时变换。后来有了儿子,为有一个掩护身份和生计,她在上海办了一家“天府川菜社”的饭馆。因为炒得一手好川菜,慢慢地饭馆有了名气,生意兴隆。但是,一些上海地下党人也知道了饭馆是自己人办的。那时地下党人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津贴,常常食不裹腹提着脑袋为革命奔走。所以三姑婆办的饭馆渐渐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聚集处,同时也成为他们的免费食堂。三姑婆一力承担,饭馆自然连年亏损,濒临倒闭。而恰逢此时,三姑爷因为身份暴露受了重伤,用白布裹住伤口装扮成布贩子从汉口九死一生逃回上海。在这紧要关头,三姑婆果断地将饭馆打出去,变卖了所有家产,回到成都。
1947年,三姑爷因为终日在外奔波,旧伤复发偶遇感冒竟溘然去世。三姑婆只好回到老家彭山青龙场,一面教书一面抚养闺蜜的女儿和自己的儿子。1948年,应中共地下党人胡春圃、肖华清和田一平等邀请,以三姑婆的名义在成都西郊护城河岸边的城墙缺口外共同购置了一座独院,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在白色恐怖下,为了策反四川军阀,争取成都和平解放,地下党人在这座西郊的小院里以打麻将的名义多次开会。三姑婆则站岗放哨,负责联系人员和传递情报等。频繁的人来客往引起了伪警察的怀疑监视,最危险的一次甚至被抓到警察局询问,但她临危不惧,机智应对,化险为夷地保护了党内的同志。如国家档案馆记载:陈子仲(三姑爷)是资深的(1925年入党)中共地下党领导,黄蜀玉(三姑婆)是中共地下交通员。但是她却一直不是共产党员,为党工作纯粹是她笃信共产党能够使积弱积贫的中国强大起来。解放以后很多地下党人的朋友相继调离成都,肖华清等想给三姑婆介绍新政权的领导,以便给五十多岁的她安排一个正式工作。特邀她参加一个川剧联谊会,结果她却让爱热闹的大姑婆去了。在解放初期,她也曾在人民公园的游园活动上见到了三姑爷的朋友贺龙,还在金牛坝宾馆见到了上海时期的老朋友邓颖超,但是她都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这使我联想到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革命胜利后,很多当年一起奋斗的同志都当了领导,可是保尔·柯察金还在西伯利亚掘地修铁路。三姑婆只有一个儿子,小时候身体不好,但是她对儿子要求严格。因为教子有方,儿子考上北京大学,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届数学力学系的高材生。本拟送前苏联留学深造,因身体不达标而落选。但是表叔在国内努力拼搏,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室主任为建设我国风洞实验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拟晋升为基地司令员,却因节肠癌晚期而亡故。或许感动于三姑婆一家的满门忠烈和贵重人品,我对她那些中共地下党人的朋友同样充满了崇敬之情。肖华清爷爷解放后当了重庆市领导,可是到成都总要来拜访三姑婆,最后一次更是杵着拐杖蹒跚地走进门来。杨伯恺烈士的遗孀危淑媛来成都就住在我家,我常常听到她们谈论国家大事,正气凛然,对个人际遇却淡然视之。老一代中共地下党人大多有文化,有修养,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中国,而不是为了赚取个人名利,为了崇高信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与现在某些一心为自己打算,甚至只信仰金钱的官员完全大相径庭。
西郊府河岸边独院里一进式的房子有客厅,东西厢房和格局相同的一层阁楼;前有花园,后有竹林,花木扶疏,俨然美丽的世外桃源。在那儿我受到三姑婆的悉心呵护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在65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被一种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声音惊醒。打开窗户一看这声音来自原本上了门杠的两扇大门被大风吹开。对着河水的两扇门的开合便产生了黑白交替的闪烁和有节奏的声响。伴随着大雨后屋檐下“滴答”、“滴答”的殘雨声令人感到非常诡异和恐怖。大姑婆呼唤弟弟和姑姑,他们没有回音。我跑到客厅看到三姑婆从东厢房来到客厅的大门口,正试图要去关门,便冲上前去拦住她说:让我去吧,路很滑。黑暗中三姑婆拍了拍我的背,说我就在你后头。我鼓起勇气冲到大门口,把大门栓插上并上了门杠。第二天发现原来是小毛贼把我们家侧屋里晾晒的衣服全部偷走了。晚上放学回家时我听到三姑婆跟大姑婆说,光光勇敢有担当,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我听了备受鼓舞。
养女孩子的家长最害怕的是孩子懵懵懂懂地遭到性侵,对人性中这种阴暗面,中国式的教育往往又是三缄其口,但是三姑婆有她的方式。当我情窦初开甚至更早一些时,她总是当着我的面与客人聊起一个认识的女孩被欺骗和受凌辱的故事,搞得我非常窘迫。一天我约了一些朋友来家玩,那时的文艺青年饥渴地相互借书,热衷讨论心得。彼时,她们口若悬河,针对《简爱》,《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卡尼琳娜》等小说中女主的人生际遇,论之滔滔。三姑婆当时佯装在场做事,其实是想了解我们的认知水平。打那以后,她知道她孙女有理想有追求,不会犯低级错误。就再未讲起过那个“经典故事”。
高中毕业时,我执着地认为既然别的女生可以下乡,作为学生干部的我也不该逃避。三姑婆经过仔细思量,同意我到离家较近的川西坝子插队当了知青。七七年高考时,我已经从农村调回成都到一家央企的宣传科担任了广播员。是否还考大学?这意味着将丢掉现有的工作,不能再自己养活自己,且毕业时还面临再次分配。作为单亲家庭的母亲,妈妈反对我考大学。但是,三姑婆毫不犹豫地说,“读书改变命运,读了大学将来发展空间更大”。支持我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学的有名专业。
也许经历了很多大事,三姑婆是一个沉着,不太表露感情的人。所以她对我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她对人处事的方式。这种教育是浸泡式的,无声无息,却可以塑造一个人的灵魂。那时,她担任居委会主任,这是一项没有津贴的工作。但她总是非常认真地忙前忙后,做事讲究竭心尽力,问心无愧。印象中她组织过缝纫社、饲养场、生产组,还管理公房的租赁等等。当然,给吵架打架的邻里或家庭断公道,也是她的工作。她断公道时讲得最多的就是“将心比心”和“换位思考”通俗易懂且非常管用,因此方圆十里内“黄主任”受到大家由衷的尊敬。
那时,流过我家门前的府城河水清澈见底,常有独木舟载着打鱼郎和鱼鹰从水面滑过,宁静而美丽。1962年夏初,据说河里发现了砂金,于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打破了河岸的静谧。他们涉入齐腰的水中,反复地挖砂,淘洗,收获颇丰。中午时分,他们会从河里上岸来,坐在我家门廊外的台阶上用午餐。灼人的阳光或骤雨下遮蔽他们的只有一顶草帽;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又多系干粮没有汤水。小孩们自然看不到这些,每当我们放学回家,等待他们挪开座位时总怀着一种天然的恐惧感,避之不及。可是三姑婆却让我们把大门打开,拿出温水瓶请他们喝水,并邀请他们到大门门廊内的长凳上休息。整个夏天和秋天过去了,我发现那些淘金人个个谦恭温和。这个童年的经历使我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遵守正反馈模式,当你心怀善意,尊重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以同样地方式待你。
也是那段时间,一天我家来了一个高大帅气,却生无所恋的青年人。原来这位左叔叔与我家邻居的女儿珍在西昌的同一单位工作,且确定了恋爱关系。珍小姐生在牛奶场资方家庭,咽不下粗粮,倒掉了半碗玉米粥,被人揭发开除了公职。左叔叔侠义辞职陪珍回到了成都。可珍父翻脸不认人,把左叔叔赶出了家门。待他找到黄主任时已身无分文且无处安生。三姑婆听罢左叔叔的遭遇,先是帮他找到一间公租房,垫付了房租,让他暂时到我家吃饭,然后又在生产组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同时劝说珍的父母接纳他。几年后左叔叔换了工作,户口迁入成都,才得以和珍小姐结婚。
三姑婆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对弱者,对劳苦大众不可竭止的同情,对需要帮助的人不吝出手相助,且不求回报。因为遭遇五七年的风波,我父亲很年轻就因心脏病亡故,三姑婆义无反顾地抚养我和弟弟长大成人。
也许成年后人脑的海马区发生了变化,转眼间,当年的少年已渐生华发。但是,往事并不如烟,百年树人,希望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失信仰且仍有传统美德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