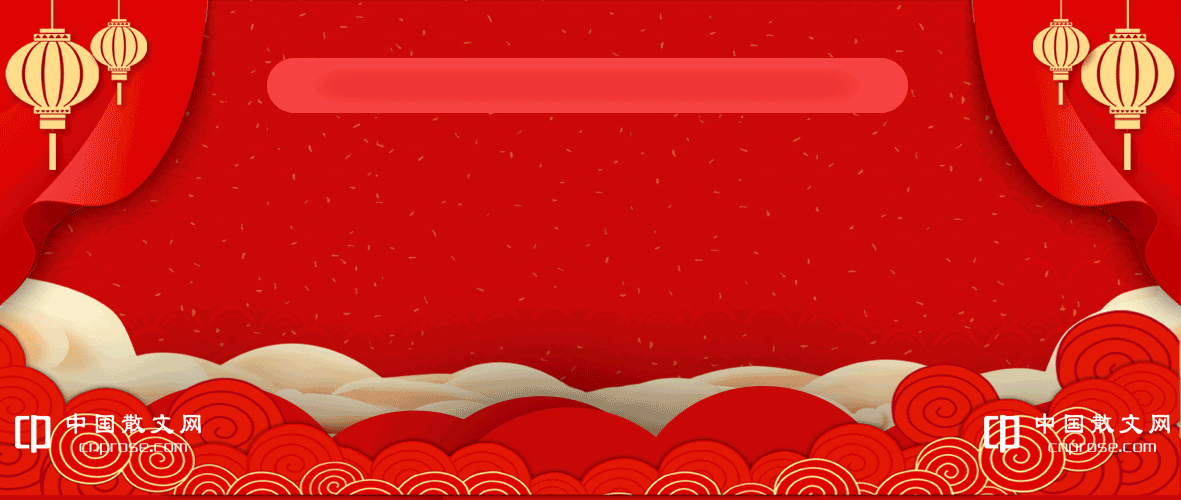【新中国75周年特刊丨当代作家 杨敬选 国庆作品展】
当代作家
杨敬选 国庆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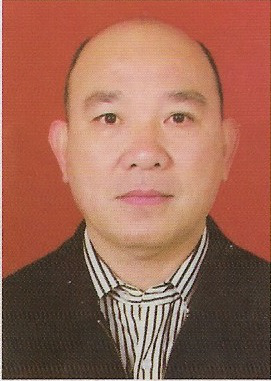
作家简历
ZUO JIA JIAN LI
杨敬选 1959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徐闻县。1978年3月入伍在特务连服役,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荣立一次三等功;1981年5月参加了中越边境法卡山作战负伤后被评为因战致残荣誉军人。1983年10月退伍回乡后从写新闻报道开始写作,并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网》和《中诗网》等各级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作品,2009年出版个人作品专集《草根·良心》。2021年5月获批准成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23年出版个人作品专集《敬心·选迹》,深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老师作诗为序。
祖国万岁
国庆作品展
GUO QING ZUO PIN ZHAN
永远的特务连
——仅以此文怀念参加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战友
我的人生将快走完工作的履历,无论我一生有过多少变化和不同的岗位,但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填写工作履历我都会毫不犹豫且庄重地填写上,“1978年3月入伍在陆军一四三师四二七团特务连任战士”。尽管我所在的这个特务连几经演变过广西边防一团特务连、广西边防三师七团特务连……!但在我心中的特务连便是最伟岸最自豪的丰碑,而且已深深镶在我心灵的殿堂,珍藏着数不清难以忘怀的永恒记忆。
我们年轻时的那个时代,文革刚结束,高中毕业的五八、五九年出生的我们那代人没有高考的机会,反正高中几年也没学几节文化课程,而是学什么种甘蔗、兽医等什么的“实用”知识,大多数时间是修水库和参加农场劳动。毕业了,农村户口的回农村,城镇(商品粮)户口的也上山下乡都是到广阔的农村去大有作为。因此,我和郑学章、吴定明等七个同学一起选择了报名参军。
经三个月的新兵连集训后,我被分配到四二七团特务连的工兵排三班,特务连便是我离开农村,离开父母后第一个拥有的单位名称,而且是如此的自豪、响亮、神秘,令人羡慕。最初我们的这个团本是生产部队,同我一起当兵的其他战友都分到生产连队,每天都有播秧任务、收割任务、养猪养鸭任务,而我们特务连是没有生产任务的。更令我激动的是,特务连里竟有几个1975年入伍的海康籍老兵曹林胜、朱兆育、陈保宏等,我所在的工兵排还远离连队,独自到师后勤部管仓库和加工大米,还管理着一个冷饮冰室。让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兵,心中揣着满满的欣喜,工作训练都不知疲惫,每天早上起床,打扫卫生,端水给老兵洗脸、洗衣服,搞副业种菜等等总是争先恐后,深得领导和老兵喜爱。我们远离连队,在烽火角独立的一个排,班长刘兴旺和副班长刘训祥都是1973年入伍的老兵,排长也是1968年入伍的老排长,对我们刚入伍的几位新兵都关爱有加、严格对待,这也是我对特务连爱得如此深沉的第一份印记。
1978年中旬过后,越南开始排华驱侨,关系紧张。那时资讯不发达,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只听说中越边境可能会爆发战争。刚入伍的我们满怀报国热血,纷纷递交参战申请,虽百般不舍刚从农村来到如此温暖炽爱、紧张活泼的连队,可这些年中国人民抗美援越换来越南的背信弃义,激起我们难以压抑的民族愤慨和爱国情怀,我们的热血和激情充满了每个细胞。终于,我的参战申请获准了,随特务连建制踏上广西凭祥市中越边境最前线——友谊关守备部队,成为广西边防第一团特务连。
几天几夜的货厢火车行军,到达驻地已是夜里。翌日,军号吹响,操场上的口令声划破浓雾笼罩着的山峦,此起彼伏,这才让我第一眼看到特务连营区即边防一团司政后指挥机关所在地。这里离凭祥市只有两公里,三面青山环绕,中间是一片几百亩开阔地。而且高山翠绿,生机盎然,纯天然屏障,屯兵之所。两山峦间的进出要塞,就是我们特务连警卫排要守卫的营区大门和指挥机关重地。除警卫排之外,特务连还有工兵排、防化排、侦察排、通讯排等,承担着不同性质的特别作战任务。也是在接下来的战前训练中,我才真正按正规条令要求,开始学习到排雷、埋(布)雷,制造地雷和识别世界上以及越军最常用的地雷和爆炸装置。还学习了地形图测绘、标识等侦察技能以及捕俘格斗等。还有经常的夜间紧急集合,越野奔袭、拉练等课目训练,训练的那种苦苦如炼狱,但“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教育,让我们增添了毫不疑问的自觉。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投入战斗,但我们的工兵排和侦察排在战前已经常地到边境侦察。因而,为提升战士们的心理素质,特务连的指导员姜书武总是绞尽脑汁地折腾我们,让我们从行动上到灵魂深处都烙下对他深深的印象。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他竟然在还未开战前的一个周末晚间,严肃地用慷慨激昂让我们提前写好遗书放到背包里的最显眼处,这让我百思不解,这会让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多岁的年轻娃经受怎样的心灵煎熬啊!我至今仍深刻记住这一晚的悲切。可我们挺过来了,胜利凯旋后重读这一份遗书,还曾让我们深深地为自己的壮怀热烈而感动。还有就是经常地夜间紧迫集合,紧紧张张地把队伍拉上阵地,做足战斗准备,拂晓又宣布实战演练结束。让《狼来了》的故事重复多次后,我们心理上的恐惧已荡然无存。到了最后那一次,看到炮火连天,枪声四起,敌人的子弹雨点般打过来时,我们已不再恐慌、害怕了,反而沉着机警地沿着已训练过的方案攻向我们的敌人目标——那行公安屯。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我还只是一个入伍不到一周年的战士,不知道什么兵力部署,作战方案之类的东西,只根据战前的训练,跟着班长听班长指挥。我们特务连,最早派出去是侦察排和配合的骨干工兵。其次是警卫排,要提前到位担任前线指挥所的警卫,还要留守后方指挥所的警卫,唯有我们工兵排是配合其他连队作战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的第一天,我们工兵排的任务仅是为进攻竹林山的连队排雷和用320爆破在敌人的雷区炸出一条进攻的通道。一开始的排雷并没有遇到越军的抵抗。天尚未尽亮,四面八方炮火齐鸣,枪声四起,此起彼伏。我们害怕紧张,但仍细心摸排着敌人埋设的地雷,很顺利但进度太慢,排长便命令提前用320爆破开辟通道。我们工兵排一班先行爆破还顺利,可到了二班却有一串320炸弹被吊挂在树上爆炸,二班班长陈周开被弹片击中头部被抬了下去。最后到我们三班推进到一土坡后面,右侧是一片竹林。我跟在班长后面,一看土坡较高,我想爬上去却被班长按住,便又想借竹林掩护观察一下地形,可还没等靠近竹林便一阵子弹扫过来,打得竹林“啸、啸、噼、噼”地响。班长大声呵斥,“危险,快回来!”我返回土坡后面气喘吁吁。想给跟在我身后的八二五无后座火炮手指明敌火力点的位置,班长也骂我,“指个屁,根本看不到火力点”。于是,班长让我们就地展开320炸弹,进行爆破,一瞬间,一道亮光冲天轰响,我们成功了,炸出一条进攻通道,进攻部队冲了过去,我的双脚却疲软了下来。直至下午四时,攻下那行公安屯,听说击毙的越军只有四具尸体,让我们十分懊丧。而我们当时并未知道受伤的二班长陈周开已光荣牺牲,更悲的我还在撤回指挥部待命时,听到在进攻竹林山时老乡、同学、战友郑学章牺牲的死讯,心情沉重痛入肺腑,却只能强忍着泪水不能溢出眼眶,不敢让战友们看到。这个夜晚,我斜靠在树林中间,依稀能见到星星,远处还能听到零星的枪炮声不断,可我内心却无法平静下来,借黑夜躲着战友让眼泪静静流淌,默默地祈祷有美梦伴我度过这不寂静黑夜,再迎接黎明的战斗……
二月二十二日,那行地区战斗结束,野战部队向纵深进攻,而我们又奉命奔袭一百多公里转战板兰地区,至三月十二日返回营区,一边休整一边随时奉命配合执行各种各样的战斗任务,历经一次次生死考验。让我幸运的是,由于战后布防需要,团里让副团长蒙柏南组织一个边境线防御工事和雷场设置勘察小组,抽调我参加。我和老乡战友万良跟着蒙副团长踏遍原边防一团所守卫的凭祥、龙州、宁明三个县(市)两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和守备连队阵地,一个一个地勘定防御工事掩体和布雷区,并一一标绘在防御地形图上。也正是因在此项工作中的表现,我被长期抽调到团司令部作(战)训(练)股做测绘员代理参谋,而离开了特务连。但编制一直还在连队里,才会有通过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那一份让我无法忘怀的永恒记忆。
在特务连的工兵排三班,我和1975年8月入伍的老兵汤昌祝最为相好。他比我早入伍三年,年龄只比我大一岁多,个子也不大,但军事训练和技术以及综合素质都是全班最好的。被派去配合执行侦察任务最多的也都是他,而且听说他是一个高干子弟,但只知道他的入伍时间很特殊,却从没听他说起过家庭背景。我也是仅从他的军事技能和个人品格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而成为最铁的战友。可没想到,我们在2月17日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最激烈的那行地区进攻战中能胜利凯旋,转战板兰参加多场战斗也都能平安归来,反而在8月14日的边境侦察中却光荣牺牲。党支部讨论我入党的这一天,他本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可他却刚刚牺牲了,我的排长李迪平面无表情平静地代读着汤昌祝早前写下的介绍,会场气氛凝重、庄严,而我却怎样也控制不住滚烫的热泪盈眶而出并任由其顺着脸腮肆意横流。我至今不敢深究是我经受起了血与火的考验,或还是战友汤昌祝,一个年轻的党员生命最后的推荐,让我顺利通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许作为军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战友们也许已不再记得起,可我人生的这一幕却已深深地镶在我心灵的殿堂40多年,每每想来或说起,我都无法忍俊得住热泪。在我的心中怎样也忘不掉汤昌祝战友那挺拔的身影和永远灿烂的笑脸,我多想这种思念能让他及特务连牺牲的战友们永垂不朽地活在历史长河中,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特务连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一共牺牲了左正强、陈周开、赖锦成、汤昌祝、王幼连五位战友,还有被地雷炸断双腿的李保二和受伤致残的战友老乡李保冰以及我本人等一共十多名因战伤残荣誉军人也都将在特务连的史册上留下鲜红的色彩。
尽管后来,我一直在团司令部,参加了1981年5月的法卡山炮击到法卡山争夺战,历时三个多月,到最后受伤致残1983年退役回到地方安排工作。在部队的五年间只在特务连训练、作战、生活不足两年,但我却一直是特务连的战士。回到地方后有过无数次的工作岗位变动,填写过无数次简历,然而最自豪的第一笔人生经历便是在特务连服役。尽管我的人生也创造过其他业绩,然而,在我心中甚至灵魂深处最忘不掉的还是在特务连的战斗岁月。那里寄存着太多我们那一批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报国情怀和不怕艰难困苦的顽强意志以及浴血疆场的生死战友情谊,还有姜书武、黎先福、农绍绥、李迪平、张卫国等良师益友般的战友、领导以及太多的想不起记不清的新老战友朱豫刚、黄永生、李景才、钱智国等等,他们历尽战火硝烟和岁月风霜的笑脸常在我的梦乡萦绕,还有经常地遥寄着亲人般的问候、关怀、祝愿,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屹立着一座丰碑,无尽思念的丰碑——永远的特务连!
落 叶
2020年的深秋,超龄工作了两年的我终于被批准退休了。为答谢在融资工作中帮助过我的一些金融界朋友,我特地租借上海湖南路一会所办了一桌酬谢晚宴。因住在兴国宾馆较近,便提前沿着湖南路漫步前往。
深秋的上海已寒气袭人,凉风嗖嗖地吹落满地金黄的梧桐树叶,几乎洒盖满不宽的路面,一阵一阵的风吹卷着黄叶飞扬又跌落,不由得我踏着落叶心头揪紧。恰逢刚退休的心境,一种莫名的悲凉袭上心头,仿佛风儿在耳旁呢喃提醒,人生再怎么样辉煌也会像这梧桐树落叶一般离开喧嚣的都市和繁华······
这一幅落叶的意境画面刻在我的脑海,让我一直在想,退休后该怎么样面对生活的心如何安放才不会悲凉。还好,因为我的实际情况容不得我有太多的遐想。我父亲早亡,母亲已是85岁高龄,且患脑血栓后遗症四年,在任时工作忙,无暇顾及,兄弟姐妹们也都能理解,现在退休了。萦绕牵挂便是该怎样回到农村老家去陪陪母亲。
我的家乡在祖国大陆最南端一个三面环海的海角——排尾角杨宅村。地处偏远,道路不通。耕地沙化缺水,冬天沙尘飞扬,夏天烈日滚烫,甭说种庄稼,人赤脚都不敢踏走。我从小就没见过爷爷,父亲就是家中独苗而且孤儿寡母,但却读了一点书,外出工作竟难以养家糊口。我母亲嫁入这个穷家,至今我都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凭她一人之力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成年,而且在那个物质极度贫穷中还让我们都接受了高中教育。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这点文化傍身,十八岁我便离开了这个贫穷落后的家乡去入伍当兵后一直在外工作生活至退休,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还会回到农村家乡来生活。然而,退休了,家中有患病的母亲需照顾,既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将母亲接到城市的家里,也不舍得将母亲孤托到养老院去,自己回家伺奉已是最佳选择。退休回家还有母亲听我叫唤,这种幸福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安然恬静和欣然。每天的清晨,保姆都会早早地为母亲洗漱、抹拾、喂饭后将她推出院子散步,我起床后也会参与推她晒太阳或匍伏在轮椅边或病床前陪她说说话,虽不知道她听没听得明白,我都当她正常说话。有时看到她精神很好,眼光发亮,我还认真的看着手机给她唱上几首歌,阎维文的《母亲》、刘和刚的《拉着妈妈的手》、乌兰图雅的《梦中的额吉》她都喜欢听,有时唱着唱着,触景伤情,我的脸上竟不自觉的淌流下滚烫的泪水,母亲的手竟也将我的手紧紧的攥着······
退休回村伺奉母亲一住几年,乡亲们无论什么时间相遇问候、招呼和闲聊都一样真诚,让我感受不到离开工作岗位后的那份失落,不像在机关大院连门卫都明显表现出区别。反而是刚上任的大学生村官和年轻的村长经常来串门,就时下政府推动的乡村振兴项目如何落实来听取一下我的意见。也就让我退休后的这几年有机会参与到对生我养我的家乡的发展尽了一份心。
乡村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贫穷落后的,可退休回村生活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如今的农村已今非昔比,城里人有的农村人也都慢慢地有了,但农村人居住的别墅庭院绿树掩映、鸡鸭成群、瓜果飘香,还有我们海边渔村的涛声阵阵,孩童们在沙滩上蹴浪兼天地嬉戏,城里人只有羡慕的份了。没有退休时对乡村振兴总是那么不太以为然,但随着中央对乡村振兴力度的加大和配套政策的到位,乡村振兴竟宛如春风吹灿了祖国的农村大地。先是村村通公路甚至村道都硬底化,让昔日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一去不复返;再是改水治旱让烈日炎烤的红土耕地都得到灌溉,而且农民大都用上喷灌设施和大棚种植养殖;还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整治,不但农村满眼青山叠翠,田园葱绿,还有村道小巷都装上了路灯,设立了垃圾站,有了保洁员,让村民自己将脏乱差都管了起来;更有文化艺术体育下乡,三乡六村都在建设文化楼、图书馆、艺术室、球场、小公园等;随着又有民宿、非遗、乡村旅游、农产品直播带货等等,人人憧憬向往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也让我忘记年龄不知疲倦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喜不自禁,难以忘怀。
2022年底,我年近40的女儿给我添了一个白胖外孙儿并回湛江休一年产假。更让忙乎的我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育婴师每周日休息就需要我回家顶班做点什么。年轻时,因生活条件苦和工作忙,我都忘了是怎样带大孩子的,可眼下的小外孙从小就喜欢我抱,喜欢听着我哼唱摇篮曲哄睡觉。把我会唱的曲唱穷了,只能用手机搜播世界名曲给他听,什么“拉德斯基进行曲”、“斯卡布罗集市”都能让他喜眉抿嘴地开心。这种辛苦并快乐着的生活让我从来没有过离开领导岗位后的那种失落,也淡了退休后世态炎凉的创伤和忧愁,燃起了渐渐过渡到老人生活的现实和自信。
在农村的乡下,冬天要比城市里冷很多,而且窗外能听到寒风吹落树叶的响声。我手捧着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但袭上心头已不是秋风落叶的哀叹,自我感觉萌生的是甘愿化作春泥的遐想。无论是投身乡村振兴还是伺奉母亲替孩子带孙子都是那么从来没有过的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让我明白人生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使命。岁月轮回,四季更替,我庆幸生逢火热的年代,付出过青春热血,收获了丰硕的秋实,坚信能走过严冬迎来更加绚丽灿烂的时代春光·····
武汉樱花别样妍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踏青赏花成了国民的冲动,远在武汉的朋友竟然还记得抗击新冠疫情时“待到病毒扫尽时,请到武汉赏樱花”的邀请,我受宠若惊。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不仅以其三千多年的楚文化发祥地而厚重深沉,更以其九省交通枢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重大历史事件而名声显赫,还与大江大湖大武汉以及科技武汉、创新武汉引领当代中国风范。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中,武汉人民团结拼搏,科学应对,为全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谱写出一曲曲雄壮的胜利乐章。我被武汉人民感动了,我被武汉的医务人员感动了,我被四面八方奔赴武汉抗疫的各行各业人员的无畏牺牲感动了······而写出了“最美的您——献给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的诗歌,发表于中国诗歌网,并被配乐朗诵。让我激动的心久久难以忘怀。也是新冠疫情中,我老家徐闻县人民除夕夜无惧新冠疫情风险妥善安置无法过海的湖北旅客而感动全国的义举,两年后曾被他乡援助安置过的襄阳青年韩金宇又千里奔袭赴徐闻报恩做抗疫志愿者的故事也被我写成“远乡疫情的呼唤”散文发表于中国散文网等刊物。都让我对武汉感动在心而答应了朋友的相邀。
但是,那时答应去武汉赏樱花却是对樱花知之甚少,到了今年朋友落实下赏樱花的预约门票,我才匆忙补课。樱花是蔷薇科,樱亚属植物,品种相当繁多,有300多种。全世界共有野生樱花约150种,中国就有50多种。全世界约40种樱花植物野生种祖先中,原产于中国的有33种。樱花呈伞状花序花瓣先端缺刻,花色为白色、粉红色,复瓣类多半不结果,常于3月与叶同放或叶后开花,随季节变化。武汉的樱花基本清明节前逐渐凋谢,网上对武汉樱花有多种褒贬说法,都是因为武汉的樱花种植史上与日本侵略我国历史相关,让我怀揣疑惑。
3月23日,我们是下午凭预约门票进入武汉大学的校园。但见这游人如织实在超出我的想象,原来是湖北文旅和高教部门结合赏樱花组织全省各地高中生专场武汉大学赏樱活动,一时间让武汉大学这座高等学府到处充盈着青春的活力。从武汉大学体育场漫步走来,整个校园的樱花都已落尽绿叶,只有枝头白色的樱花竞相怒放,一簇一簇争妍斗艳,洁白羞红淡粉,让人惊叹流连,说不尽妖娆美媚,心旷神怡。正当我们忘情观赏时,突然樱花大道上人群骚动,呼唤声一浪一浪传来,竟偶遇网红董宇辉在武汉大学做赏樱直播,只因为我们没淌追星潮流,竟不知道董宇辉如此备受追捧,宣传功力爆表,而不得不为武汉市的文旅部门点赞。
在樱花大道上,恰逢一位年长的老教师给高中生专场的学生介绍武汉大学的樱花为什么夹杂着耻辱与和平的复杂感情。原来武汉大学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曾被日军强占做为日军伤兵医院。日本侵略者为了让侵略日军伤兵免除思乡之苦,便带来18株日本野生樱花栽种在武汉大学校园内,这也便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耻辱印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日本友华人士为了纪念中日缔结和平,也赠送20株日本樱花在武汉大学校园里栽种,到中日邦交20周年纪念日时,日本友华人员更是一次赠送1000株日本多品种樱花在武汉大学主干道两旁种植出一条樱花大道。祈望这和平之花遮盖了一切日本侵华之耻辱。后来,武汉人民更是将樱花种满了东湖以及大街小园,让樱花作为和平之花的愿景开遍武汉以及全国各地。从此武汉的樱花不仅记载下侵华日军的血泪深仇并留下淡红的血印,更寄托着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珍惜。现在又经历过抗击新冠疫情病毒胜利的壮举,粉碎了西方列强的抹黑攻击,更以创新发展描幕出蔚蓝的大美中国的缩影图画,武汉的樱花已别样妍美、鲜艳,让人奋发憧憬。只不知日本仇华的军国主义者们会否明白中国人民的善良和愿景,那是另一回事了。
正在我们满心专注的欣赏着一簇一簇花瓣时,忽然一阵大风刮过,吹得整条樱花大道樱花像雪花一样满天飘洒。我迟疑地停下脚步,看着满眼的樱花薄如绢纸般飞落,竟仿佛看到林黛玉的葬花篮中装满侵华日军的亡魂凄苦且狰狞,不禁让人寒蝉,心中更揣满了对樱花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热烈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