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华忠|金龙贺岁·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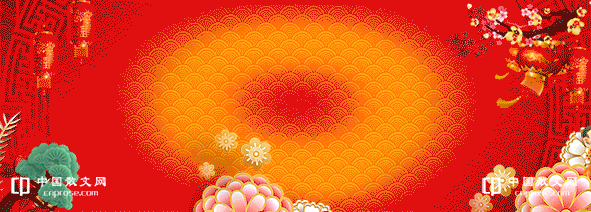
熊华忠|金龙贺岁
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作家简历
★
熊华忠 生于1966年2月,重庆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学资深语文教师。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网高级作家。中学时代,文笔初露锋芒,高考预选,作文斩获满分;大学时代,即开始在《重庆晚报》上发表散文。阅读不止,笔耕不辍。迄今,已创作出散文500余篇、古诗词近2000首,在《重庆晚报》《重庆民盟》《金沙文化》等报刊及中国散文网等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发表散文近百篇。《夜色朝天门》等多篇散文荣获全国文学大赛一等奖(金奖),《空山新雨后》等数十篇散文入选《漫卷书香》、《本色依然》等文集,编撰《沙磁春秋·人物卷》等书籍数部。
孩子,别哭!
——致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实习老师李*同学
夜阑珊,灯黯淡,宁静的夜,仿佛是一首摄入心魄的曲子,随寒风悠然地传唱……伴乐而起,手指跳动出浓情的文字,心音拨动着牵挂的琴弦。
惜别的那一刻,你泪眼婆娑。三个月的历练,你从初始实习时的畏葸踌躇,至最后走上讲台时的泰然自若。凤凰涅槃,你收获了惊喜。泪眼里,五味杂陈。
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
你来自古都南京,书香门第,大家闺秀。学生时代,你曾感受过黄海之隔的小学教育,也在一所封闭的县中里度过人生最灰暗的光阴,高中时就读于巴金先生的母校。可以说,你经历的教学模式是多样而丰富的。自走上实习岗位的那一刻起,你一直在思索: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日本教学模式科学、规范,培养出彬彬有礼的高素质公民,可日本青年人自杀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他们的教育,是否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孩子们的个性?‘衡水模式’或‘县中模式’是目前中国应用最广泛的教学管理模式,在情感上,我对它深恶痛绝。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因为我少写了一道题而当众羞辱我、把我一巴掌打到咯血的男数学老师,以至于我有时在办公室里见到某个男老师疾声厉色地训斥学生时,我都会忍不住颤抖——那是我一生的阴影呀!”
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孩子。
你将你的高中时代戏称为“我的人生思想启蒙时代”。你说,这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学校,它的优秀无法用字句描述。“倒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知名的校友,而是它教会了我独立、自由、民主的思想,并使我受益终身。在这里,学习即是目的,成长即是目的。在这里,我了解了帕斯捷尔纳克和十二月党人,了解了形而上学与佯谬理论,了解了乔治奥威尔与《利维坦》。这是一种无可取代的体验,亦是一双珍贵的思想的自由之翼。”
你是一个有风骨的孩子。
当你由学生身份开始转变角色时,你不由得开始思索:我该以什么样的姿态站在讲台上?“我的语文老师王栋生(笔名吴非)说过:‘不跪着教书’。我见过太多跪着教书的老师了:我初中时那个数学老师——大肆兴办补习班,下作排挤不参加的同学的老师;明示暗示送礼不成,就百般折磨羞辱学生的老师;醉心于各种作秀的赛课评选,实则腹内草莽、知识陈旧不堪的老师……”
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一次,细心的你,无意间发现我正在阅读梁晓声的《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文艺》,于是,话题打开了——聊文艺评论、文学创作,进而聊诗词歌赋、“竹林七贤”……侃侃而谈,好不投缘!似相见恨晚。
过了几天,你竟然虔诚地送给我一本梁晓声的《中国生存启示录》。对此,我甚为惊愕!原来,此书是你父亲2014年8月去上海出差时,巧遇梁晓声教授正在复旦大学举行现场签名售书活动,嗜书成癖的他,于是头顶烈日排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的队,才得到的,如获至宝,乃视若家珍。当你得知我也喜欢梁晓声的作品时,便心领神会地火速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你父亲求助,恳请他“忍痛割爱”把那本《中国生存启示录》快递过来,然后赠与我。用心何其良苦!
品读着你实习结束离别时亲手捧给我的那封透溢出娟秀字迹、饱含着质朴真情的书信,我泪如泉涌!“……而老师您,向我示范了一个学术经验兼修型老教师的专业素养。您课堂上谈笑风生,深厚的文学积淀洋溢于每一句话,让我拜服之余又深感欣慰。这也许才是‘师者’真正的姿态。”“实不相瞒,大学时期我得了抑郁症,母亲实则是因为我的病情而来的重庆。之前多次向您请假实则是去心理治疗。这三个月与您、与老师孩子们的相处,使我渐渐宽慰,前阵子医生说我病情也减轻了不少,渐渐停了用药。老师以及孩子们、给我带来光明与温暖的人们,这份感激不知如何表达才好!(希望老师能帮我在孩子们面前保守这个秘密)”
天下终无不散之宴席。三个月之期过隙,笑语之晏晏犹然历历如昨。知惜别之不免,悔欢聚之无多,惟望后生平安喜乐。
恣意的笔尖再一次落在洁纸上时,不知所措的情丝里,让我早已写不尽这个季节里的离别和喟叹。
孩子,别哭!
候鸟断想
深秋的一场冷雨下过,天色已近黄昏。
天空,随风而动的灰色云层下,几只燕子忙着捕食。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跋山涉水”飞往南方了。用羽翼追求梦想,丈量天下,一路奔波劳顿——如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
飞去兮,排云几万里;归来兮,击水而嘹唳。风餐露宿,戴月披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它们自有风骨,傲气铮铮。
说起候鸟,人们并不陌生,常见的燕子、鸿雁便是——因其随季节变更而迁徙,故名候鸟。古往今来,一些文人墨客在其诗文中常常写到它们,特别是其中的燕子、鸿雁更是屡见笔端。如唐代诗人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宋代诗人徐府《春游湖》中的“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等诗句,都写到了燕子的情态。在这些隽永清新、脍炙人口的诗句中,燕子成了春天的使者,成了生机盎然的春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燕子不仅选择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到来,而且其对居住环境也十分讲究:它们不在树上、崖上做窝,而是选择在人们的屋梁上筑巢。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免受日晒雨淋之苦,免遭天敌的侵害,而且还能受到主人的保护。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一诗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名句,写的就是燕子这种傍人而居的特点。王谢堂前的燕子并非攀附权贵,只不过那里屋宇轩敞,环境宜居罢了。一旦王谢家族败落,华堂不在,它们也能随遇而安,飞入寻常百姓家筑巢而居。至于历代文人墨客写到鸿雁的,也不乏其例:如“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其名冠古今的《藤王阁序》中就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锦句来描绘鸿雁在寒风中列阵而飞、大声鸣叫,大规模迁徙的场面;又如南宋词人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画面清新,借助鸿雁传书的传说,渲染了一个月光照满楼头的美好夜景。记得上小学时读过的一首以鸿雁为题材的儿歌:“西风吹,雁南飞。飞到天空里,同去又同回。谁也不抢先,谁也不掉队。晚上停下来,芦苇里而睡。相亲又相爱,胜过亲姊妹。”儿歌作者巧用拟人的手法,通过描写鸿雁迁徙过程的生活习性,赞扬了它们遵守纪律、团结友爱的精神,很有感染力,对幼儿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与鸿雁有关、影响深远的故事莫过于“苏武牧羊”。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被迫在“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牧羊十九年,受尽折磨,仍坚贞不屈。后来,汉王朝假托从苏武的鸿雁传书中得知其尚在人世的消息,并据此与匈奴交涉,把苏武营救回国。千百年来,这一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对国人影响至深。在国家遭遇外辱时,它成了教育国人保持民族气节、抵御外敌侵略的经典教材。
想起苏轼,也似一只离了群的孤雁。他也曾年少轻狂,满怀单纯明亮的报国理想,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几起几落,仕途坎坷,贬谪之地更是一远再远。落魄徐州时,他拜会一山间隐者,山人有两鹤,温驯而善翔。他与宾客觥筹交错,兴起而作《放鹤亭记》,文末录山人招鹤之歌:“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
是透了骨的寂寞吧,那寂寞泛着凉,寄语归鸟,却是拣尽了寒枝,无处栖身……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无心白鹤,温柔此乡,都是留不住的盛景,可笑多情太守,竟千般不舍。
我习惯于跑步。每当夜幕降临,我就会到小区健身道上运动几十分钟。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奔跑的方向也从未改变,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惯性,从未仔细去想过缘由。总会遇见相似的人,彼此擦肩,然后默默远离,一段距离之后,又会重复这个过程。
常常会想,这周而复始的圆周,好像钟表的循环,每一个人,都在刻度着一分一秒的流逝。
头顶上是闪烁不定的星辰,有时停下脚步,只需驻足一会儿,就会看见夜航的飞机当空划过。明明灭灭的夜航灯,勾勒出流星过境般的轨迹。
但我不愿把它想象成流星,因为航班终会回程,而流星去而不返。我愿意把它当作一只候鸟,挥舞着巨大而孤单的双翼,满载着旅人们说不清是忧伤还是幸福的心愿,迁徙在漂泊的天空。
说到底,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只候鸟,以为命运是不再回头的直线,却总在某个转角,偶遇久别重逢的故事,喜也好,悲也罢,那一瞬间心惊了,却终于释然。
等某一天老去,再遇见熟悉的眉眼,淡笑一句:“哦,原来是你。”
再不需更多的话。那山河岁月,覆盖了候鸟苍白的羽,把归途和起点,都模糊成了迷离的流年……
夜色朝天门
宽阔的江面突然一暗,那是吝啬的夕阳急不可待地收回了最后一抹残红。朝天门,识趣地投入了夜的怀抱。
没有了黎明市民晨练的闲适,没有了白昼游客熙攘的磕绊,照理说,入夜后的朝天门该是安歇的时候了。然而,此刻的它,却比白天更多了一份暗藏的热闹。不信你瞧——
“朝天扬帆”,由8座超高层塔楼、6层商业裙楼及3层地下室组成的重庆来福士广场,在灯光的映照下,水晶宫般熠熠生辉,现代时尚气息爆棚。一边是霓虹闪烁的缭乱红尘,一边是和静清寂的江流,它们宛如得道的老僧,宠辱不惊,一任时光荏苒。
在江滨上悠然漫步的人们,是在夜色中寻思着当下的生活,还是在贪恋这份江风拂面的舒爽?抑或正触景生情缅怀着自己如烟的过往?
灰暗的江面,渐渐变得炫目起来。打着各种醒目广告语的游船,在江中慢悠悠地游弋着,将黛青色的江水,勾上了一抹艳红,如花似绸一般。甲板和船舷边上影影绰绰的红男绿女,又在窃窃私语着怎样的人间情话和绵绵心思?或许,他们只是在凝神静听微波粼粼的长江,讲述着数百年来纤夫们在江滩踩出的那条蜿蜒曲折的纤道、“古渝雄关”曾经的恢弘气势和历史岁月里发生在码头上那些波诡云谲的家国传奇吧。
江北嘴的重庆大剧院、南岸区的弹子石老街等地标建筑,华灯璀璨,但与江面上的热闹炫目相比,顿显黯然失色——同朝天门近在咫尺却隔江相望,与星空更是遥不可及,泛着曲高和寡般的冷清。
往小巷里插,一条路叫朝东路,距离“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来福士很近,但与大码头整洁的面貌形成强烈反差——路两侧搭着板房,兜售低价日化商品。
一条连接着滨江路的梯坎,比较隐蔽,路况也挺差,四周没有多少游客。
这条连接上、下半城的梯坎,是在陕西路干活的棒棒们的必经之路。从前那张感动了全中国的棒棒照片(冉光辉,手上牵着未来,肩上挑着责任,嘴上叼着自己),就是在这儿拍下的。如今的梯坎,仍有许多棒棒来回,以自己的劳动积累着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值一赚的小钱——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复制冉光辉的道路。
东西方向的小巷在南北方向生出更细小的里巷,里头是棒棒们的住处。
抬眼朝街道尽头望去,挺拔的来福士遮住了全部的视野,仿佛一种隐喻,两种生活在这里碰撞了:一种是在大街小巷吃苦流汗的生活,一种是在商圈里眼睛也不眨地买下几千元一条皮带的生活。
象征着财富与资本的大楼俯视着在霓虹灯下辛苦劳动的人,仿佛在说,他们的存在真是一种耻辱,没完没了地辛苦只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表现。
网络上,重庆也时常被嘲弄为“农直”(农村直辖市)——“城区很破,街上还到处是农民。”
有的人会为此感到恼火,但在我看来,我们根本没必要把这种狭隘而傲慢的评论当回事,因为重庆本来就是江湖的、平民化的城市,这也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有人以为这种满地赤膊的景观是“农村”特有,但其实不然。
每座城市都有勤劳、木讷地出卖着自己劳动的人——在其他城市,这些人通常是不能被看到的。
但在重庆,劳动者们被允许出现在街头,重庆人不排斥他们,反而将这些打着赤膊的挑夫视作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接纳下来。这种对底层劳动者的包容,并不是重庆的耻辱。
资本会以各式各样的手段暗示我们:“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就是有罪的人。”——而这并不是真的。
这些劳动者坚韧而木讷地出卖着自己,在这种行为里藏着的,是属于老重庆的,是来福士们无法替代的、值得尊敬的码头精神。
在我看来,努力工作,让每一天尽量充实,然后健康快乐地陪着家人,尽情享受余下的闲暇,这样的平淡,何尝不是另一种令人艳羡的幸福?知足常乐,即便此刻,只是静静地看着近前的江景,抑或来上一场穿越古今的神游,日子,已了无遗憾。
此刻,我正站在朝天门广场“重庆公路零公里起点”打卡点,夜色中的两江汇合处,宛若一方月牙形的墨玉,流光中的气息,温润而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