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春特刊|中国作家 薛毓文 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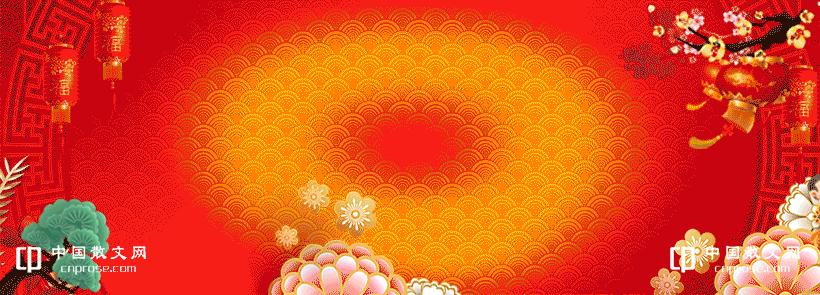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
—— 薛毓文 作品展 ——
作家简历
★
薛毓文 作家、记者、特约撰稿人(评论员),作品多次荣获国内、省内奖项并结集出版。近年来主要从事乡土民俗、生态文旅、经济社会领域主题的创作,数十万字的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山西日报》《山西晚报》等报刊及诸多知名网络平台。
难忘那碗腊八粥
不论离开家到外地上学的那几年,还是在县里工作的那些年头,每当年前回到家里,总能吃到母亲特意留下的一碗腊八粥,那一丝冬日里甜甜的暖意,瞬间将路途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乌有。久居省城后,回家的次数渐渐减少,但每当过年回去,那碗黏黏的粥还在,再后来母亲也不在了,那碗散发着淡淡谷米红枣香味的腊八粥便化作了记忆中的一缕乡愁,内心深处的一份思念的情结。这些年里,每逢腊八节前后,常常想起那碗腊八粥,有时想着想着就去商超买几罐八宝粥,偶尔也拿出食材用高压锅自己煮一点吃,但总觉要么过于甜腻,要么过于寡淡,全然没有那种炭火铁锅焖煮出来的乡间烟火味,也品不到亲人间那份深情的牵挂。
家乡的腊八粥中既没有各式各样的杂粮豆类,也不添加任何的香料糖分,极其简约,只需选取软米、红枣,以及山脚下挑回来的山泉水。软米还数当年的糜子用石碾盘碾出来的地道,糜子性软,生长期短,秋分刚过,熟透了的糜穗子便成孔成堆的摆上了打谷场,刚脱粒后的糜子湿漉漉的,需要在太阳底下晾晒保存,待到需要碾成软米时,先将其铺到生着火的土炕上,然后用席子覆盖三四天,等到可以用手两个指头捻出米来,便可以上碾子去碾。皮壳碾开后用扇车吹掉谷糠,剩下的便是黄澄澄的新软米。倘若用陈年的糜子,碾出来的软米看着没什么两样,但做成粥就泛起了乳白色,让食欲大打折扣。虽说家乡是著名的红枣之乡,秋风吹过,漫山遍野沟沟梁梁的枣树上到处挂满了红红的枣儿,但不同红枣品种的用途是有差异的,牙枣皮厚肉、酸甜利于着生吃,木枣皮薄、肉醇厚,利于熟着吃,即使同属木枣,阴凉地生长的的枣树结出的个儿大、硬度高、品相好,利于熬汤、做酒枣以及深加工成糖枣、蜜枣,当地人吃的枣糕、粽子、八宝粥中则选用向阳生长的树上熟透了的小红枣,这样的枣儿皮薄、肉酥、甜度高,持续蒸煮后呈褐红色,与软米相互成就,往往能呈现出色香味俱佳的独特效果。挑山泉水当然是孩子们的事,初七下午放学后,通往沟底窄窄的井道坡上,快速的跑步声、水桶的碰撞声顷刻间响成一片。水井很浅,不需要辘轳,用扁担上自带的钩子就可以把水提上来,井台上和井里边到处结了厚厚的冰,需要格外小心翼翼,但井内的水是有限的,如果抢不到前边,要么得排队等待,要么就得到较远的另一口水井去挑,而且据说那口井水的甜度稍微差一点点,会影响腊八粥的品质。每年这个时候去挑水,都带着大人们尽量挑好水的旨意,所以为此发生碰撞、争抢,甚至小的推搡也是常有的事,但为了追求一口地道的好吃食,也是为了表示堆节日的重视,家乡人年年如此,乐此不疲。
腊八节的凌晨,报晓鸡最后一次打鸣声刚过,天还黑乎乎的,家家户户的女人们便起来生火,整个山村弥漫着浓烈的柴火味。等我们起床准备去上学,锅里的水已经开了,母亲便将适量洗干净的红枣、软米依次放进铁锅里,然后不停地用铜匙左右翻炒。铁锅须选用尖底形状的,否则粥很容易烧糊粘锅,为了防止铁锈影响粥的感官,翻炒一般是不用铁匙的。我不止一次好奇地发问,那么一锅水中究竟放多少红枣和软米才算合适,母亲常常一边说着枣铺满水面即可,一边用铜匙做着演示:软米入锅烧开三五分钟后,将铜匙立在咕嘟咕嘟的锅中央,如果能立得住大约半秒钟时间,然后才缓缓地开始向一遍倾倒,表明比例正合适;如果铜匙立不稳,而且倾倒的速度很快,即需要再不断地添些软米进去,一直翻炒至炒不动为止,这时枣和米已熟透,满窑洞都透着诱人的香气,但口感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需要将锅端起,放到灶台后面温热的地方去焖,所谓三分蒸煮七分焖,待焖上两个多小时后,正是放学回家吃饭的时候,红枣、软米和水的融合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时的腊八粥既香甜,又柔韧,外加一碗白萝卜疙瘩汤,堪称绝配之美味。但在动碗筷之前,须先拿出一个盛满清水的碗,用筷子将锅中的粥象征性夹进去一点点,然后走出院门,朝着硷畔外的远山泼出去,用以表达农家人对大自然慷慨馈赠的感激与敬畏。
腊八粥不仅是美味的节日吃食,而且被赋予维系家庭和谐的美好寓意,所以也称“黏家粥”,意思是通过这碗看似普通的粥,可以把家庭的成员紧紧的粘合聚拢在一起,所以每年的腊八粥必须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吃得到,哪怕只是小小的一小口,都可令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开锅吃粥时,大人们是不允许孩子在锅里乱舀乱挑的,必须从一个侧面慢慢的来,尽可能将没有动过的粥留给节前回不了家的亲人。在没有冰箱的岁月里,腊八粥的保存只能依靠自然的力量,叫“冻粥”。先将腊八粥放入大点的碗或小点的盆子里边,然后再放在稍大点的容器,置于墙根下阴凉的地方,为了保持洁净和防止猫狗偷食,外面扣上一个更大的粗瓷盆。讲究人家冻粥,有时是根据在外的人数按份分开的,这样存取用起来更为方便。山里的数九寒天,零下二十多度,放进去的粥不久冻得比铁还坚硬。按照现代人的说法,这种就地取材的快速冷冻法是食品最好的保鲜办法,其实不只是存粥,冬天里存放鲜肉、馒头、饺子馅等的办法也大致如此。过完腊八就是年,腊八节后十多天,外出上学、务工的人们陆续开始返乡,回到家里的第一顿饭通常吃腊八粥。事先通过书信或捎话得到回来时间的大人们,为了让归来的游子吃上一口地道的腊八粥,一大早便做好了各种准备,提前把封冻的粥拿回家,慢慢消融两三个小时,叫“消粥”。倘若等不及直接上锅加热,不仅十分费时,关键是即使最后蒸热了,此时的腊八粥也过于稀松没嚼头,实在找不到原汁原味的感觉。那些归来就能吃到腊八粥的人们,口里含得是粥,而内心深处都知道,其实吃下去的岂止是粥,而是与家人相互守望的团圆、和谐与期盼。
一碗小小的腊八粥,甜蜜厚重而温馨,在不断变幻的时空中伴随着山村的袅袅炊烟飘过了千百年。如今的家乡,一茬茬年轻人迎着时代的潮流,已经将根牢牢地扎在了远方的城市,而村里的老人们依然保留着腊八节焖煮红枣软米粥的习俗,他们也依然会把那一份念想和爱留存在冰箱里或院子的某个角落,到时捧给年前回家的孩子们。也许他们孩子的孩子们早已喝惯了带着大江南北口味粥品,但老人们却依旧固执地坚守着,在他们的心中,再没有比家庭的和美更为重要的事,为的是让子子孙孙永远记住家的味道。有人说,对于漂泊在外的人而言,家乡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父母不在了,语言和美食便是家乡,而那碗晨曦中香气四溢的腊八粥,不正是深深刻在记忆中的家乡吗?
年 味
元旦过后,城里便到处充满了要过年的味道。家政服务的小卡片开始到处飞,微信里冷不丁就推送过来一则购买年货的小广告,进出小区的快递小哥比平时多了些趟次,喜滋滋地把满满当当的年货送到居民手里。尽管经济有些不如人愿,但商超里客流平缓的态势完全被涌动的人流取代,服装、鞋袜、金银饰品、灯笼对联前挤满了精心挑选的人们。4S店里,赚了点钱的顾客,都急着想添置辆新车,遇到货源紧缺,即使加点价也毫不吝啬,要的就是年前能够开回家方便方便,显摆显摆。差不多规模的饭店门楣上,早早打出年夜饭火热预定的广告,提醒着人们赶快下定决心把订金交了进去。搞项目的大小老板们电话一刻不停,脚步也不停,急赶着把工程款结算到手,好让那些风雨一年的兄弟们回家过年。而当真到过年时,城里反倒安静了许多。整夜里响不停的放炮声音没有了,奔波一年的新老城市人也携家带口早早的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有点钱财有点闲暇者乘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喧闹的城顷刻变得空旷了起来。除了门口贴满的红对联,以及扎堆在公园、影院、饭桌旁的人流,与平日差别无多,城里的年慢慢变得索然无味起来。
乡村的年味自然来得要晚,但较之城里,味道更浓烈,持续的时间也久。过完了腊八节,年的序幕才算徐徐拉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推年磨、做针线活是最具年味的苦活计。过年的吃食只能依靠老祖宗留下的石磨,常常天还不亮,各家的院子里大人们将麻绳系在磨杆前边拉,女人和孩子们后边推,凛冽的寒风中便传来嗡嗡嗡的声音,在静谧的夜空中彷佛一首命运的交响曲。那时的家庭人口都多,再加待客用,正月里又有不敢动磨的讲究,常常要准备下一个多月吃的白面、豆面、玉米面、高粱面。白面是极少的,能磨上三二十斤小麦的绝对算是村里上的等人家,普通家庭磨的多是玉米高粱面,而最难磨最费力气的当数玉米面,玉米颗粒大,石磨要先通过两三遍先将其磨碎成小颗粒,然后才能去磨成面,磨面的过程中小颗粒也坚硬无比,没有三遍五遍不能成为细细的面粉,所以磨玉米时往往放在推年磨的最后,全家老幼齐上阵攻坚克难。后来村里有了粉碎机,磨玉米便不再是心中的负担。大人小孩过年的穿着全靠母亲们的双手,衣服要靠手去缝,鞋袜要靠手去做,为了赶上过年穿用,她们在昏黄的油灯下熬走一个又一个黎明。最苦最累的是纳鞋底,那用浆糊一层一层粘了十几层厚的鞋底,需要一针一针带着麻线穿过去,一只成年男人的鞋底,少说也有四五百个回合,尽管有简易的辅助工具,但一只鞋底纳下来,手背上会出现好几条沟壑,有时还泛着血丝,但不能有丝毫的闲暇,马上换只手进入下一只鞋底,就这样忍着痛来回倒替着,为着是让全家人在大年初一早晨都穿上一双崭新的土工布鞋。对于孩子们来说,年味莫过于穿上新衣裳,揣上几个鞭炮相跟着去挨家挨户串门拜年。年三十的晚上,等他们熟睡后,母亲便将新衣服、新鞋袜,还有两毛压岁钱齐齐整整的放到炕沿边孩子们的枕头旁。即使是最爱睡懒觉的孩子,在大炮小炮的噼噼啪啪声中都会早早的从炕上爬起来,在反复嘱托大年初一不敢说不吉利的话音中,便不顾严寒相约几个小伙伴而去。最先要到的地方是去寻找没有响过的鞭炮,在放过的爆竹碎末中挨家挨户扒拉,总能捡到不少,然后放进衣兜,到谁家院子里,往火炉子里扔一个,啪的一声,就知道有人拜年来了,主人便掀起门帘,将一帮毛头孩子让进去,然后拿出酒枣和自己炸的油果子让吃。在有人在外边工作的几家,偶尔还能得到个水果糖,真是如获至宝,宁可让其受热粘在衣兜里也舍不得拿出来吃。大年初二三,村里的大秧歌出场,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锣鼓唢呐声中扭起来,尽情地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有文化的伞头总能即兴编唱出吉祥喜庆的秧歌,让人们在捧腹中津津乐道。随着闹上七天八天的大秧歌谢幕,年味也便渐渐的淡了下去,生活也恢复了常态。
当人们开始不再为衣食发愁的时候,乡村的年味也发生着悄然的改变。虽然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有的已娶妻生子,在电话那头一股劲讲什么都不需要准备,到时全家回来吃几顿饭、睡几晚上年就算过完了,但老人们总想着把年味传承给儿孙辈。他们说城里卖的油茶太腻,便用碾盘将自己种的小米碾成米面,然后放进少许的羊油,支起柴火炒出黄澄澄的油茶面,得让孩子们能够喝出年味,又说拌凉菜用的芥末油还是自家熏的味道正劲儿大,便将夏天收获的胡芥碾成芥末面,等着过年时用。女人们早已不再纳鞋底缝衣服,但总也闲不住的他们忙着为孩子们做着各种图案的鞋垫,在她们看来,城里一两块钱一双的鞋垫不舒服,所以每年底都要为回家过年的孩子们准备上两双。年三十晚上最具传统年味特色的垒火炉子自然是必须的项目,提前准备好百十斤上乘的块煤,单等到时再院子里将火炉烧得旺旺的,而这的确是孩子们的最爱。自从通上了电,煤的价格也飞涨,过惯苦日子的乡下人便将年三十家家户户垒火炉子的习俗改为院子里拉上一颗电灯泡,但只要有子女从外地回来过年,火炉子是必须要垒的。除夕晚上只要看到谁家院子里点着火炉子,人们马上会说人家的孩子们过年回来了,而那些孩子们没有回家过年的老人,只能在睡觉前黯然地拉下电灯的开关。后来我常常想,乡下的年味,其实最重的还是人气,是烟火味,随着乡村人口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又忙于生计不选择回家过年,乡村的年味也越来越变淡,失去了传承和吸引力,单靠老人们的守望是远远不够的。
烟花爆竹自然是年味的灵魂,燃放过后那股清香浓郁但有些微微呛鼻的火药味,那才是真正过年的味道。后来禁燃,虽然从极远处偶尔能零零星星听到一点,但远形不成气势、形不成氛围,感觉到似乎欠缺了点什么。年前,深知我恋旧的兄长年前都要寄来些他自己制作的烧肉丸子、恶,以及甜甜的酒枣,村里的发小们会发些充满年味的短视频。每年正月,都要带着孩子回去祭祖,有时扭几步大秧歌,顺便找寻着儿时的年味。虽然今年有些特别,孩子们有的忙着照看小孙孙,有的远渡重洋去做访问学者,但我和爱人一定还会回去的,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乡间年味早已流淌在血液里,而下一代,我想自然也会有她们对年味特殊的记忆方式。
乡厨乡宴
家乡大大小小的红白宴席上,多少年来都活跃着一支乡厨队伍,用他们不太专业的厨艺,粗犷而略显苯拙的服务,满腔热情地满足着八方来宾客的味蕾,了却着主人们发自内心的心愿,不知不觉中演绎传承着乡村宴席的文明音符。
乡厨是一个群体,既有见过些世面,有点做饭技艺的掌勺师傅,也包括勤快不惜力,乐于助人从事生火、盥洗、跑堂的打杂服务人员。前者专业性相对较强,能够被大家公认为大师傅的掌勺乡厨者往往一个村子或几个村子就那么两三位,需要办宴席者提前去邀请,后者则多由家族里边的晚辈们组成,以互助为基本的组织形式。乡村的宴席看似简单,但因蒸烩烹炒从选材到成品都需要乡厨们亲力亲为,是非常辛苦的一件差事。乡宴中最复杂的当属蒸的环节,宴席有三蒸,即蒸馒头、蒸糕、蒸恶。蒸馒头需在早两三天就将面自然发酵好,由于笼屉层数少,为了避免浪费,宴席上的馒头个头不能不,一斤面须做到八个以上,遇上上百人的大宴席,从早到晚蒸上一整天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有时还得挑灯夜蒸,蒸完最后一笼馒头,初出道的乡厨们胳膊都会红肿,即使老乡厨也累得蹲到地下需狠抽几袋旱烟提提神;蒸糕是宴席早饭必有的固定程式,也极考验乡厨们的功力活计。软性的糕面需拌得稍干点,成圆形小块状即可上锅,如果糕面硬,则需拌得软和些才行,否则蒸出来的糕就成为窝头,客人不爱吃,是天大的失败。糕要蒸好,还需要火力旺且均匀,乡厨间上下配合协调很重要,否则糕会夹生,被视为大不吉利。尤其是冬天蒸糕,支在院子里的敞口大铁锅一边蒸汽突突地冒,一边还要均匀地将拌湿的糕面一层层均匀撒进去,蒸汽打着臂膀,眼睛还得掌握锅内的成色,没有一定的力道是很难办到的。恶是吕梁山上几个县份独有的吃食,也是乡村宴席上大烩菜中的灵魂性食材,需要先将土豆或胡萝卜蒸熟,然后抿成泥状,与土豆淀粉和到一起,将红皮大葱、花椒面、食盐等和在一起,然后用手拍成一条条的放进大锅内蒸四五十分钟,为了防止受热后倒伏,中间多用一节一节的高粱杆隔离开。
乡宴是露天摆放的,就像乡村的电影都是露天演出一样。谁家有长圆桌子,谁家有多少凳子,乃至谁家有多少碗碟酒壶酒盅乡厨们都了如指掌,统统的拿来院里院外摆好。酒是杏花村、吕梁山或太原高梁白,但多是散装的,图得是便宜,后来假酒泛滥,渐渐改为了瓶装。下酒菜一凉一热,凉的就叫凉菜,如今在城里老乡饭店都挂家常凉菜牌子,土豆丝、绿豆芽、细长的土豆粉条以及切成细条的油炸豆腐,倘若在夏秋之交,外加一些黄瓜片。如此简单的食材,在乡厨们用葱姜蒜盐醋胡芥末等调料的加持下,呈现出绵延千百年的人间美味。冬春时节的热菜以土豆粉条和油炸豆腐块为骨架,再烩进去适量的白菜、恶、海带丝,夏秋的宴席热菜则多以豆角、西葫芦等鲜菜为主力,与上述食材烩为一锅,就上事先蒸好的热馒头,成为一场宴席完美的压轴大戏。吃完了这碗烩菜馒头,宾客们便陆续的褪去,忙碌了几日的乡厨们才稍稍松口气,拿张桌子坐在一起,在主人的道谢声中相互斟满一盅酒,祝贺着宴席的圆满成功,同时也期待着下一场宴席再相逢。
随着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潮的兴起,农村渐渐呈现空心化的趋势,曾经活跃乡村千百年的宴席班底也不再生活在村里,虽然需要时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会放下手头的活从千百里之外返回来,但毕竟费事了许多,而且会耽误外边的工作。再后来,人们的日子普遍过好了,乡宴的规格也不再满足于一凉一热的低档次,至少需炒上六八个炒菜,有的甚至鸡鸭鱼都得上,对传统乡厨手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他们业余的技艺显然满足不了来宾们日益增长的高水平胃口,于是专业化的乡厨服务组织应运而生。这些新乡厨们瞅准了乡宴的巨大商机,主厨通常从事过餐饮业,外加几个服务人员,一辆大篷车、一顶安席的帐篷、一套完整的灶具餐具,虽然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服务费用,但这种专新业态的出现既省却了办宴者不少麻烦,又足以表达他们款待乡邻的心意,成为办乡宴普遍选择的方式。
时光变迁,乡厨更迭,永不生变的唯有乡宴中那浓浓的乡音乡味。冬日的暖阳下,去参加一场非去不可乡宴,一口略显咸涩的乡味土菜,一杯清香浓烈的乡味土酒,一声粗声大气的乡味问候,可让远离故土的心灵享受在当下,也可将过往的记忆拉得悠长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