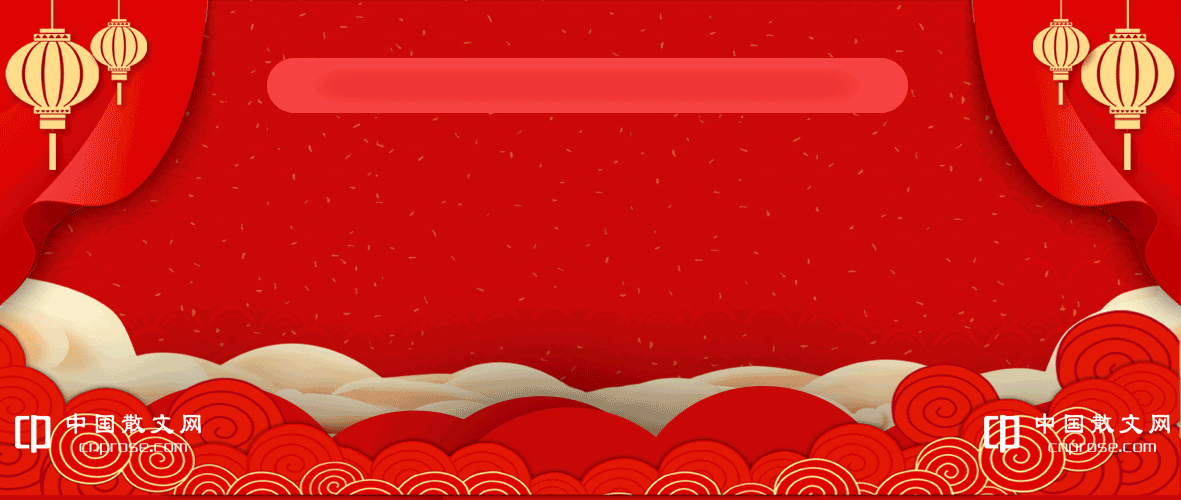【新中国75周年特刊丨当代作家 丁兆鸾 国庆作品展】
当代作家
丁兆鸾 国庆作品展
作家简历
ZUO JIA JIAN LI
丁兆鸾 女,笔名柳涵,生于1953年2月。曾当选霍邱县第九、第十次人大代表,获过县委县政府嘉奖,获过“三八红旗手"奖章。1987年读文学函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国画,书法等。2012年开始在霍邱网站,黄山在线,中国散文网,中国诗书画家网,搜狐网等发表散文诗歌等。辞条入编《中国艺术风采人物辞海》《中国当代杰出文艺家大辞典》。文学作品在今日头条,都市头条等发表。文学作品获过一等奖,特等奖等。书法作品获过二等奖、三等奖等。
祖国万岁
国庆作品展
GUO QING ZUO PIN ZHAN
柳情依依
柳,没有林逋爱的梅那么高洁,没有陶潜爱的菊那么傲霜,没有濂溪爱的荷那么出污泥不染……
柳,自有柳的品格,柳的风韵。
春来了,她穿上一身绿装,把万紫千红的众芳衬托得更艳丽,春色更怡人。
到了冬天,她卸下盛装,把它化作养料,让翌年草木繁荣花更美。
有时,她伴着微风轻舞,有时,她静靜伫立,默默注视水面一一不是自我欣赏,不是顾影自怜,而是把清莹莹的水面当作镜,照照自己有无瑕疵污洉,暴雨来临,尽情洗涤,风雨过后,更加葱翠。
贺知章赞柳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枝垂下绿丝绦”,白乐天的“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更耐人寻味,意趣横生。可见古人也很赏识柳的风情韵致。不过他们大都从审美的角度或是烘托气氛才吟咏她的,往往不注重她的价值和美德。
柳,不仅能点缀风景,绿化环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她的价值和美德在于从不挑拣肥瘠,天论把她砍作几段,插在何方,只要有一抔黄土,她就在那里生根开花,生机盎然,为那儿留下一片绿荫。当人们需要,她又把枝身献出,做燃料,做各种物器。
柳,有白杨的伟岸,却不是白杨那般高傲骄矜,一味向上看,柳,既仰视苍穹也俯首大地。当她肃穆靜立时,呈阳刚之美,当她款款起舞时,又婀娜多姿,情态万干,似妩媚的少女。
每当望柳遐思,我不禁联想到这里世代劳作的农民,他们的品性也似柳一一平凡而伟大,扎根贫瘠,默默繁衍,默默奉献,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汗水付于春夏,喜悦获于秋收。春来为大地披翠,秋到为人类积金。在求自我生存的同时,为人类创造了财富,创造了美。
但愿,勤劳的农民和我眷恋的垂柳,在告别多雪的严冬后,迎来更明丽的春天。
西湖秋韵
裹在涌动的人流中,放纵着驾驭不了的双眼,左右张望。
西子湖边的山山水水,记不清我看过几多遍了,只是每次游赏总还像笫一次身临其境,总也看不够。
这段时间,总惦记着湖边溜溜,看看暮秋初冬的湖山易容换颜的模样。今日方才付诸行动。
湖边可意的场所,有吹的拉的,唱的舞的。我看一眼便匆匆离开。
游人双双对对,牵着扯着,还有成群结队的,指指点点,笑语欢歌……
看看女性着装,虽千奇百怪,但下身的装束大同小异:要么薄的不能再薄,要么瘦的不能再瘦,就是大腿和臀部是一目了然的……
偶然,生一丝淡淡的凄然,热闹中的孤寂。
走累了,湖边坐坐、望望:对面宝石山上的保俶塔巍巍然耸立在蓝天苍穹之下,青山绿树之上。对面名气满满的雷峰塔,与其隔湖相望。这么看着,心中涌出四句:
雷峰山上憨老纳,
保俶美女恋着他。
俩俩望穿一湖水,
问谁能把鹊桥搭。
骄阳艳丽,晴空万里。时令虽已入冬多时,气温犹如阳春三月。不过,冬的脚印已涵盖漫山遍野,打破了以绿统治山河的局面,把金黄橘红涂抹在山山岭岭、湖边路旁的树枝上,为湖光山色添些斑斓,把单一的绿、组装进多种色素,以象征着秋的黄为主色调了。
从树上悠悠然飘下几片梧桐的叶,这种落叶随处可见,俯拾皆是。这该是上帝撒在人间的奇妙文字,让识得人拣起组成染着秋意冬韵的诗篇。
垂柳呢?像迟暮的美人,还碧滢滢的,或袅娜的舞着,或端雅的垂着……湖中的荷,满目焦黄了。偶有几竿绿着立着的,也似年过七甸的阿姨一一留得残肢听雨声了。
有棵枫树,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棵。片片红叶,没一点杂色,布满一树的枝枝杈杈,像巧手的染匠精心染制的,浓烈密致,每一片红叶都是整齐鲜美的,每一个角都是平直水灵的,没一点焦枯的痕迹。少男少女们云集其下留影……
西湖山水的万种风情,我的笔,太拙……
双庙小学变迁记
双庙小学的校名来源于当地的一处古迹。人称“庙里有庙"。不知始于哪朝哪代,何人所建,也不知毁于何年。但确是载入地方志的。早年还可见庙址处瓦砾狼藉。
小学校几经搬迁,以上略记。
到我入学那阵子,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我们家的庄宅被政府征用为双庙小学的校园。我的一年级是在自家的房舍里念完的。
当时,全校有一至六年级六个班级。学校有操场蓝球架等体育设施。老师都是国家分配来的正规师范毕业生。双庙小学也是全乡三所公理小学之一。
那个时候全乡还没有民办小学和民办教师。
第二年,公家占用的民房归还了房主,小学校迁到人称老油坊的地方。我们家又搬回原址。
不到一年学校从老油坊搬迁到往北一公里处大队部去了。
之后又过一年,学校又是抬桌子搬椅子,再次迁回老油坊。政府给我们盖了新的校舍。仍是一至六年级六个班。附近三个村(当时叫大队)的孩子都到双庙小学念书。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能进学校读书的不多,能念个初中毕业都是有工作安排的。
这段时间里,学校有了小小图书室。《中国青年》,《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十万个为什么》……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染上了书瘾,走着看坐着看吃饭看睡觉看上课了还看……
在这片校园里,我读完了小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和全国一样,停课,复课闹革命……
时光荏苒,我初中毕业了。大队领导安排我在双庙小学代课。我从这个学校的学生变成了这个学校的教师。同事都是我的小学、初中老师。
没过多久,我被辞退了。
原因是:我父亲的舅舅解放前在傅作义部下为官,他是黄浦军校最后一批毕业生。解放后他解甲归田,妻子离异,他孤身一人一直住在我们家。
在我毕业之际,正赶上他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当时全县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批判声讨他的团伙一一“豫皖边区反共独立团"的罪行,(其实莫须有。后无罪释放)
我走出双庙小学没两年,小学校再次由老油坊北迁至原大队部。只是大队部已搬到别处去了,只剩下双庙小学了。
政府又重新给孩子们建了新校舍,由原来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
时间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再次进入双庙小学任教。只是,双庙小学己在文革时改为联合小学。邻村的孩子都在本村念书不再到原来的老学校来了。各村新办的小学当时叫民办小学,老师也都是本村安排的民办教师。
学校原来的教师有的退休了,有的在文革后各奔东西,不知去向了。这个时期的同事几乎都是乡、村两级安排的民办教师。
又过若干年,我因为没有教育局的任用证再次走出村小学。
十多年前,我从外地打工回村。
小学校又从原来的地方西迁几百米建了新校园。新校园面积比原来的学校大好多,搡场也大,蓝球架,乒乓球桌,食堂门卫室全都有,一切焕然一新。
每当上学放学之际,学校大门外,接送孩子的家长排满一大片,熙熙攘攘,络绎不絕。学校里的琅琅书声,老远就听得见。
到了近年,小学校门可罗雀,接送孩子的家长逐年减少,只到全校仅剩三名学生。
这些孩子有的随同父母去了城里,有的转学到镇上小学去了……
每当看着冷冷清清,甚至有点荒芜的曾经的双庙小学,心里总是五味杂存:
曾经,那么多孩子上不了学,上学了又没有教室安身,
那个时候一个教室里坐着两个年级的学生,老师教完一年级又教二年级,名曰“复式班”。
现在,校园这么大,教室这么多,这么漂亮,并且也不受寒窗之苦,炎热之苦了,又没有几个孩子在里读书了……
热烈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