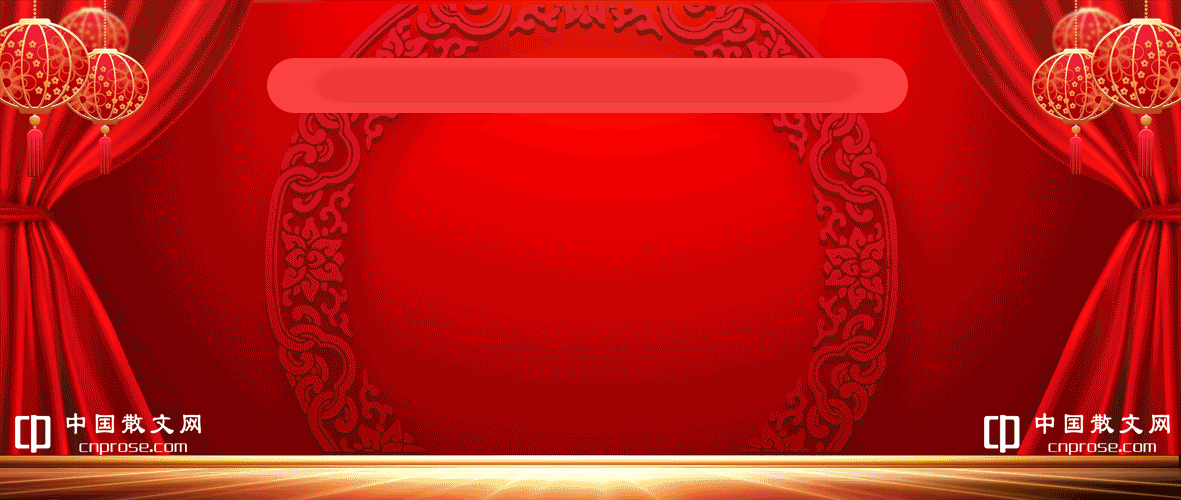【2023国庆特刊丨当代作家 张朝金 作品展】

艺 术 简 历
张朝金,笔名今朝,“文学之乡”商洛人。系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天津散文研究会会员、西安作协会员、未央作协理事。中华作家网签约作家,中国乡村人才库作家,中国作家网会员。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在军地省(军)以上刊物、知名微刊发表作品500多篇,部分作品获奖。
作 品 展 示
我的“手表梦”
1979年,改革春风徐徐吹来,吹遍了山乡田野,“人勤地不懒”的古训,应验了那个时代,生机勃勃的庄稼竞相疯长,昔日瘦骨嶙峋的山山峁峁、沟沟洼洼渐渐长高了、长满了、丰腴了,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山变了,水变了,人也悄末声息地变着呢!
年轻人头上、脚上、手上、腕上,最先起了变化。小姑娘别上了五颜六色的发卡,仿佛五彩缤纷的蝴蝶闻香而来,爬满了青丝,妆点着一头乌发。鬓角处一只艳艳丽丽、粉嘟嘟的蝴蝶最为惹眼,不由让人多看一眼。姑娘长长的辫子末梢处,别一只蜻蜓,走起来一摇一摆的,蜻蜓跃跃欲飞似的,叫人忍不住想抓一把呢!小伙子骄傲地蹬上了象征着光荣与梦想的“解放鞋”,个个英姿飒爽,走起路来发出“嘎吱嘎吱”脆响,听起来非常带劲。穿上它,既不怕冰雪,又不怕风雨,小伙子们可以肆意地奔跑了、跳跃了、撒疯了,好不开心哟!
渐渐的,女娃们脖子上系上了花花绿绿的围巾、纱巾和装饰物。有火红火红的,像一团火;有翠绿翠绿的,像一汪潭;有洁白洁白的,像一朵白云......,脸脸儿被衬得如烂漫的花朵,美极了。男娃们或迟或早地换上了时下最流行的、柔柔滑滑的“的确良”衣衫,风儿鼓起时,吹得衣衫突突突直颤,心里哪个美呀,真真舒坦。
然而,谁也美不过发展叔,仅他左腕儿上的钟山牌手表,就让人垂涎三尺了。
发展叔在县城工作,是村里最先戴手表的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手表,是一个临近黄昏的傍晚,夕阳西照,金灿灿的。他下了公路往回走,左手甩得老高老高的,好像印度士兵踢着正步,夸张地摆着双臂。手腕扬起时,一道亮锃锃的金光,明晃晃的,耀眼得很;手臂下垂时,一道白光划成弧线,像一条银龙,围着他的周身绕圈,我看呆了。
半晌,才回过神来,前后脚跟着进了他家。
“叔,发展叔!”一进门,我就亲热地叫。
“谁呀?啥事嘛?”他满不在乎地回应一声。
“是我,想看看您的手表哩!”我直截了当的回道。
“手表有啥看的?”他不耐烦的样子。
“叔,好叔哩,看一下嘛!”我哭腔央求着。
“好吧,小心弄坏了,贵着哩!”他不放心地安顿一声。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手表,放在手心儿,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手表,紧张、兴奋、喜悦,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不时看看表罩,摸摸表链,听听指针“铮铮铮”悦耳的声音,又试试带到自己手腕的感觉,感慨良多,心想:“啥时候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呢?”
发展叔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宽慰说:
“我看你是戴手表的命,将来会有的。”
说着,拉过我的手,有根有据地描绘我的手相,说是隐隐约约看得见手表印印呢!我信以为真,生怕手表印印消失了去,赶忙回家,用彩笔在印印处精心画了一个手表模样,远远看去,好似真的一样。我还美了好一阵子哩!
如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小康社会全面实现,手表已经普及,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寻常物件:从几元到几十元,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价格不等;从机械表到自动表,从运动表到智能表,功能齐备;从防尘表到防摔表,从防水表到夜光表林林总总,极大满足着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
我的“手表梦”早已实现,不仅有了比发展叔当年更好的表,还有功能齐全的机械表、石英表、电子表、智能表等等等等,非但能看时间,还能打电话、发短信、拍照和监测身体健康呐!
让我们盛赞这个时代吧!它给了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暖和爱。
从陕南到陕北
秦岭,因“秦”而得名,东西绵延八百里。秦岭的南边有陕南,秦岭的北边是陕北,关中平原居中,“聚宝盆”似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被奉为“龙兴之地”。
我出生在陕南,十八岁从军入伍赴陕北,如一朵孕籽儿的柳絮,从南漂到北,在那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了一个小家庭。陕南有我的娘亲,陕北有我的妻女儿。几十年里,我在陕南陕北生活着、工作着、穿梭着,蜜蜂般忙忙碌碌,来来回回编织着幸福的小日子。
从陕南到陕北,要穿越茫茫秦岭、关中平原和沟壑从横的黄土高坡。“蹲俑”似的陕西版图,每年我要从脚心走到头顶,再从头顶返回至脚心,候鸟似的往返迁徙,纵贯三秦大地。常常出了南山又进北山,出了北山再进南山,出出进进不知多少回,亲眼见证了“绿美陕西”的蝶变新生。
从前,人们“靠山吃山”,伐木取材、砍柴取火、开荒种地......,生活所需取自山里。年复一年,山山峁峁似剃过的秃瓢儿,光秃秃的。
出南山,只有依靠班车的四个轮子。人虽然是走虫,却难以逾越绵延不绝的丛山峻岭。全县每天通一趟班车去山外(山里人把出山叫“去山外”),购票比登天还难,购得一票,如同中奖一般高兴。班车不大,超载在所难免。车内拥挤不堪,腿脚插秧似的,动弹不得。从县城出发,400里山路,如同一条疙瘩啰嗦的麻绳,弯弯曲曲,坡路陡陡的、窄窄的、险险的。有时在天堂,有时在地狱,人人攥紧一双拳头,捏了两把汗水。车轮卷着尘土,仿佛点着的开山炮仗,在岭凹里燃着一条羊肠小道。倏的,车子淹没在浓烟滚滚的灰土里,钻天猴儿似的。一会儿,在云端岭巅攀爬;一会儿,又在深不见底儿的狭沟颠簸,七上八下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
常言道:“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人就有多高。”仰望南山,处处斑斑点点住着人家,或一家独院儿,或三五一簇,你家南山,我家北坡,各自占领生存的领地。人进山退,长年经受刀砍、斧凿,䦆挖、锄刨,山已体无完肤,支离破碎。一座座山峰,孤孤矗立,像一个个伤兵,不是这儿一块溃烂,就是那儿一块蜕皮,处处伤痕累累。
进北山,更为艰辛,车子趴地虎似的,在黄土洼里从黎明转到黄昏,仍然转不出黄土地的一道道皱纹。窝头似的土丘,大的大、小的小,胖的胖、瘦的瘦,像一群衣不遮体的难民。山头土梁梁上,“受苦人”(当地称呼农民为“受苦人”)犁成螺纹似的梯田;山腰崖畔间,野生了一圈儿羊儿吃不到嘴的酸枣和野刺玫;山脚低洼处,横七竖八排列着各式二样的土窑洞或地窨子(储藏菜蔬的矮小窑洞),仿佛一群谢顶的陕北老汉,腰间系一根儿草绳儿,脚下蹬一双破了洞洞的土布鞋,挤在一起诉说着日子的苦焦呢!
偶尔,山的皱褶里,有一两孔像样的窑洞,石板砌的墙、砖头罩的面,青瓦翘的檐,金黄的玉米棒子鱼鳞似的爬满了墙,一群羊儿漫山遍野扫荡刚刚冒尖儿的青苗苗儿,令人惋惜。
后来,人们不满足于“靠山吃山”的日子,不屑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日”的生活,梦想着开山采矿,实现“一夜暴富”。于是,掀起了“向大山要票子”的热潮:南山的金、钼、钒,北山的媒、气、油,就像大山的血液一样,“汩汩汩”地往外流。一座座大山被“开肠破肚”,一口口矿井被“摘心挖肝”,一路“大开挖”,一路“大开发”,处处满目疮痍。
有钱啦,又是一轮儿“别墅热”,森林资源锐减,生态功能下降,青山绿水不在。
这十年,三秦儿女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秦岭生态环境优良等级达99%,黄土高原成为全国增绿幅度最大的区域,陕西版图由浅绿向深绿不断迈进,绿色水库滋养着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态陕西”美丽画卷成为卫星云图最醒目的一片“绿洲”。“氤氲绿树多,苍翠千山出”的景色,惊艳了世人的眼球。
陕北的“春”。藏在陕北黄土高坡褶皱里的“生态明珠”,正以她嫩嫩的绿、浓浓的情诠释着“春”的盎然。一片片绿叶翩翩起舞,一树树绿枝婀娜摇曳。从“雨涝流泥浆,冲成万条沟,肥土顺水走,籽苗连根丢”,到“层层梯田绕山梁,座座坝堰锁沟掌,绵绵峰峦碧水漾”,背后是陕北儿女矢志不渝坚守的“绿色梦想”。作家用诗的语言赞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陕南的“秋”。秦岭的秋尤为热烈,是铺展在祖国腹地一幅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立体山水画。习习秋风、沥沥秋雨、炎炎似火的秋叶,酿造了一坛坛醇香飘逸的美酒,醉倒了秦岭南北一座座山峦奇峰,到处都是令人心醉的美景。
如今,“三纵七横”路网四通八达,从陕南到陕北,朝发夕至。条条高速,处处都是风景。任你随手一拍,说是“南国水乡”,绝对不会有人怀疑,一定会成为网红打卡地。
泉
在我的家乡有一眼泉,模样丑陋,寂寂无名。它既不像革命圣地南泥湾的九龙泉,滋养过三五九旅革命战士的身心,成为闻名遐迩的“革命泉”;也不像道教圣地楼观台的化女泉,千年传唱“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神奇传说,成为道文化的“神泉”;更不像黄河母亲怀抱里的处女泉,“泉涌沙动,如绸拂身”,成为去病健身的“养生泉”。《县志》找不到它,百度搜不到它,“旅游景点”也没有它的身影。
它,时而清澈,时而浑浊,不时还会涌出一些腌臜的东西,让人恶心;它,时而甘甜、时而苦咸,牲口也受不了它的刺激;它,时而生硬、时而绵软,常常泛起一层层白花花的盐碱,浇地会使土壤板结,庄稼也没了精神。
当地群众厌恶它:用土填过,用石头堵过,还用炸药包炸过,无济于事;又试图引水改道,不让它注入地里、溪里或井里,亦是徒劳。唉,惹不起躲得起嘛!村民只好背过它,绕开它,在泉的上游取水,信由其自生自灭吧!
它似乎跟这个世界无任何瓜葛了,人也不疼了,畜也不爱了,自个寂寂寥寥、无休无止地淌着、淌着、淌着......。
据老人说,这眼泉,是一条修行千年的海怪在海底挠的一个洞,通着海呢!海水暴涨时,如同山洪爆发,浊水喷涌而出,不仅会涌出海上漂浮的垃圾,还有尺把长的鱼虾喷涌而出哩!海水安澜时,泉水也会清澈碧绿,涓涓滴滴,如泻万斛之珠,清澈、甘甜、冰清玉洁的呢!
当地人流传:“碰到清泉会走好运的,碰到浊水会走霉运的”。川道人进山谋生,每常驻足观看,预测自己进山的运气:若遇泉水暴涨,浊水横流,就会打道回府;若遇泉水舒缓,叮咚悦耳,甘甜如怡,就会欣喜万分,虔诚地捧一把泉水扑到脸上,祈愿自己进山能够顺顺利利,甚或奢望挖一颗千年人参,发一笔横财哩!
终于有一天,一群地质队的后生进山勘探,扛着“长枪短炮”路过这里,人困马乏、口渴难耐,发现了这眼泉。恰巧,这天泉水清澈见底,甘美无比,吸引了他们,几步开外就能嗅到一股沁人心脾的甘润,一群人围着泉眼儿不走了、住下了,测呀、量呀、拍呀、照呀地折腾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不几日,又派来一拨增援的,拿着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装呀、灌呀、摇呀、幌呀的又是一通折腾,再将不同颜色的“佐料”放进长颈瓶、大肚瓶、长条瓶、方型瓶、菱形瓶等不同形状的仪器里,左摇摇右晃晃,登时,各种仪器变成了五颜六色。一致的结论:“这眼泉是宝贝!”
他们说:山里的宝藏是黄金,泉里的营养赛黄金。泉水有人体需要的钾、钠、钙、铁、锌、钼、硅、硒等二十多种微量元素,珍贵得很。
月余,大队人马开进,轰隆隆的机器声昼夜不停,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开发宝藏,造福人民”“大地乳汁,饮育优秀儿女”“千锤万击出深山,喝得健康在人间”等让人眼花缭乱,使人不敢相信。
山里人很诧异:这么不起眼儿的泉,咋会成了“宝贝”呢?他们更不敢相信,它还是通了海的,通向山外的世界呢!它漂过洋,过过海,见过世面,走过五湖四海;它涵养过地球、滋养过人类呢!它走到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生命、生机和活力。它落寂了,在深沟里、荒草里、乱石堆里默默流淌了百年、千年,亦或是万年都不止呢!
山民不解:它咋一下就“宝贝”了呢?它可是一无是处呀?
“它看起来,是一无是处”男地质队员说。
“这正是它不同凡响的地方啊!”女地质队员感叹道。
“它是在默默蓄积能量呢!”领导模样的地质队员深有感触地说道。
是啊,不经过千激百撞,万年蓄积,怎会富含那么多宝藏?当然靠一朝一夕是难以成就的。它不仅仅是供人饮用的生活水,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浇灌水,它大器沉稳,不愿显摆自己,更不会张扬自己,自然会遭到白眼、非议和攻击,甚至弃之如敝履,恨之如仇敌,想着法儿破坏它、毁灭它。面对山泉,我们惭愧了。
山泉开发了,我们富裕了:梦想“村村通马路,户户铺柏油,家家住上小洋楼,出山只需一脚油。”成为了现实,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乡村,成为“人世间”最美的风景。
2023国庆特刊征稿启事
请添加办公微信13681238889,将您的20首诗词(新诗共200行内)或3篇散文(共6000字内)、简介、照片传来。传前请仔细校对好您的简历和文字,确保准确无误。10月31日截止,依次在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重磅推出。
联系电话:010-68688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