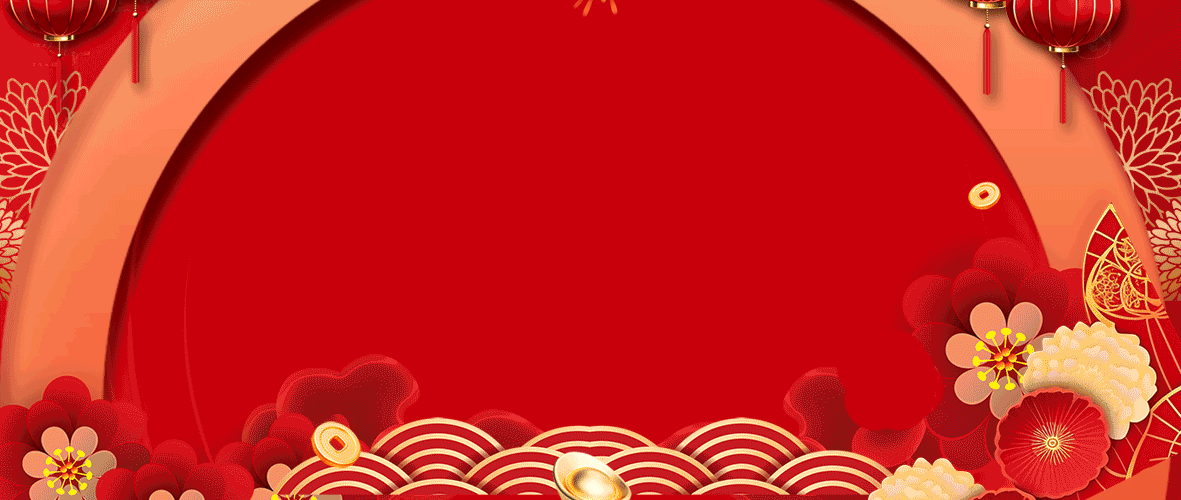【2025新春人物丨当代作家 王 杰 作品年刊】
2025新春人物
当代作家 王 杰 作品年刊
2025新春人物简历
XIN CHUN REN WU JIAN LI
王 杰,中国散文网会员、青年作家网特约作家。河北怀安人,中共党员,国企管理人员,一直从事水利管理工作。工作闲暇笔耕不辍,将从日常中获得的感悟以散文、诗歌、小小说、中篇小说进行艺术化表达,积累了30多万字200多篇作品。从2023年11月底开始投稿,参加文学赛事,2024年11月底加入美篇,目前有20余篇散文、小小说、诗歌发表。有多个作品在全国文学大赛中获奖。在美篇作品阅读量80多万,作品加精率83.5%。
作 品 年 刊
ZUO PIN NIAN KAN
父亲的菜园子
小时候,我爸爸哥四个和我爷爷奶奶挤在一个院子里,前后两排9间房,每家两间,爷爷奶奶一间。前两排住着大伯二伯两间,东侧是走廊。后排住着三伯、我家和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住在西北角最僻静的那一间。房子都是石头墙,墙上地下空洞相连,是老鼠的乐园。露头的椽头已经腐朽了一半,感觉比我爷爷还老,勉强支撑着覆泥的屋顶。每家的院子大概五米宽十米长,扣除厕所、猪圈、鸡舍、兔窝的占地,大概有二十平米可以作为菜园。
每年春天,我父亲早早地选一捆粗细均匀的葵花杆,用刀剁成齐长,挖沟把葵花杆均匀栽到空地的四周,然后用略细的葵花杆作为横杆,用麻绳将横、竖杆紧紧绑地绑到一起,方方正正围城一个精致的菜园子。然后灌溉洒肥翻地,形成肥沃湿润松软的土床,东西向用耙子耧成四畦,一畦种西葫芦,一畦种白菜,一畦种黄瓜,一畦栽西红柿。那时候食难果腹,能吃的蔬菜又是稀罕之物,种下去就成了我呵护的重点,我就急切地盼望他们快快生长,快快结出碧翠的黄瓜和红红的西红柿。每天早晨一起来就蹲在园子里看看长出来没有,是不是缺水了,黄瓜怎么长的那么慢呀,西红柿怎么还是个小绿球,后来黄瓜长到二十多公分长了,西红柿也白中微微透出了红,我就问我爸能不能吃呀,他说还不能,黄瓜还可以长十厘米长,西红柿红透才可以吃,我每天耐心等呀等,有一天我父亲说应该能吃了,去摘吧,可到园子里一看傻眼了,早已被人捷足先登了,我们共叔伯姊妹十三个,都塞在那么小的院子里,原来不知道有多少“黄雀”在后面盯着呢,我和弟弟哭着告我爸,我父亲挺后悔但从不发脾气,一来是他性情温,二来毕竟是吃的东西,何况也不是外人偷吃。我母亲也特别宽厚,不好意思追查,就唠叨我爸:你不知道院里这么多“狼”,让孩子吃了倒行了,非要长长红透,现在怎么样了,傻了吧,明年别种了…。说归说,第二年该种还是照种不误,呵呵。
参加工作后,我开始住单位宿舍,没有地方种菜,但可以在门前的砖缝中种花,那花特别给力,长的郁郁葱葱,秋天成了一小片花园,给简易的家增添了别样的情趣。
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院子不大,硬化房子的时候特意了十几平米的菜园,每年春天早早地在菜园周边垒砖填土种花,在园子里种满西红柿、黄瓜,秋天瓜果飘香,看着孩子们随意摘着吃,我总悠然想起老家那个小院子,想起父亲菜园子里总也长不长的黄瓜和永远也红不透的西红柿。
孩子们长大了,秋收后,儿子就建议种小葱。一到春天,女儿就建议种韭菜。我虚心接受照单全收,然后全家总动员落实。现在丰衣足食,他们对秋天能吃上鲜黄瓜鲜西红柿没有多大兴趣,就是希望院子里早早有绿色,用我女儿的话说就是能早早迎接春天。
现在那个曾经的小院子早已归公,栽满了挺拔的油松,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如离巢的鸟飞落到祖国各地,这么多年来我几乎吃遍了祖国各地的瓜果,但最香最好吃的还是父亲菜园子里总也长不长的黄瓜,和永远也红不透的西红柿。
父亲的手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15年了,曾经的伤痛,渐渐地被匆匆的岁月扶平,父亲慢慢地淡出我们的思绪,成了一片片美好而又苦涩的记忆。记得前几年,每年清明我常常难以自已地想起我的父亲,几乎每年都写一篇祭文,表达我一缕缕悠悠的哀思,后来慢慢地就没有多少感觉了,长篇的祭文变成了简短的日记,剪短日记变成了偶尔的回忆,偶尔的回忆变成了与妻儿踏青觅春,追寻春天的脚步。
我的父亲特别爱我们,他的爱细腻宽让,公平和气,让人很亲近很陶醉。小时候我常常摸挲父亲的手,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作,我父亲的手指很粗壮,倒是比较均匀,手掌手指都被老茧覆盖,厚厚的硬硬的一层,很厚重很踏实。而这双看似笨拙的却异乎寻常地灵巧,能做出比别人精巧实用的玩具,不仅满足了我们儿时的虚荣心,也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不少欢乐。
新春他用糊窗户的下脚料拼成红绿黄相间的风车,不仅漂亮,转的欢快而持久,每年春节都会让小伙伴们嫉妒不少时间。初夏他用湿榆木和麻绳做弓,以高粱穗杆绑扎铝丝为箭,射程特别远,并且用的时间越久,榆木由于干燥拉的麻绳更紧,弹性更大,箭的射程自然就更远,和伙伴比赛总是遥遥领先,感觉比奥运射击冠军还牛气。金秋他割一把绿绿的蒲草,在阴湿的墙角晾成柔柔的细丝,然后编制成一个碧绿而精致的蛐蛐笼,剥草丛抓几只蛐蛐放进去,挂在矮矮的屋角,每天晚上我们在清脆而动听的歌声中进入梦想。寒冬他用别人家打家具的废料为骨架,从柴薪中找出较直的木棍为滑杆,用磨亮的粗铅丝为滑条,做成的冰车既轻巧又飞快,我常常鹤立鸡群式的成为同学们关注的焦点。他们都羡慕我有这么耐心又颇有匠心的爸爸,让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都过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
我父亲做的饭菜很受用,尽管那时既缺菜又没调料,但他都用他的爱心和耐心做的很有味很可口。那时做饭都用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手拉风箱吹火,柴薪基本就是玉米秸秆,火势不好把握。熬菜的时候,尽管油很少,他都耐心地榨出葱段、花椒的香味后,才加水放菜。他能听出熬菜里有多少汤的声音,他都能及时停止往灶腔里添柴火,揭开锅盖一铲,汤正好熬完,火候正好,也没有扒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糊锅),极其有限的油、葱和花椒的香味最高效率地孕育在熬菜里,菜既黏糊又好吃。当时的主食主要是扒老玉米饼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玉米面锅贴,就是将菜煮到沸腾,大铁锅菜汤以上的锅面达到了一定温度,然后将和好的玉米面揉团用手轻轻地按在锅边,为避免重力下垂的影响,也考虑玉米面不好熟,将面团均匀多按几次,基本达到上下薄厚一致,然后盖锅盖煮菜,等菜熟了停火的时候,锅贴没有糊,正好紧挨锅面的是一层黄灿灿的硬层,我们亲切地称之为隔家家,特别好吃,这硬层增加了玉米饼子的香气。扒馒头的时候,由于白面好熟,就简单多了,我父亲总是把和好的白面很潇洒往锅面一甩,由于重力作用,自然形成了上薄下厚流线型,等出锅的时候,一看那一个个齐刷刷可爱的急剧膨胀了的小家伙,就觉得特别有胃口,确实比笼蒸的馒头好看好吃许多,也增加了不少情趣。
我父亲能把杂散的黍秸绑扎成好看耐用的髫埽;能用葵花杆和报纸加工成平整的顶棚;不管位置多不好,他用泥板磴的土炕,又顺烟又热乎。他那双粗糙的手常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再加上为人朴实厚道,因而每天特别忙,农闲的时候,人们都侃大山或打骨牌,而我父亲被邻里邀喊做家什。
我读高一的时候,我们家特别困难,几乎到了辍学的地步,我父亲就日思夜想靠双手改变窘状。偶尔的机会,他捡到一个铁笊篱,忽受启发,仔细看了看笊篱的编法,就买了些铁丝开始编,由于铁丝比较粗壮,比机器加工的耐用的多。用精心雕刮的粗杨树枝为杆,以编制的铁网为头,用八号铅丝巧妙连结,结果编出的样品美观度比机器加工的一点不差,却经久耐用的多,去商店批发,很受欢迎。就因为这小小的笊篱,使我们家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我们姊妹几个都顺利完成了学业。
我常常和我爱人、孩子谈起父亲的慈爱,聊起我父亲的手,感叹自己没有遗传他心灵手巧的基因,对操作性的东西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多少悟性,尽管也用了不少心思,编出的笊篱却难看的没法上市。我特别怀念父亲那双手,那双充满灵气、满载爱心的手,他让我们知道世界上什么是最柔软的东西,那就是对孩子们的细腻,是对家庭的责任,是对邻里的热心,是在困迫的日子对美好日子的创造,引导我们信心满满地去开拓未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难的,除非你丧失信心;没有什么是苦的,除非你失去希望。
父亲的新年
我一直喜欢过年的感觉,我这种感觉主要来源于我的父亲。
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少米没面的,现实很骨感,但年却过得很丰满。
腊八前夜,我爸提前用热水泡好芸豆,次日早早起床,煮豆、下下米、劈米汤、火煮、焐闷,香味在矮屋越渐弥漫、香气在土炕越渐凝聚,米豆香在周围越渐馥郁、直到越渐浓烈的充耳不塞,唤醒了在睡梦中游弋的我们。父亲笑着给我们每人盛一碗,当把米饭揀到嘴里的时候,一缕有些发红的晨光穿越狭小的玻璃窗户,射到我们眼里,我妈笑着比我们的眼谁更红,可能预示着谁红谁旺之意。让人惊叹的是爸爸的厨艺,一开锅刚刚好,刚刚熟透却不胡锅,米饭筋灿灿红巍巍的,中看有好吃,真可谓色香味俱全。更让人惊叹的我爸对时间的把握,不迟不早刚刚好,不用等不用急,每次都是第一口饭和第一缕阳光喜相逢。
小年是新年的开始,中午都吃炸黄米糕,饭后我爸打开仅有的一板鞭,给我和弟弟每人掺10来根,每人一根细香,让我们一根一根地响,那时的鞭很细色彩也多也很精致,纯火药的也不炸手,我们一下午和伙伴们轮流着半天响一根,日子过得惴惴而愉快。晚饭后,麻糖有时有有时无,尽管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我们家当年的收入晴雨表,但饭后响两根二踢脚红炮是必须的,父亲总是试着鼓励让我们响,把炮用拇指和食指拿捏到不掉不紧,然后点捻,伴随哧哧作响的白烟炮腾空而起,很响亮很敞亮,好像横扫了残留的霉运,预示着食难果腹日子的远去。
二十七八打扫家糊窗户,我爸爸常用花花绿绿的下脚料给我们做风车,风车大方又转的欢快,在小伙伴间赢得不少荣耀。
除夕前天,上午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劈一些木材整整齐齐垛在东角的屋檐下,尽量正月里生火少出烟,让屋子多保持一些干洁,多一些节日氛围。中午总要煮些肉,哪怕只有一斤,马上过年了,必须让我们提前尝尝腥解解馋,感受一些年味的气息。午后必须完成两件事情:一件是用木盒装稻谷,用黄纸糊裹一个斗子,在上面的纸上写金银满斗四个字;另一件是蒸供品,就是在捏好小馒头上加一条曲环,在最上面按一粒芸豆后蒸熟。然后将古老的桌子正南摆到院子中间,将斗子和供品摆到桌面中间,虔诚地点一根香穿过黄纸戳在斗子里,上供品,点一根红炮,一年中的仪式就算开始了。一直到大年初五,每天三餐前都首当其冲做这件事,除供品外还用小碗盛每天做的新饭,应该是祭拜天地祈求五谷丰登米粮满囤吧。
除夕,早晨吃炸糕和豆芽与粉条拌的凉菜,中午是插酥糖饼和豆腐熬粉条。大年初一,早晨不用说吃饺子,中午吃大米饭、熬菜和熟肉。初二以后就比较随便了,可以蒸着剩下的饭菜吃。每次饭前都依次祭拜天地、祖先、财神。祭拜天地、财神用黄裱(将黄纸拆成16k大小,沿宽的方向折两至三折即成),祭拜祖先用纸钱。如做新饭了,将新饭、肉块与供品一块供,没有做新饭就将原供品蒸热后上供。初五中午一般吃炸油饼,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从炕席底扫一些尘土,用小铁簸箕盛上,倒在交叉路口形成圆锥状,在顶部插一根香,点一份黄裱后,在附近找一块石作为支撑,调整倾度和方向,我爸爸总是指着远处的目标说就对准那儿了,然后点燃红炮,尽管很难击中目标,我们总是乐此不疲、百查不厌。
不管多忙多累,我爸爸总是毫不忽略地做着这些事情。当时真是太穷了,和任何邻里都没法比较,一般过了正月后就断粮了。好在父母都宽让厚道,在村子里享有最好的人气,一切困难都可以靠借来缓冲,过年生产队没有给分到大米白面,就和街坊借点,家人可以凑合着过年,但供品必须是纯白面的,香和鞭炮是不能或缺的,哪怕少到不可再少。
有句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也可以套用说贫困人家百事哀。当时家里那么困迫,家人还常常在新年前后生病,我、我弟弟和我爸记得都病过一次,我是急性肠炎。母亲病的次数就多了。记得有一年除夕夜难受的特别厉害,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把我们吓了个半死,半夜跌跌撞撞地去阮家窑村找医生。不管境遇怎么样,我爸爸一直自觉地认认真真执行着过年的程序。如果家里有病人,我发现父亲有意把旺火的木材劈的粗壮些,把谷子秸秆准备的多些,院子中间拉一根绳子,隔段粘块剪好的彩纸,玻璃上贴几个自剪的双喜字。除夕夜在大门口还燃两捆秸秆,旺火燃烧的浓烈而持久,感觉霉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天亮后,院子虽破,但看到红彤彤的对联,花生生的彩挂和笑盈盈的喜字,将院子点缀的喜庆浓郁,无可怀疑地觉得好日子很快将会来临。
记得看过一则故事:二战期间,美丽的柏林几乎被夷为平地,两个英国记者去现场采访,一个记者问:一座那么美的城市被炸成这样了,还能重新建起来吗。另一个记者说:能,一定能!记者惊愕地问为什么,另一个记者指着一家破烂不堪的房屋,桌面却擦的干干净净,上面摆着正在盛开的玫瑰,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在这么凶险的时刻还不忘浪漫的民族,一定是无坚不摧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爸的所作所为不算迷信,应该是被禁锢手脚、家境困迫而又很无奈的农民的一种信仰,尽管当时比较艰难,但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坚信那是暂时的,好日子是值得向往的。
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凡人,疾病灾难在所难免,家境越糟糕,生活越艰险,越要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过得有情有趣,过得有气势有潜质,这样我们的家才有希望,我们的生活一定充满阳光。这是我爸爸用行动告诉我的生活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