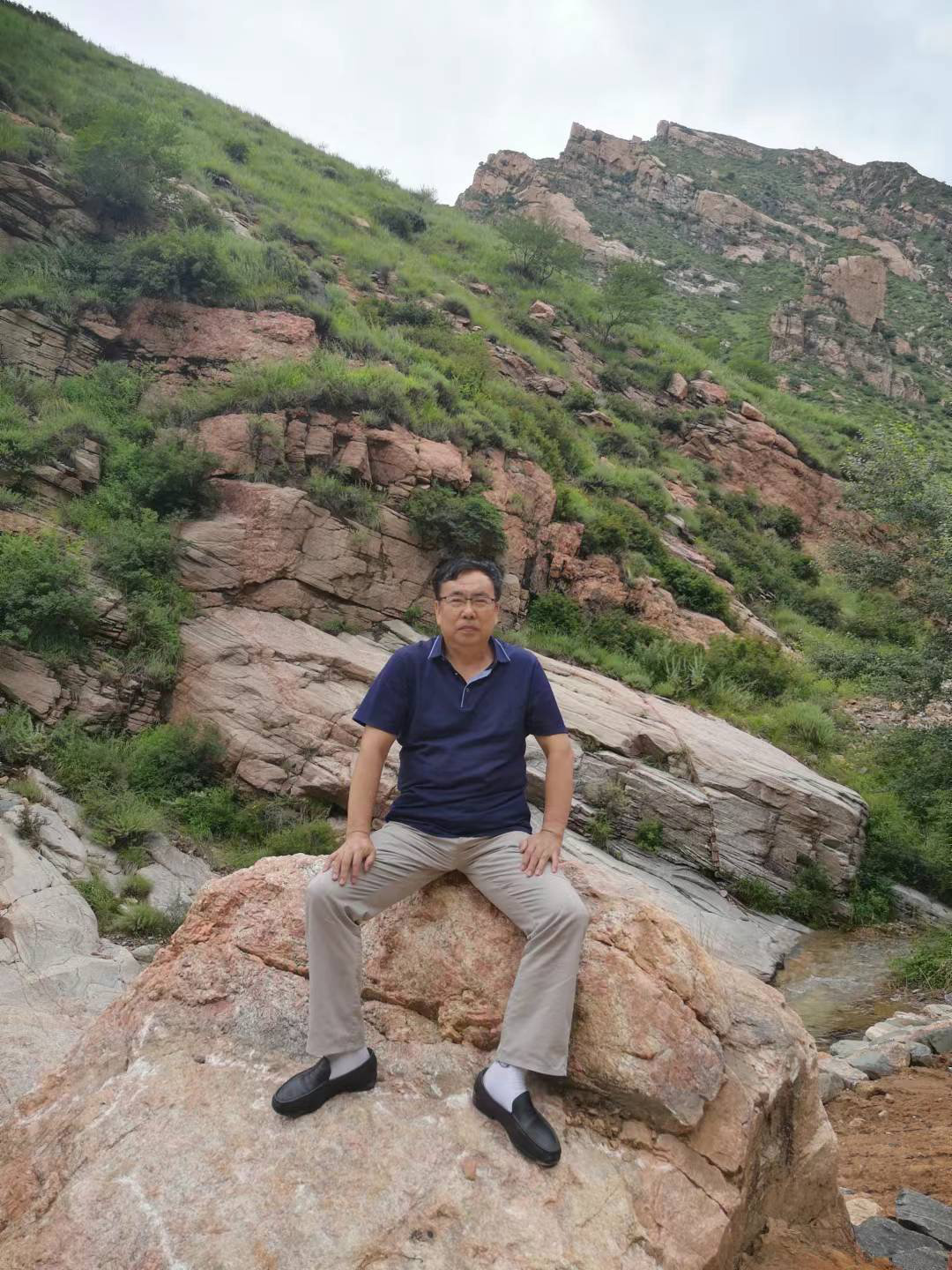【国庆特刊丨中国作家 薛毓文 作品展】
丨国庆特刊丨
中国作家 薛毓文
作品展
作家简历
薛毓文 作家、研究员、媒体评论员,近年在中央及省市媒体发表散文随笔、经济研究、古体诗词、新闻评论等作品数十万字,其中散文、评论作品多次获得国内、省内奖项并汇编出版。
★ 作 品 展 示 ★
枣乡故事
在我的家乡,不管是沟沟梁梁还是平坦的土地上,到处立着的是哨兵似的枣树。
每到初夏时节,漫山遍野的枣树芽开始展现她独特的魅力,嫩嫩的、绿绿的,仿佛一枚枚镶嵌在枝头的绿宝石。枣芽直直向上迸发生长,不久便自然分立出三五个枝丫,沿着一根根枝丫两边各长出了四到五片的小叶子,像极了人的手掌。过不了多久,在掌心的支脉部分便长出了一串米粒状的东西,密密麻麻的,这便是我们常说的“枣米米”。大约再过半个月左右,“枣米米”绽放出枣花。枣花开放时,山野里弥漫着的是一种奇特而厚重的浓香,这时整个山村就笼罩在了“嗡嗡”的蜜蜂采蜜的声音当中。小时候听村里养蜂人讲,枣花糖分高,蜜的质量最为上乘。
当枣花褪去,一个一个绿色的点开始显现,这便是红枣的雏形,形状像小孩子的肚脐,我们称为枣肚脐。小肚脐泛着青光在光、热和水分的作用下一天天长大,在特别旱的山梁上长到大拇指头大小,在水分充足的沟坝长到成人半个中指头大小便基本定型,然后开始静静吸吮天地精华,享受阳光雨露的哺育,慢慢进入成熟的时节。
白露前十来天开始,绿玛瑙般滚圆滚圆的枣从上到下依次开始挂红,从最初的“眼圈红”,到后来的“半腰”,再到最后的全身通红,这时的村里村外,简直成了亿万个红灯笼环绕着的世界。家乡有农谚云:白露枣两头红,红不够连夜红。白露过后,枣没日没夜赶着红,仿佛都要赶在秋分前把美丽成熟的自己奉献给滋养她们成长的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儿时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跟着大人们去打枣。到了枣树林,男劳力拔下腰间别着的斧头,抬着头在林间寻找着细长细长的树枝,然后砍下来当打枣杆用。通常是抱住枣树先使劲摇,没有掉下来的再用杆子使劲敲。女劳力们抱着头,一边叫一边骂,等男劳力转向下一棵树时,便蹲下将一颗颗红枣拣到随身带的筐子里。而我们则到处挑拣奇形怪状的枣:有长得像人鼻子的“鼻鼻枣”,有长得像人蹲下去样子的“歪歪枣”,有长得像酒壶酒瓶的“瓶瓶枣”,有长得早已熟透发软了的“绵绵枣”等,然后拿着各自的战利品到处炫耀。
在粮食短缺的年代,除挑拣个大肉厚品质好点的枣留足逢年过节待客用以外,剩下的大多被用来加工“炒面”。将红枣煮熟,与谷糠和在一起,用碾子碾成一片一片的,晾干后再掰成小块,加一点点炒熟的黑豆、莜麦之类的,再用石磨磨成面,这便是“炒面”。我们那时的早饭晚饭大都吃这个。将“炒面”放到碗里,加上稀饭或开水使劲缠,缠好后就开始吃,但不敢吃太多,因为有谷糠,吃多了排便会非常困难。日子虽苦,可加了红枣的“炒面”吃起来还是有甜丝丝的感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红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那些年,每到打枣季节,红枣贩子会成群结队来村里收枣,最高时每斤1元多钱。他们有的将枣拉到外地直接卖掉,有的就地简单加工,也有做深加工的。简单加工就是将收来的红枣装入塑料袋,然后喷上酒,密封好,放入纸箱装车,等到了东北,就成酒枣了。东北人喜欢喝酒,据说很受欢迎。深加工就是将红枣去核,然后用地火烤,再加上糖,做成蜜枣,价格成倍地翻,据说喜欢甜食的南方人特别喜欢。不少脑子灵活的人还建起了红枣深加工厂,用红枣做饮料,做醋。
好的市场、好的行情,激发了家乡人对红枣前所未有的重视热情。自古以来,家乡的红枣树都是自然生长,自生自灭,没有人专门侍弄。看到了红枣的经济价值后,便有人开始把原来种粮食的平地也栽上枣树,秋春两季既施肥又修剪,三两年过去,红枣的产量成倍增加,每到卖枣的时候,枣农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喜悦。于是,家乡人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新房多了,年轻人还把自行车也换成了摩托车。
然而好光景没有几年,家乡红枣一落千丈,从最初价格一路下滑,到后来几乎无人问津。有好几年秋后回乡,看到地上跌落的红枣满满一层,那些没有落下的枣则孤零零在枯枝上摇曳。有的村民干脆将辛苦栽下的枣树悄悄砍掉重新种上粮食,或换成了核桃树。问及原因,原来是受外地红枣的冲击。外地红枣个大肉厚,而家乡的红枣多属于老品种,加之土地贫瘠,块头不大,市场不待见。
我常常感叹,世间万物都有定数,红枣的命运亦然。家乡的红枣多少年来不打药不催熟,都是自然生长而成,是当之无愧的纯天然绿色产品,怎么会突然间就失宠?但有时转念一想,正如人不进步就会落后,就会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会被淘汰一样,传统的红枣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唯有在坚守品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寻求到生存之道。好在勤劳的家乡人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布局,“公司+农户”的合作、系列产品的开发、老旧品种的改良、电商平台的搭建等等,正在为红枣产业的再腾飞积蓄着力量。
家乡素有“红枣之乡”的美称。不论是离家在外的游子,还是依旧生长在那块土地上的乡邻,对红枣的那份记忆、那份期许,早已超过红枣本身。因为那一颗颗小小的枣,承载了他们祖祖辈辈人生的酸甜苦辣,承载了他们的梦。
碛口记忆
千里黄河经晋陕大峡谷一路奔腾而下,在碛口古镇变得平缓而温顺。尽管下游百八十米处就是波涛汹涌的“大同碛”,但眼前这最宽处约有400多米,波澜不惊、波光粼粼的河面,使你忘却了这就是雄浑大度的母亲河。
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之如此天然良港,使得碛口古镇在明清时期至京包、同蒲铁路开通的数百年间成为西北物资运往华北乃至全国各地重要的“水旱码头”,自古有“拉不完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山西离石区)”之说。位于古镇街边的记忆馆里,现代化的科技正呈现着当年“物阜民熙小都会”的繁华盛景:一艘艘顺流而下的皮筏商船挤满了开阔的河面,一件件粮食、皮毛、油篓等货物在河岸边堆积如山,一群群操着不同口音的商人在石板铺成的街道上往来穿梭,一支支驼队沿着崎岖的黄土高坡一路向东,将粮油皮货源源不断地运往晋商腹地的汾州(汾阳市)方向……
有人说,碛口是用来看的,那些富甲一方的商贾们的确留下了许多搬不走的遗存,诸如古镇上依山而建,依河而筑“巷巷相通,铺铺相连”的网格状窑洞、商铺建筑群,西湾村里“背山面水,左青龙右白虎”的陈家大院,南山坳间“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的李家山特色民居等等,令许多游客乃至学界大咖们叹为观止,赞口不绝。也有人说,碛口是用来听的,每当夜深人静,“大同碛”边传来的咆哮声犹如千军万马在鏖战,好一派“河声岳色大文章”的滔天气势,老河口边艄公们“哎吆、哎吆”的吆喝声,搬运货物的伙计们“一二一”的唱和声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这是深刻在碛口几代人心里的声响,历久弥新,挥之不去。石板街道上,不时有嘀嗒嘀嗒声,说不定又是哪家掌柜骑着马匹还在为明天的粮油能否到货,或者能否发往外地商家而忙碌奔波着。突然,十余里之外的东山上传来了叮咚叮咚的阵阵驼铃声,精明的商家立即连夜通知伙计们,明天的货物又可以正常起运。
而更多的时候,我想碛口是用来品的。已故古镇盲人艺术家张树元先生的一曲三弦书《夸碛口》,道尽了碛口的人文荟萃,古今沧桑。当你拿着一条小板凳坐下,倚靠在门框边闭上眼睛静听老人手把三弦,抑扬顿挫娓娓道来,那简直就是一幅幅如醉如痴梦幻般的古镇兴盛画卷。冬春时节,外地客商涌向塞外明珠包头,“都来包头买粮油,装上皮筏流碛口。”“烧了香、磕了头,艄公才肯把船游。”“碛口的街道五里长,前后一十三道巷。”“碛口街上尽是油,三天不发满街流。”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语言,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从中品得到的不仅仅是栩栩如生的动人画面,更是晋商们在古老碛口商道上生生不息的传承与传奇。
碛口古镇背靠石山,生态古来脆弱,难得有泉水。随着商贸业的快速发达,一些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吃不惯黄河水,好客的商家费了好大力气,终于在黑龙庙背后的山涧中凿出了一眼水井,当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古镇人欢呼雀跃,后人取《尚书•仲虺之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和南宋王应麟《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之意,冠名曰“裕後泉”。在长期的粮食贸易中,精明的商家利用上游运来的粮食就地转化,用此泉水开始了白酒酿造。据《碛口志》记载:民国30年前后,碛口有酒坊6家,其中西市街四十眼窑院“裕後泉”商号于1916年酿出的白酒曾名噪一时,可惜在抗战时期停产歇业。夕阳西下,伫立古井旁边,捧一杯清澈甘冽的“裕後泉”俯瞰黄河,雄浑而平静,如母亲博大的胸怀。是啊,虽然在她的面前世事不断的演变,时而欢腾,时而寂寞,但她始终看得清,容得下,依旧缓缓地流淌,静静地诉说。这,或许也正是商业碛口、人文碛口真实的魅力所在。
过生日
过完了今天,我的人生就算走过了五十五岁。
中午在食堂吃了盘饺子,一群每天在一起工作的小姑娘小伙子大惑不解。她们早把我的规律摸透了,要是在平时,我这人性子急,偌大食堂我总是哪儿人少吃哪儿,可今天偏等了有二十分钟,破天荒吃了盘饺子。
早晨刚上班,远在老家的爱人发了张祝福的图片,才记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临了,再三叮嘱中午吃点饺子。其实按照老家的习俗,过生日最应该吃的是糕,后来也开始学习城里人,有吃碗拉面的,大概是取长寿之意。记得在儿时,家里再困难,不管谁过生日,母亲都要给全家蒸顿糕吃。先将黄橙橙的软米(用糜子脱壳而成)用碾子碾成面,叫糕面,然后用温开水拌成颗粒状,在火上蒸熟,叫蒸糕。蒸糕是有学问的,糕面如果粘性高,就得拌得硬一点,否则蒸熟后粘手,不好处理;反之,如果粘性不够,就要拌得软一点,否则像玉米面窝头,全然没有糕的滋味。蒸糕时,要把火加旺,然后一层一层往笼布子上均匀地撒拌好的糕面,第一层没有蒸熟,是绝对不能撒进第二层的,否则就整个蒸生了,不论如何重复蒸,也永远再蒸不熟。糕分为油糕和枣糕,油糕是包上红糖或豆沙后用油炸出来的,枣糕是蒸的时候一层糕面一层时红枣蒸进去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要能吃上油糕简直是一种奢望,因为家乡盛产红枣,多数情况下就地取材吃得是枣糕。我曾无数次地问母亲过生日为什么要吃糕?母亲总是一句:吃了糕,走得高。可见这吃糕有讲究,寄托着大人们对下一代的殷殷期盼。这一传统代代相传,后来给孩子们过生日,爱人也总是给蒸糕吃,可惜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那时候喜欢吃糕了。
小时候盼过生日,在生活困难的年代,过生日才可以吃上一顿好饭;稍长后烦过生日,过一次生日长一岁,成家立业谋工作,一大堆的事情接踵而来,人生的各种无奈和矛盾陡然而生;像我们这种走过了半辈子的人,现在对过生日倒有些又怕又盼,怕的是人生就这么一天天会耗干的,过一天少一天,总使人不舒服,盼的是孩子们快速的长大,去承担他们该承担的东西。其实不论愿不愿意,每天的太阳照常起落,每年的生日如约而至,小的都要长大,大的都要变老,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心理作用而已。
生日也是有大小之分的。在一些地方,孩子过十二岁生日叫大生日,邀请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参加,有主持人、有音乐、有布置考究的场面,杯盘交错,场面酷似结婚。十二岁生日原本在晋西北一带叫做“开锁”,意思是怕孩子生下后难养活,外婆家送把锁子,十二岁生日那天由外婆亲手打开,标志孩子成人了。连开三次,一边开,一边口中念叨着咒语:“开开了,锁住了,我娃今年十二了。”本来就这么简单一事,以前在家吃顿糕就办成的事,现在都在饭店,而且相互攀比,规模越变越大,确是有点过。还有一些地方男人过四十岁生日,本意大致是这个时候的男人事业有成,有夸耀的意思,但后来事业一般者也加入进来,你过我也过,大家都来过,热闹规热闹,但对人是一种负担,对资源是一种浪费。给老人祝寿也属于大生日,古人讲六十大寿,从六十岁开始,每逢整十,子女都要为老人过生日。与给孩子过十二岁生日不同的是,这样的大寿一般规模都比较小,在一些农村子女有大出息的,也不乏有唱大戏、宴宾朋,热闹个三两天的,但一般都是子女簇拥到一起祝福老人快乐健康长寿。母亲在世的时候常说,人老了不敢庆寿,她说过几个人的名字,都是庆完大寿不久就走了的,庆寿当然是指过规模相当大的那种生日了。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庆寿,几十桌的宴席,鼓乐齐鸣,老寿星端坐在花团锦簇的帷帐中接受晚辈的轮番参拜,场面甚是隆重。所以每年给她过生日,都是我们兄弟陪她吃顿饭,拉拉话。我至今还在想,究竟是她怕我们多花钱,还是真有其事?反正老人家健健康康活到九十多岁。
其余的生日,自然是象我过的这种一盘饺子、一碗长寿面,或外加一碟小菜、一壶美酒的小生日了。这种生日过得就是舒心、过得就是安静、过得就是坦然、过得就是亲人们发自内心的祝福。其实人这一生,舍此情意又有何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