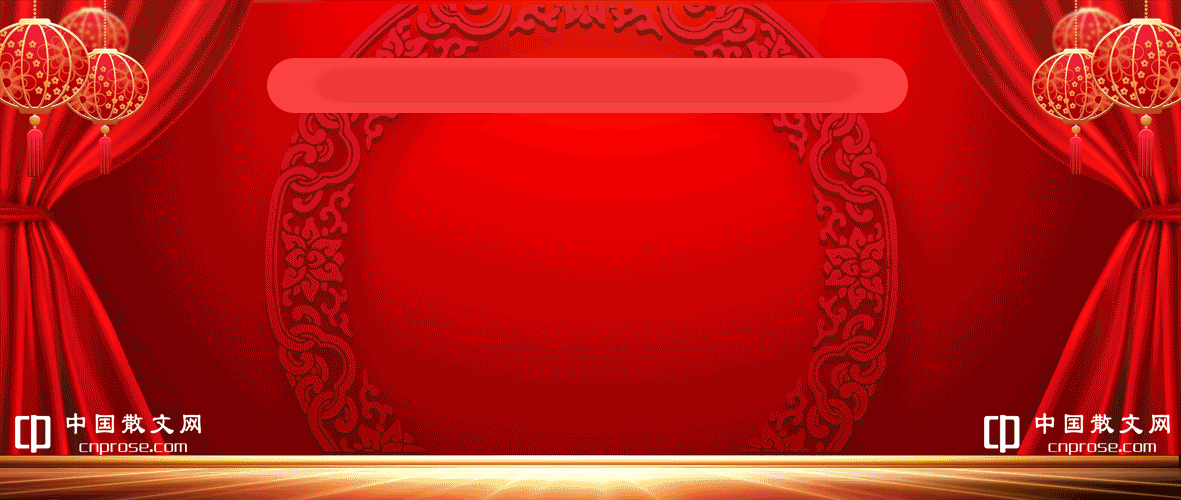【2023国庆特刊丨当代作家 王冠群 作品展】

艺 术 简 历
王冠群,字远航,男,1954年出生,辽宁省人,现定居大连。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曾在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发表译文2篇(英译汉)。科研成果曾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市二等奖。近几年来,在书刊、报纸等上发表散文、小说30余篇,发表诗歌近200首,发表书法、绘画及篆刻作品近200幅。其文学、艺术作品多次在国内不同大赛中获奖。系中国诗书画家网高级书画家,华夏开明书画院理事,中国百家文化网专栏作家、高级书画师、注册文艺家,北京国都墨韵书画院会员、理事。
作 品 展 示
爱的奉献
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曾说过:“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逼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再劳动!”
1996年,我任科主任仅近两年,又刚刚被医院破格聘任为副主任医师,因此干劲十足,如火如荼。为完成一项科研项目和复查当天诊断过的病例,每天下班后,我在职工食堂(或中午留出点儿饭)匆忙吃口饭,回到科室继续工作,有时至午夜才回家。而且时常,周六和周日遇到急诊,我还得来到医院加班。但,我从来没要过一分钱的加班费。
有一天,医院工会主席找到我说:“王主任,再过两个多月就到中秋节了,市里准备筹划一台文艺晚会,指定我们医院出一个舞蹈节目,主题是‘爱的奉献’。因此,院领导非常重视,特意从市歌舞团请了一位舞蹈老师,又从医护人员中选了四个男的和八个女的,其中男的有你一个,从明天下午起,你去大会议室排练。”我听后,不知是喜还是忧,那年我已43岁了,而且我的科研项目已进入尾声,时间很紧。但,我还是问了一句:
“又是中老年舞蹈吗?”(因为1991年我与同事们代表医院参加了市卫生局举办的中老年首届健身舞比赛。)
“不是,这次选的都是年轻人。”
工会主席回答。于是,我不解地说:“别开玩笑了,我都四十多岁了,院里有那么多年轻小伙,为什么选我?”主席说:“许多人都推荐你,但还未最后定,先让舞蹈老师看一看……”我心想,这是严格选拔,层层过关,还要参加“面试!”有点不痛快,觉得有伤自尊。然而,我就是有个韧劲,凡事向来不服输。谁怕谁呀!面试就面试,管他呢!于是慨然应允。
当晚,我将此事与媳妇说了,她听后立刻说:“你脸皮也够厚的,快拉倒吧!多大岁数了,还和一群小姑娘、小伙子同台跳舞,别叫人笑话了!”我反唇相讥:“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这也是院里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你年轻又漂亮、想去跳,可没人要你。再说娱乐娱乐有什么不好?平时,医生的工作既紧张又劳神,难得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我如期而至。一走进大会议室,便看见十几个年轻的医生护士早就到了,旁边坐着一位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这时,工会主席站了起来,彼此打了招呼后,她便说:“大家都到齐了,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医院从市歌舞团请来的田老师。从今天起,由田老师指导我们排练,请大家鼓掌欢迎……”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位田老师——他穿着一身牛仔服,中等身材、相貌平平,腰身也不健美,还有些秃顶,显得土里土气,看不出有什么艺术气质和舞蹈才华。心里有些不服气。
田老师先给我们做几个舞蹈动作,让我们每个人跟着做。我心想这大概就是考试吧!然后,他又给我们讲这个舞蹈的整体构思,细节设计并示范一些舞蹈动作……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位“土里土气”的老师果然有真功夫,其投足、亮掌确实很专业,不可小觑,便暗暗地佩服起来。
第三天,工会主席打电话通知我照常去排练。这证明我考试合格了,未被淘汰。于是,我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上午处理复杂而繁重的医疗工作,下午进行排练,时而还被科室的医生找去,解决疑难医疗问题。下班后,我依然在医院加班两个小时左右。每天晚上大约七点钟到家后,我先练习基本功——压腿、踢腿、弯腰,趴在地上做三组俯卧撑,再仰卧于床上做三组仰卧起坐。然后,温习白天所学的舞蹈动作,力求娴熟、美观大方、精准到位。
我妻子时常抱怨,唠叨个不停:“你一天天忙,就顾自己,家里的事一点儿也不管,买米买菜,买家用电器大件等和大事小情都是我战友们帮忙。(妻子是从部队医院转业的军医,在本市的战友很多,市政府的、公安局的、工商局的、汽车队的……干什么的都有。医院里有的同事经常跟她开玩笑,管她叫“赵营长”。)我看家里有你是‘五八’,没你也是‘四十’,你干脆搬到医院去住得啦……”我假装没听见,或用双手捂住耳朵——不听!继续练我的。有时,我半开玩笑地也回应她几句:“你不是‘营长’吗?指挥‘你的那些兵们’干不就行了,还用得着我吗?”
经两个多月紧锣密鼓地排练,舞蹈已成型。演出的日子到了,地点在市人民剧场。
傍晚,明月高悬,微风习习,秋菊溢香,蝉鸣渐远。大街小巷彩旗飘摆,花团锦簇,而那一抹抹的“中国红”才是我们心中最靓丽的色彩。我们乘坐大巴车来到人民剧场。舞台上方挂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喜迎中秋佳节文艺晚会”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晚会开始了,我们的舞蹈是第一个出场。
紫红色的大幕徐徐被拉开,我站在舞台中间,头上蒙着一块写有斗大癌字的白布,此时响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咚!咚!咚——咚!旋律深沉而凝重,又不失自强不息,寓意着患有癌症的病人在痛苦中挣扎;在绝望中期盼着奇迹发生。他们眷恋生命,渴望得到医治。交响曲过后,我头上的白布被揭开,“亮了相”。一位美女热情而奔放的歌声响起——“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与此同时,一群美丽、文雅的“白衣天使”缓缓而出,翩翩起舞。如同红十字下最圣洁的白雪,融化、牺牲了自己,却孕育出一个绚丽、和煦的春天。此时舞蹈达到高潮,我也渐入佳境,纵情地舞起来。心里无比激动和兴奋,情绪高涨,将我所对患者的那份同情、责任与担当全都融入在舞蹈里……也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整个舞蹈编排新颖,气势宏伟,有情有义又有爱,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演出结束后,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小朋友们登台献花,舞伴们相互击掌拥抱,我也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俱往矣,时光在流逝,容颜在改变,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至古稀,成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两个孙子的爷爷。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一颗初心和矢志不渝的信念。我每天勤奋不怠,笔耕不辍,书写人生百态,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歌颂改革开放和党的“二十大”以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咱不图名也不图利,只求过的充实,活得愉快,活得身心健康,真正活出新时代老年人的风采。而且那一次演出时常在我脑海里萦绕,久久挥之不去,难以忘怀。回首那激情燃烧之岁月,我们曾经的付出、奉献与收获和欢乐……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2023年金秋于大连)
八路军来得可真及时啊
父亲是一名医生,60岁离休后,又先后受聘于几家医院出专家门诊,直到75岁才回家休息。但他并没有停歇,始终抱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心态继续为周围居民义诊和讲解医学科普、养生保健等知识,深受百姓的欢迎和赞颂。居民们都亲切地称父为“120王大夫”。而且几年来,父亲每天勤奋不怠、笔耕不辍,完成了一部10万余字的专著:《顺逆从容》,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60余篇(医学科普、散文、诗歌等)。某报社编辑曾打来电话问我:“王老先生今年多大年龄?他投来的那些文章是您在电脑上替他输入和发送的吗?”我回答编辑说:“都是我老父亲自己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出来并发出去的。”编辑称赞道:“这老爷子真了不起!”
如今,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于2018年3月17日去世,享年90岁),然而,他那全心全意、无怨无悔地为患者看病治病的高尚美德;他那正直善良、谦和宽容、助人为乐及不为权势所屈的优良品行;他那孜孜不倦、刻苦专研、勤奋好学、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心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闪现,我每时每刻都在怀念我亲爱的父亲。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的他所经历的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忆较深刻的是父亲在苏家屯发生的一件事。那是1948年10月,辽阳解放了,全城的老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涌向街头热烈庆贺。然而,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却被抛弃在城内的一个大院里。党和人民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发动老百姓组建了一支担架队,把伤病员送往沈阳。因为那时沈阳尚未解放,还是国民党统治区。
父亲当时还是一名高中学生(以总分第一名考入辽阳高中),而且患伤寒病一个多月刚好,头发都掉没了,又瘦又弱个头还小,也参加了担架队,和乡亲们一起抬着国民党伤病员向沈阳进发。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难免有时食宿无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有些乡间小路崎岖不平非常难走,尤其是遇到泥泞打滑的路段,更是步履艰难,何况肩上还抬着沉重的伤病员。不到一天的时间,父亲的肩头就被压肿了,脚也磨出了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疼痛难忍更加艰难而缓慢。
这一天下午,天阴得像个黑锅底,隐约的雷声还在空中隆隆地滚动着——眼看着一场大雨就要袭来。担架队艰难地来到了苏家屯附近的一个村庄,刚刚安顿好伤病员。突然,见村头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三个斜挎着盒子枪的便衣特务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他们驱马来到担架队的驻地,从马上跳下来,手执马鞭,朝着父亲他们住的屋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留着两撇胡、满脸横肉的大个子,眼睛闪着凶光厉声喝道:“都给我蹲下,双手抱头!你们领头的是谁?”喊了几遍,队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这时,三个特务气急败坏地轮番喊叫着:“都滚出来,集合!”于是,十几个担架队员在院子里站成了一排。那个大个子特务又嚷道:“据可靠情报,你们这些人里有八路的探子,是谁?赶快站出来!不然,把你们全都枪毙。”旁边另外两个特务也喊叫着。他们威逼恫吓一阵之后,大个子特务看没人出声,便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你给我出来!”随后又把父亲的同学张鸿逵也拉了出来。先是一顿耳光……打得两个人左右腮红肿,鼻口淌血。“快说,你们俩是不是八路军的密探?”大个子吼叫着。
“不是!不是!我俩都是学生。”父亲实在压不住火了,充满了对狗特务的仇恨。他虽然个小而瘦弱,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一头向大个子特务的胸口撞去……将大个子撞了个大仰八叉——四爪朝天地摔到了地上。
“嘣了他!嘣了他!”旁边的两个特务凶神恶煞地吼叫着。这时,几个队员,上了年纪的老街坊邻居战战兢兢地出来说:“他们俩确实是学生,我们都住在一个胡同里,多少年了。再说,你们把他嘣了,谁来抬你们的伤员?”
“不要多嘴!”大个子特务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满脸铁青,怒斥着,并拔出了盒子枪,将枪口对准父亲的脑袋——正要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危难之际,突然传来一阵枪声和喊杀声……队员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八路军来了!”顿时,三个特务吓得惊慌失措,只见大个子特务左手一扬,喊了一声:“撤!”三人慌忙上马,一溜烟地向沈阳方向逃去。
一场暴风雨过后,第二天早晨,太阳露出了笑脸,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大家吃过早饭,抬着伤病员继续向沈阳方向行走,近黄昏时,担架队到了沈阳。经领队与有关方面联系后,把伤病员安置在车站附近的大厅里,全体担架队员完成了任务,各自散去。父亲拄着木棍,在同学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诉说了遇险的经过。全家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并为之庆幸。爷爷说:“八路军来得可真及时啊,要不然就没命了!”
(2023年金秋于大连)
练书法使人聪慧脑健
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宇宙之精华,能上天揽月,“龙宫”探宝,创造奇迹,就是因为人有高度发达而灵敏之大脑。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组织将逐渐萎缩,功能衰退减弱,尤其是步入老年后,更会加速。因此,加强大脑功能训练,激发大脑功能,是延缓大脑组织萎缩、功能衰退的有效方法。其中,练习书法是激发大脑功能的重要方法之一。
书法,是中国古老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品位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及很高的审美价值。距今三千多年前,当中华文明还处于襁褓中时,作为萌芽状态的书法艺术便诞生于黃河(两岸)——毌亲的揺篮里。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甲骨文和殷金文,有好些作品都非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法家,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留传下来。”
书法是借助于笔墨纸砚而达到排忧以调神、运腕以调身、行气以调息、娱心以调情。练习书法,久而久之,可使人的心灵煥发、大脑聪慧、身健体强、延年益寿。由此可见,古往今来,说书法能使人聪慧长寿,并非虚传。如唐代著名书法大家柳公权88岁,欧阳询85岁,明代著名画家、大书法家文征明89岁,近代书画大家黄宾虹90岁,齐白石97岁,均以长寿而仙逝。
根据现代医学观点而言,在练习书法时,需排除杂念、聚精会神、一丝不苟,每个字都要仔细斟酌。同时,下笔要指实、掌虚、腕平,手指执笔的肌肉及关节连同腕部、上肢,甚至全身都在大脑的支配下,随着书体的不同、笔势的走行而做有节奏的运动,从而激发了大脑的功能,同时也提高了免疫功能。根据“用进废退”的生物规律,大脑越用越灵敏,否则即衰退。人经常用脑、持之以恒、锲而不舎,一定会有成效,就是到了老年还可以大有作为。
我的老父亲,从70岁开始练习书法,于78岁时写出了一本10万余字的著作:《顺逆从容》。他每年都有许多文章发表于多种报刊上。至89岁时,仍然耳聪目明、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步态稳健,而且文章频频发表于各种报刊上。这些文章都是他自己用笔记本电脑敲出来并发送的。某报社编辑曾打来电话称赞道:“这年近九旬的老爷子真了不起!”
我今年已70岁了,练习书法已十多年,作品百余次发表于不同报刊及网络上,并多次在全国不同大赛中获奖。几乎每天笔耕不辍、勤奋不怠,虽然已步入老年,但至今,我仍然体健神清,理解力和记忆力不亚于当年。这与练习书法均有密切关系,从而体会颇深,受益良多。
老年朋友们,为了聪慧脑健、延年益寿,活得更有质量、更快活、更幸福,劝君拿起笔来,循序渐进,打好基础,由浅入深,步步深入。多观摩、常动脑、勤动笔、敢于创新,一定会进入那浩瀚高远、绚丽多彩、美不胜收的书法艺术天堂,使之其乐融融、益寿延年。
(2023年金秋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