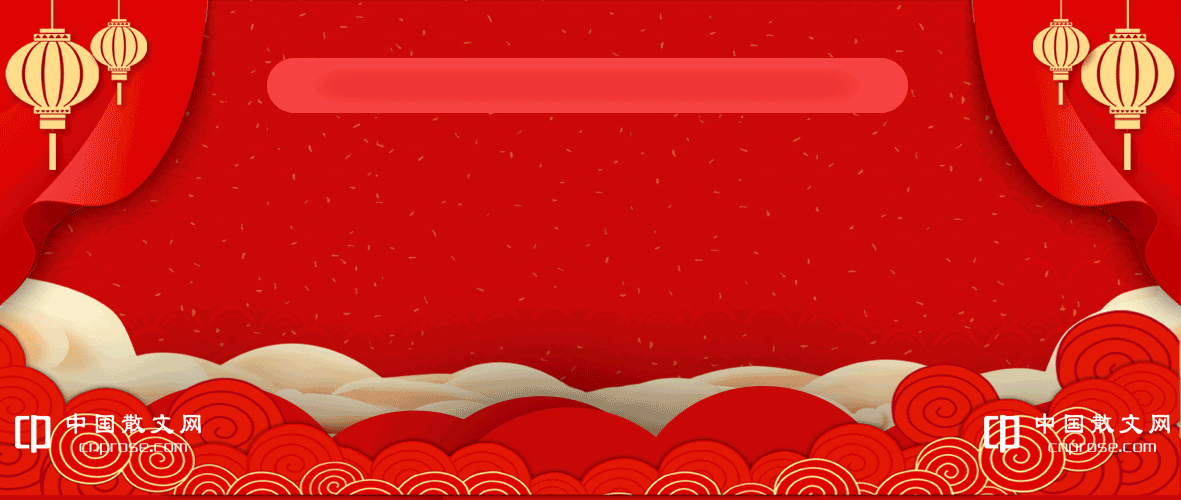【新中国75周年特刊丨当代作家 冰寒 国庆作品展】
当代作家
冰寒 国庆作品展
作家简历
ZUO JIA JIAN LI
冰寒 原名:曾芙蓉。湖北洪湖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荣获中国纪实散文大赛二等奖,《百年散文》征文中获金奖。《中国最美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在全国诗歌散文大奖赛,荣获奖项二十多次。已出版了散文集:《野草》《心灵的使者》《步步生莲》。
祖国万岁
国庆作品展
GUO QING ZUO PIN ZHAN
《记忆里的味道》
美味,像一把童年的钥匙,它锁住锈迹斑斑的炊烟,却锁不住,深藏在记忆里,那又香又甜的成份。
①,散落在教室里的豌豆
童年的零食,几乎都是家里人自备的。麦芽糖、麻叶子、炒米、糯米粉子、炸豌豆、米泡泡,我最爱吃炸豌豆,又香又脆又吃的嘎嘎响。
父亲在国营林场工作,我家里没有分田,虽然在农村生活,却是商品粮户口。队里分杂粮,我家却没有,小伙伴家就分好多黄豆、芝麻、豌豆,他们家大人就用沙锅炒豌豆,让他们带到学校当零食吃。我也馋,可我家一颗也没有,父母在林场上班,离家又远,根本没时间来看我们,更不敢奢望有炸豌豆吃哦!我知道,二姐比我更喜欢吃炸豌豆。别看这小小一粒,放在锅里用沙一炒,小火再小火地煎炒,不一会儿,锅里就噼里啪啦,像过年时的炮竹响过不停,豌豆屁股后面炸开后,露出白白的肉,摊凉后,放在嘴里,又酥又脆又香,又咬得蹦蹦响。无论它多么坚硬,我们的牙齿都会将豆豆嚼碎,那口余香一进肚,管饱好几天咧!
每到下半年,农活不那么忙了。村里经常出现一个老爷爷,推着一个打米泡的土机器,呦喝着:打米泡啰!打米泡啰!一听到这声音,我们小孩立刻像打了兴奋剂似的,从家里偷偷舀来米、黄豆、玉米、豌豆,打上一炮。老人家会收取加工费,五分、一毛即可。但烧炮的柴火要自己带来。打米炮要等十分钟左右,如果炸豌豆时间会更长些。小伙伴们也自觉排队,一个接一个,从不插队。
我们家没有多余的粮食,只能眼巴巴看小伙伴们一袋一袋的米泡装回家,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一些,我舍不得吃,拿回来给二姐先尝。特别是炸豌豆时,一开炮,那豆香弥漫在整个村庄上空,久久不散。我贪婪地闻着空气中的豌豆香,看着那香香的豌豆从口袋倒出,口水都流出来了。实在忍不住馋虫的侵咬,狠下心撕下刚买的练习本最后几页,从小伙伴手里换回二把刚炸的豌豆。平时,我们相互之间,经常这样交换所需要的东西。借几滴墨水,半块橡皮,几页纸张,那时候,这些都是宝贝。我家虽没有多少杂粮吃,但笔、本子、墨水都有。三个哥哥都在读书,练习本有很多,其他小伙伴们,却常常买不起一个练习本。有时用铅笔写完后,再用橡皮筋擦掉,继续用。一见我用新练习本纸跟他换豌豆,他开心极了,我也高兴。换好豌豆立刻飞奔回家,放在二姐手里,最喜欢看姐姐吃豌豆的样子!
有一次是午休课,我趴在桌上假睡。突然发现课桌底下有几颗散落的豌豆,它们胖胖乎乎,圆圆滚滚,可爱极了。又瞟一眼二组、三组、哦,都有散落的炸豌豆,零零散散在教室里的角角落落,我心中一阵狂喜,像哥布伦发现了新大陆。现在大家都在午睡,还不能捡,等放学铃声响,等同学们都走完,才能去捡。好不容易下课铃响了,班主任叫醒我们,问道:今天中午,谁愿意留下来打扫教室?
“我!我愿意留下来打扫!”我立刻站起来回答,生怕有人跟我抢似的。待同学老师走完后,迫不及待将教室里散落的豌豆一颗一颗捡起来,聚在一起,居然有小半碗。
这些散落的豌豆是这么来的:
有的同学兜里破了小洞,漏出来的,有的是从口袋掏出来时,从手指缝溜出来的,有的是打闹时从兜里蹦出来的,,,,,,被我捡到一起,就是送给二姐最好的零食。为了捡教室里的炸豌豆,我连续扫了一个月的地。期末,我还被评为:“劳动积极份子”那张奖状贴在年画旁边,特别好看。
②,一只掉在麦芽糖盆里的老鼠
那个饥饿年月,特别盼着过年。因为快到过年之前,不管家穷家富的人家,都会熬一锅麦芽糖。然后,将晒干的阴米去炸锅,炸成炒米。炒阴米时都喜欢用细沙子混合炒,说是增加香味。最后,将熬好的麦芽糖与炒米一混合,用擀面棒擀成长方型和正方型,稍微凉一下,不能凉太久,硬了就不好切了,容易碎,太烫了,又粘刀。时间正好时,用菜刀切成一片又一片,麻糖片就成了我们童年,最美味的零食了。
用剩下的麦芽糖,再熬一下,盛在一个大盆里,等冷却后,藏好以后想吃糖片了再拿出来用。一年也就熬这么一次!大人们都藏得严严的,防老鼠,更防我们这群偷嘴的小孩。妈妈为了不让我们偷到糖,也是费尽心思将麦芽糖藏得紧紧的,三个哥哥翻箱倒柜,就差掘地三尺了,也没找到。年过完了,父亲还想做一些麻叶子,留给我们平时吃,让妈妈把藏着的麦芽糖拿出来。
突然,听见妈妈大声叫了起来:快来哟!快来哟!错了拐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全朝房间里跑去。只见妈妈从衣柜最内层端出一个瓷脸盆。怪不得我们找不到麦芽糖,原来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呀!老妈呀老妈,算你厉害!
“你们快来看!好好的一盆麦芽糖全被浪费了。”我们围上来一看,妈呀!一只肥肥壮壮的大老鼠,不偏不歪正躺在盆中央,一动也不动,早已经死去。这只坏老鼠,肯定是被甜死的。自己的孩子偷不到,老鼠却先找到了。麦芽糖又粘又糯,它一踏进来,肯定也逃不了,我猜想,老鼠临死之前,肯定大口大口吃着麦芽糖,它前面缺了一大块,幸福的老鼠呀,你死的也不亏。
父亲没有责怪妈妈,他用两根粗筷子,把那只肥鼠从糖盆里弄出来。老鼠只是另一面全沾上了麦芽糖。父亲说麦芽糖再回锅烧开后还能用。他拿着大老鼠,叫三哥、二姐去扔掉,他们都怕老鼠,吓坏了,哪敢去拿。都不肯去。
“爸爸,我去扔。”我毫不犹豫接过老鼠走出门。看着手里的糖老鼠,它一面的毛很干净,灰白色,几根胡须长长的,尖尖的嘴上,也糊满麦芽糖。另一边,全沾得满满,粘粘糊糊的。那麦芽糖的甜,诱惑我。好奇舔了一下,好甜,真的好甜。
赶忙跑到一个僻静无人的谷草堆旁。开始,认认真真把那只老鼠舔干净,那麦芽糖的甜,至今仍留在味蕾里,不曾散去。
③,糖水荷包蛋
很想念小舅妈给我煮的糖水荷苞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几个糖水荷包蛋,简至是在吃仙桃圣果,饮琼浆玉液。心中美好滋味,瞬间打开,涌泉般闪出。
春节刚过,初五初六开始走亲戚,去给妈妈家的长辈拜年。也许我是家里最小的,也叫得动我。父母总是叫我,带上准备好的蛋糕茶点,去外婆家。哼!大过年的,妈妈太小气了,也不给乘车的钱,就靠二条腿走着去,还要挑着礼品,走一路,歇一路,累死人了。
外婆住在老湾回族乡六和村,我从家里出发,要花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到外婆家时,正赶上吃午饭。在众多亲戚中,我特愿意去外婆家吃饭,那是小舅妈很喜欢我。每次去给外婆拜年,小舅妈总是立刻给我做一碗糖水荷包蛋,用一个大海碗盛着,五枚鸡蛋像一朵盛开的莲花,静静卧在糖水中间。小舅妈的手真巧,荷包蛋煮的不老也不嫩,白白的蛋皮里,有一颗淡黄的心,被糖水侵泡着,浮在碗上面,又像五颗晶莹的珍珠,滑滑的。美美地咬上一口,蛋蕊爽口润滑,甜而不腻,软柔入口,蛋白合着糖水一起送到嘴里,适度的甜,满口的蛋香,略带点点蛋腥味,下肚后,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说不出的舒服,心情爽极了。一大海碗连汤带汁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还不忘舔舔碗的周边,每一处都是甜的。穷的时候,人总是喜欢甜的东西。
年年去拜年,小舅妈必定为我煮上一碗糖水荷包蛋。外婆与小舅妈住在一起,每次,我都想分二个给外婆吃。外婆却说,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小舅妈也说,你吃,下一锅再给奶奶煮,我便相信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小舅妈家里的鸡蛋都是平时省下来的,你外婆从来没吃过,这鸡蛋都是来招待贵客的。
“我这么小,也算是贵客吗?”
“傻丫头,你爸当场长,是当官的人,平时隔三差五送些粮食,钱给小舅,暗暗帮他们改善改善贫困的日子,也是孝敬你外婆。”
哦!怪不得,外婆总是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偷偷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从她旧棉袄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印着“喜鹊登梅”的手帕,手帕上的喜鹊太惹眼了,印象特别深,那是一叠叠零食。外婆仔仔细细数了又数,才从钱堆里抽出10张崭新的一角,先看一下四周,确定没人,才慌忙塞在我兜里,千叮万嘱,钱别弄丟了,不要告诉他们。外婆孙子、外甥有十几个,唯独给我压岁钱,我都觉得好惭愧。可一走出外婆家的大门,我心里又暗暗高兴,开心极了,一元钱相当拥有一笔巨款了,能不兴奋吗?
现在,我只要想吃糖水荷包蛋,就煮上一锅,也用大海碗装五个,勉强只能吃下二个就饱了,唉!再也没有当年的味道了。
④,六碗猪肝汤
妈妈走了快二十年了。在我记忆的味道里,妈妈做的猪肝苕粉汤超级美味,鲜爽无比,每每回味,那滋味又涌心头......
一到腊月,雪花飞舞,学生放假,农民闲着,父母也忙完了手中的活,回家了。为了准备过年,家家户户都炊烟袅袅,香味溢出。
大家都在忙着年货,我家平时挺穷,超支户,缺衣少食,可一到年关,家里分的东西让我眼花缭乱,花生瓜子,香蕉苹果大鸭梨,糕点麻片白兔奶糖,肉、鱼、丸子、烟酒,应有尽有,可以开个杂货铺了。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冒出来的,怎么不见平时有呢?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爸妈忙了一整夜,其实家家户户的大人都在忙,准备第二天过年的美味菜。
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妈妈叫醒,她端来一碗猪肝苕粉汤,香喷喷的,立刻将瞌睡赶跑了。起床一看,哥哥姐姐们都起来了,一人一大碗,低着头,津津有味地吃着呢。让我们一年没有油荤的肚皮,痛痛快快享受猪肉猪肝的鲜美,啊!太香啦!
妈妈做的猪肝汤其实极其简单:只见她驾起一口大锅,材火在锅底欢快舔着火苗,旺旺的。锅烧热后,将几块生姜片炒出香味,舀上几大瓢水,大火煮开,然后将泡好的苕粉放到锅里,继续沸煮,待苕粉蔫了之后,再将切好的猪肝、腰花、瘦肉用生粉酱油调和好,等锅里的水"吱","吱"的响声时,掀起锅盖,将调好的肝片均匀分散在大汤锅的周围,先不搅动,等猪肝被沸水稍稍凝固后,轻轻推动几下,放上盐、胡椒,再次轻轻铲动,切细小葱花随手撒在苕粉上,最后在出锅前淋点麻油,端锅盛出。首先给父亲盛一大碗,六个孩子六个大碗,每人一大碗,个个都不落下。汤里的内容都盛得差不多了,锅里还有少许汤,妈妈兑些水再煮开,加上苕粉,她给自己也盛了一碗,有滋有味吃了起来。
我问妈妈,为什么总要在三更半夜,偷偷吃呀!白天吃不行吗?
“傻丫头,别人家都没多少肉,一年到头就分一二斤,都省着吃,幸亏你爸爸是公家的人,有单位。分的肉多,物质也丰富。白天做给你们吃,别人不仅会眼馋,还会说闲话,影响不好,不能给你爸找麻烦。肉要捂在饭里面吃!”
妈妈说完,叹了一口气又说:“但愿以后家家都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猪肝汤。”妈妈煮的那六碗猪肝汤,是我们一生的惦记,忘不了,根本忘不了......
美味,在记忆里,何止这些,酸甜苦辣,咸涩霉馊,爽甘香麻,皆尝过,舌尖将味道一一储藏,都烩在人生大锅里。不同的年代尝遍百千异味,无论如何,最后一道菜的味道,就二字:清淡!
《赤卫路一巷里的故事》
①,领取抚恤金
赤卫路一巷,临近江堤边旁,并不起眼。骑着车,从堤坡上冲下来,一不留神就错过去了。1988年搬家到城里,赤卫一巷就成了我每天必走的小巷。其实,自从父亲病逝后,我就熟悉它了。
那年,1987年10月4日,正在读初中的我,突然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一下子懵了,以为是来人开玩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家。一进门,哭声阵阵,只看见父亲躺在堂厅里,闭着双眼,面容祥和,像熟睡的样子。二姐、妈妈早已哭晕过去,身边是手忙脚乱的人们。懵懵的,傻傻的,呆呆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手脚瞬间麻木冰凉,不会哭......
几天后,哥哥姐姐们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妈妈、二姐还在悲痛中。我,没他们那么懂事,还不知道失去父亲的重要性,对一个贫穷之家意味着什么?继续上学去了。没有父亲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这样过了小半年。
有一天放假,妈妈对我说:“三丫头,你去趟城里,到林业局财务室,把你们的抚恤金领回来,妈妈不会签字,你去领吧!”
“抚恤金!什么是抚恤金?”我疑惑地望了望妈妈。
“那是林业局发放的抚恤金,你爸是林场的职工,又是干部,你爸走了,你、还有你三哥,妈妈都有抚恤金,你和你三哥可以拿到十八岁,参加工作了,才会被取消。其他哥姐都有工作了就没有,妈妈的可以拿一辈子”。
“噢,知道了!妈,今天正好放假,我去领”。
平时在乡下林场生活,没去过城里。林业局,父亲曾带我去过一回,印象中好像离江堤很近,具体什么位置,真不知道。算了,到地方了,再向人打听打听吧!我兴冲冲起程了。
搭乘的公共汽车,停在广播大楼前(以前叫三层楼副食商店),一下车,向旁人打听林业局在哪?旁人告诉我,一直往前走,不用拐弯,看到木材公司和防疫站之间,有条小巷,再拐进巷子进去往里走,就到了。依照旁人指示,也顺利,很快就找到了林业局。心里又激动又害怕,犹豫半天后,才小心翼翼上了二楼,挨着门檐上左下角的指示牌,一间一间找财务室。它在左边第二间,财务室里有好多人,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好像都是来领工资,今天应该是发工资的日子。人太多,我不敢进去。等人少些,我再来吧。我悄悄溜下楼,又回到小巷里,看了看周围环境,下次来就熟悉了,以后,每月都要来一次的。这条巷子并不长,路面也不算好,坑坑洼洼,路面还有些细小的砖渣小石块,碍脚。醒目林业局牌子挂在院墙上。门对门是水产局,水产局左邻是豆腐厂,豆腐厂对面是林业局下属单位木材公司,与木材公司一巷之隔是防疫站。在防疫站墙面上有一块红色铁牌,上面方方正正写着:
“赤卫路一巷”
趁有空闲时间,我上江堤逛了好久,太阳正午,肚子也饿了。心想,领工资的人应该差不多了吧!我又小心翼翼走到二楼,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办公室有人在说话。我还是很害怕,不敢进去,躲在窗户下边来来回回走,心里给自己打气,勇敢点!可一移到门旁,又退回去了。“哎呦,曾芙蓉,你太没用了!平时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比男孩还男孩吗?怎么这门槛你都没勇气迈进去呢?”我暗暗骂了声自己。一不小心,碰撞到窗户上。
“喂,这个小孩,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办公室里传来问声。
我...我......我来领抚恤金的,硬着头皮,怯怯地走进办公室,头也不敢抬,眼睛只敢看下面,双手不停搓捏衣角,紧张的手都冒汗了。像犯了错,被人逮住似的。
“你是谁的女儿?你妈妈叫什么?”一声温馨的问候像春风拂过,好听!我稍微不那么紧张了,仍不敢抬头,低声说:“我父亲叫曾凡华,妈妈叫李各珍,是我妈妈让我来领这个月的抚恤金。”我蚊子似的声音,还是被人听到了。
“哦,是曾场长的女儿呀!你父亲真是个大好人呀,可惜走得太突然了,你妈妈还好吧!你不用紧张,你爸爸和我们都是老熟人、同事,也是多年的朋友。”
听到这亲切的话,我才敢抬起头。看见一位阿姨在跟我说话,轻言细语,问长问短,我一一回答,心里暖和多了。阿姨姓吴,是财务室会计,与吴阿姨对座的是一年轻漂亮的小姐姐。吴阿姨转身吩咐道:“小刘,跟曾场长的女儿把领取抚恤金的手续办一下。唉!曾场长突然就这么走了,留下孤儿寡母,怪可怜的。我们应该多照顾关心他们呀!你说,曾场长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太可惜了”。
吴阿姨的话触到我的伤心处,我含着眼泪,抽泣着,忍不住一阵又一阵心绞着疼......
最后,我领到了:126元钱,我和三哥都是未成年孩子,抚恤金是每人每月36元,妈妈略高些,有54元。我第一次知道,父亲病逝后,居然还能领到钱,这给我们贫穷之家,相当有一份救命稻草,度过那难挨的漫长岁月。拿到钱,小心把它放在贴肉的地方藏好。回家的步伐,轻松又愉快,心情格外好。
走出巷口,我又回头深深望了一眼那路牌:
“赤卫路一巷”
亲切又温暖。太阳光一照,五个红色大字犹如五朵鲜艳的花,绽放在我眼前,更照亮我前方的暗路。
②,搬到赤卫路
每月十五号,我都要来城区一次,领取抚恤金。赤卫路一巷,已经走熟了,不再是怯怯懦懦,反而脚步轻盈,心情愉快地来林业局财务室。每当拿到生活费的一瞬间,心里都美滋滋,像灿烂的阳光照射在心里。一家人的生活有着落了,父亲的抚恤金,给一贫如洗的家,带来生机与希望。仿佛父亲并没走,还在支撑着,我们的家。
俗话说,“宁可死当官的老子,不可死叫花子的娘”。可父亲突然病逝,我就如塌了天,心里又恐慌又悲伤。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孤儿寡母以后依靠谁呀?妈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也没有正式工作,平时在父亲的林场打零工。突然变故,让妈妈承受这双重打击。
无论日子再苦,还得继续往前过。经过大哥努力争取,林业局照顾遗属,决定在林业局新建宿舍,分一套房子给我们家。以前父亲在世时,也曾够分房的资格,被父亲拒绝了,优先让给别人。为此,大哥与父亲大吵了一架。这回,是真的有套新房了,而且还是在城里。我们几兄妹都高兴坏了,既兴奋又激动。唯独妈妈愁眉苦脸叹了一口气说:“唉!听说城里什么都要钱买,你们都还没正式工作,这日子该怎么过哦!搬到城里好是好,可这柴米油盐过日子,哪哪都是要用钱啊!听说材火、水、小菜都是要花钱买,以后,一大家子开销,怎么过哟?”
“妈,别怕!有我们呢!都是一双手,城里人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只是比别人过得苦点、差点。但搬到城里,以后弟弟妹妹读书、找工作都方便些,他们的见识看得也比乡下多些。城里肯定比林场要好百倍呀!”大哥安慰妈妈说。
“你爸已经走了,以后家里的事,你做主吧!妈妈没有文化,又没什么主见,以前都是你爸当家。老大,弟妹们都还小,家里的事该你担着了。”
“嗯,知道了,妈!”
1988年下半年,我们一家从黄蓬林场搬到林业局的一个下属单位一一一一木材公司宿舍三单元四楼。本来,是分在林业局新建的新房子,却被人调换到,木材公司旧宿舍楼里,我们刚刚从乡下上来,争不过人家。其实,新房、旧房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崭新的。因为它正处在:
“赤卫路一巷”
熟悉的巷子,我像见到多年的朋友。以后,领取抚恤金会更近了。
初搬到城里,我心里格外兴奋,城里的一切既陌生又新奇,从来没住过楼房的我,一下子住在四楼。心情美滋滋的,好自豪。跑到阳台上往下面一看,呀!头,顿时晕乎乎的,心,跳得好快,不行,不行,不敢往下看了,吓死我了。三哥取笑我,胆小鬼,这有什么,以后住着住着就习惯了。第一夜,失眠,睡不着。平时,在林场,早已夜深人静,林子里漆黑漆黑,各种各样的鸟不停低婉哀鸣,扑腾着竹梢,弄得哐啷响,窗户用报纸糊上,雨水一打湿,只剩一小半节贴在玻璃上,树枝被月色弄影,在窗口外妖娆多姿,让我想起了《画皮》里的女鬼,害怕地裹紧被子,总是在害怕中睡去......
此刻,墙上的时钟敲响了十一下,从窗户望去,小巷里夜市好热闹,灯火通明,斜对面的豆制品厂机器轰隆,工人们都在上晚班。原来,城里人晚上还有上班的,还能买东西吃,好羡慕呀。我们在乡下吃二顿饭,上午一餐九点多吃正餐,下午5点多吃晚饭。就没了,即使饿了,也得忍着,等第二天再吃。城里人深夜居然还能喝酒、聚会、消夜,上班,真幸福!
这一夜,我终于不再害怕黑夜,觉得安全极了。也不怕晚上会有女鬼敲窗,窗外透进来的亮光,布满整个房间,巷子里这么多人在消夜,谈笑风声,鬼应该不会来。就这么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睡着了,睡得特别沉,特别舒服。
一早起床,洗好脸。巷子口里传来一阵阵吆喝声:
豆腐脑,新鲜的热豆腐脑......
包子、馒头,刚出锅的包子馒头......
油条包糯米哦,咸的、甜的油条包糯米......
快来买菜呀!刚摘的青菜,二分钱一斤,多买,一毛钱7斤......
卖鱼,卖鱼哦......
哎呀!在林场,除了被大公鸡和鸟儿吵醒,还从来没听过,这么多卖东西的声音混杂一起的。真好听!
来到楼下,一眼又看见那红色铁牌路标,钉在防疫站的墙面上。好亲切!
我,就这样与你再次相遇。以后的日子,要与你朝夕相处了,我新家的门牌号码:
“赤卫路一巷”。
③,楼顶的小屋
自从搬到,赤卫路一巷木材公司宿舍后。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安稳下来,也开始慢慢习惯城里的生活。
妈妈和我,三个哥哥,住在二室一厅,54平方的房子里。大哥、小哥一个房间,我和妈妈一个房间,唯独剩下三哥没地方睡,不大的房间都放了两张床,大哥、小哥都是二十多的小伙了,谁也不愿意让这个弟弟来蹭床。没办法,三哥只能委身在,客厅沙发上将就。有时候,见他没睡好觉,很心疼三哥。便主动与妈妈挤一张床,把我的床让给他睡几天。
这种日子渐渐熬到夏天,三哥终于不用睡客厅的沙发了,他拿起一张凉席,上楼顶去睡。他每次睡之前,先提几桶凉水把楼顶泼湿。白天的烈日把楼顶烤得像火炉,直接把凉席铺上去睡,他的背像似锅里煎的鱼,就差那"吱吱"冒烟了。
用凉水多泼几次,吸干了再泼,反复多次泼,晒热的地板会慢慢变凉,再睡上去,就好多了。
日子,总是过得很慢。即便过得再慢,转眼间,秋冬季节还是来了,树上的秋叶正凋零飘落。三哥不能再到楼顶睡觉,深秋露寒。只得再次缩在硬硬沙发上。他很乐观,从不计较,也没觉得他像家里多余的人。
直到有一天,三哥兴冲冲地喊我,高兴地说:“妹妹,来楼顶,给你看样好东西。”
“你能有什么好多西给我看呀!”我疑惑地问他。他故作神秘,急急地拉着我上了楼顶。
跟着他,迫不及待上了四楼平台。他带我翻过栏杆,来到邻边一建公司宿舍,楼顶的一间小屋子前。木材公司宿舍与一建公司宿舍紧紧挨着,跨一小步就翻过去了,中间几乎没有距离。
来到楼顶那小房子前,三哥瞟了瞟四周,见没有人。神神秘秘从口袋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那黑色的小锁,推开门,三哥做了个绅士般优雅的请进姿势,自豪地说:“妹妹,请参观你三哥的豪宅。以后,我也是正儿八经有房间的人了,你三哥我呀,在这个繁华城市,终于有属于我的房间了。”
顺着三哥的手势看过来,呀!一间小小的房间布置倒也简单、巧致,靠右墙边放了一张简陋的床,很节省空间。床的左方,一张破书桌,一把旧竹椅,估计也是捡被人丢弃的,擦得干干净净,摆放两旁。书桌上,整整齐齐码着,他平时要看的书。四面墙上,用旧报纸糊了一遍。地,扫得贼亮,撒上水遮尘。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刚刚进来的小门。没想到,他还偷偷装了电灯,30瓦的灯泡,长长开关线连在他的床头,一拉,满屋子都像金色的阳光,温暖如春。
“快关了!快关了!不能让人发现了。灯,平时不能随便开,只有在深夜人静,想看书的时候才能用。”
“三哥,你太聪明能干了,我都有点崇拜你了,你是怎么想到的”。
“我也是被逼无奈,偶然发现的。每天,睡硬沙发睡得腰疼,大哥、小哥也不愿意我与他们搭睡。那天,我就发现这间房子,门没锁,推开一看,是间杂屋,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破破乱乱,花了好几天搬运,清扫,整理,白天怕人发现,只能晚上偷偷干。看,这间房还不错吧!”
“我是说,这些天,你每天往楼顶上跑,原来是在干这个呀!三哥,你真行!佩服你,真的!”我自豪地望着他。
那晚,我在三哥的“新房”呆了很久,兄妹俩的悄悄话,像斩不断的溪水,润湿了天边的星和月,也吵醒了东边的鱼肚白。
赤卫路一巷还有很多的故事,待续......
《父亲的烟火》
父亲手指间
熏染成深黄、积攒厚厚香烟岁月
手中的缭绕、除了睡觉、从未熄过
乡里人俗称抽“接火”
父亲专情独宠“常德”一种牌子、直到烟蒂燃尽
仍贪馋飘在空气中那缕残香
给父亲买烟
成了我童年最惬意的事
二张二角或者四张一毛
从父亲手中接过
蹦蹦跳跳到商店
余剩的四分钱买几颗棒棒糖
一路小跑回家
风中都带甜的味道
父亲唯独叫我
又要做出不让哥姐们吃醋的样子
每次总是沉下脸故意训喝道
丫头
快去跟我买一包烟来
不许在路上偷懒
宠溺给我一个眼神
心领会神接过钱飞冲而去
每次余剩的钱
让我的童年过得多姿多彩
不知道还有没有
三毛六分钱一包的常德
若能寻来肯定买上一百条
穿越时空隧道递给他
重新点燃
熄灭37年的烟火
写在2024年父亲节前夕
热烈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